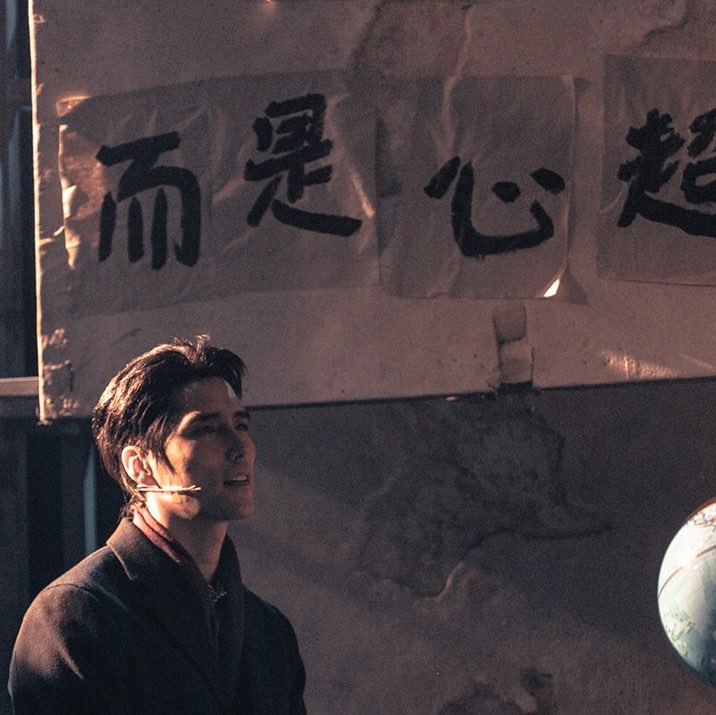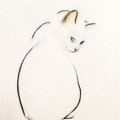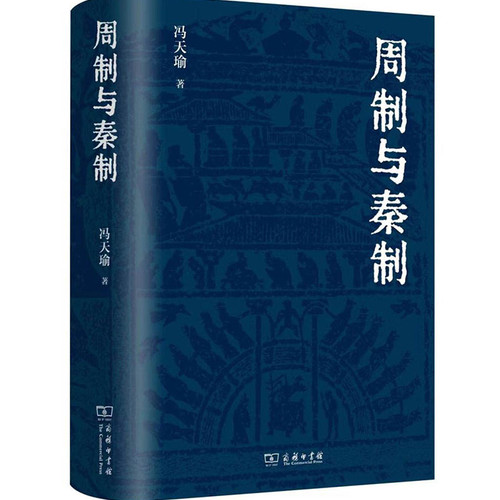别人是游客,我是旅行家
作者:维舟
2018-02-07·阅读时长7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3635个字,产生6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印裔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
就像这世上有许多种意义完全不同的“旅行”一样,与行走相关的书也是五花八门的,以至于很难说它们能构成一个单独的分类。
在早先的历史上,人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出行:朝圣、行军、移民、逃难、经商、探险,如此等等,这其中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他们旅行的目的并不是“旅行”本身。在前现代人的心目中,异域就算不是神鬼之地,至少也是路途危险的未知空间,出门前往往都要先占卜、祷告,甚至留下遗书,远途旅行就更是如此了,那基本是在“用生命行走”。在英语里,“旅行”(travel)一词源出古法语,其本意是“劳苦”(to toil,labor),实际上,就算是被公认为一种娱乐活动的现代旅游,有时也包含着艰苦的“自虐”成分。因此,被我们现在称之为“旅行家”的那些古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都是对他们的误称,最伟大的早期旅行家玄奘、马可·波罗、伊本·巴图塔,他们既不是想要“旅行”,眼里的世界也完全不一样,自然,他们所留下的“游记”,现在更多地被当作是历史文献,其事迹也往往笼罩在一种幻想和传奇的气氛之中——想想看,《西游记》也是一个关于旅行的故事,但我们大概很难想象哪个现代人的旅行能玩出《西游记》这样魔幻体验的境界。
作为一个安土重迁的民族,中国人对“旅行”一事原本并不在意,加上自身文学传统中那种无可救药的抒情传统,即便是游山玩水,通常也把情怀蕴藏在简短的诗词中打发了事。传统观念中的“风景名胜”,其实都蕴含着强烈的人文色彩,即便是魏晋以来传统中的“山水”也是如此,像徐霞客这样的人物,差不多是难以继承的异端。从某种程度上说,“旅游”所暗藏的那种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这种离心倾向,是与传统的价值观相矛盾的。大概也是因此,直到晚清的危机年代,中国才开始大量涌现出各种对外部世界的游记——不过那时的游记,无论是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还是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读起来都总有几分“考察报告”的味道。话又说回来,当时来华外国人的许多游记,无论是传教士或探险家们的记载,或日本人所写的《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燕山楚水》之类,也大多如此:他们描述的与其说是自己的行程,倒不如说是对中国的新认识。
文章作者


维舟
发表文章33篇 获得3个推荐 粉丝419人
涉猎驳杂,少时沉迷于古典文学与历史,长而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