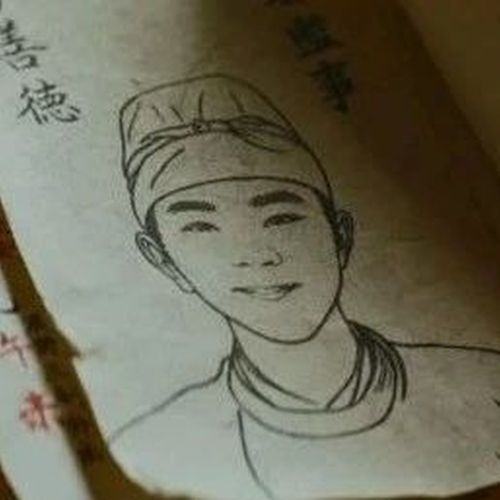黄滨:有说服力的演奏是个人化的
作者:爱乐
2021-02-19·阅读时长13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6760个字,产生5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文/张可驹
一直希望访谈小提琴家黄滨,她与钢琴家郑吟合作,演出莫扎特几首奏鸣曲的现场是我最难忘的室内乐聆听体验之一。后来她们的莫扎特发行了唱片,无论就表现室内乐默契的精髓,还是莫扎特的戏剧内涵来说,都可谓精彩绝伦。前段时间,黄滨来上海演出贝多芬的协奏曲,同样呈现了非常耐听的演奏。其后很高兴得到机会,对小提琴家进行了一次访谈。
张可驹(以下简称“张”):能否谈谈你早期的音乐生活?
黄滨(以下简称“黄”):我是从四岁开始学小提琴,因为我父亲很喜欢小提琴。开始学的时候,是跟着离家比较近的一个老师。但我父亲是学物理的,对于声音等等,有科学的认识,发现那个老师教得有点问题。后来我们找了周善同老师,当时他年纪已经比较大,我叫他周爷爷。每周去他家,父亲带着我,骑自行车过去,每次骑一个多小时。周爷爷教了我一年多以后,表示他已经无法再教我,需要更好的老师。于是,他帮我介绍了郭淑敏老师,她也在长沙,我就继续跟她学。八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父亲看到《光明日报》上刊登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招生启事,那是文革后的第一次招生,1980年。考上了,念到1988年附中毕业,就到了美国的皮波蒂(Peabody)音乐学院。早年非常重要的就是父亲看着我练琴,他对声音、音准的要求比较高。之前两位老师都很重视基本功,到中央音乐学院之后,我和王治隆老师学了八年。他是非常非常负责的一位老师,每周要上两三次课,对基本功的要求很严格。当时我很喜欢听歌剧。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父母放很多童声唱片,我就一首一首地从早唱到晚。中央音乐学院的音响资料不多,一位同学的父亲在美国,给她带了《茶花女》的唱片,我每天听,都能背下来了。歌剧对我的影响很大。去了美国之后,其实有点失落,因为在国内还挺好的,到那边却发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赴美一年后,霍洛维茨去世,我当时确实没听过什么音响资料,就问:霍洛维茨是谁?我的老师感到诧异。
张:从2002年那张巴洛克音乐到后来的莫扎特,从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的现场全集到最近的贝多芬协奏曲,能否略谈你如何建立全面的技巧和音乐表现?
黄:在技巧方面,我一直在探索一些更好的方式,现在也是,有不少尝试和研究。我总觉得,海菲茨那代人就是最为黄金时期的小提琴演奏,他们的技巧和现在不一样。包括声音、清晰度,纯粹从技巧来说,先不谈音乐层面。我在想为何会这样?因此一直在探索。而出现这种情况,我想可能是某种小提琴技巧的……遗失吧。现在主要推广的一些技巧,和当时不太一样了。
张:你认为主要遗失的是哪些方面?
黄:肩垫的使用是很关键的。现在的人大多用肩垫,而当时的人基本都不用,这是很关键的,因为两种拉法完全不同。用力,还有弓子上的很多东西,都会不一样。持琴的角度会变化,而且在用力这方面,不用肩垫的话,肩部是自由的,而用了,就会把这部分固定住。手的情况也不同,在不用肩垫的情况下,琴是三个支撑点,这两个(注:指着下颚和肩部),还有左手。此时,手不托住的话,琴是夹不住的,必须托着。而用了肩垫,不用左手托着,也能夹住琴。左手托与不托,用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还在研究,因为想表达心中的音乐,没有最自由的技巧是无法达到的。当你和乐器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连接,它会启发你,关于声音,也关于更多对音乐的感受。而从音乐(表现)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要去了解从某种“起源”所展开的一个大的图谱,知道很多东西从哪儿来,它整个的发展过程,作品的不同的形式,它们在不同时期的风格。对我来说,巴洛克音乐像是一把钥匙,能打开古典、浪漫,包括更后期的作品的理解。因为从巴洛克开始的音乐,已奠定了很多东西,包括和声、曲式结构,还有一些风格,譬如很多舞曲。很多现代的、后现代的舞蹈的节奏,都是从那边延伸过来的。所以,如果对巴洛克音乐没有较深的认识和感受,演奏家就会缺乏某种坚实的基础。或许你对那些舞曲也会有感觉,但仍会丧失很多潜移默化的东西。同样,不和谐的和声的用法,也是从那时延伸过来的,对位等等也一样。我原先很多是直观的感受,研究了巴洛克音乐,还有更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会感到自己有了坚实的基础。但我想,无论如何,尽管需要这样的基础,演奏者直觉的感受和感动还是最宝贵的。
文章作者


爱乐
发表文章834篇 获得3个推荐 粉丝18389人
三联书店《爱乐》杂志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