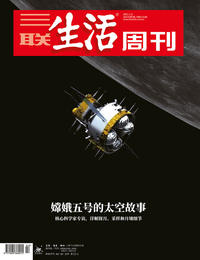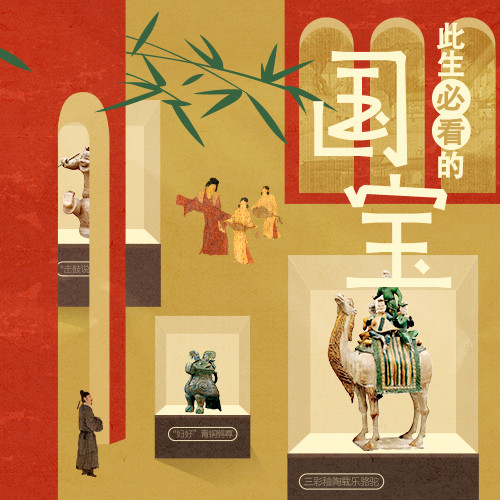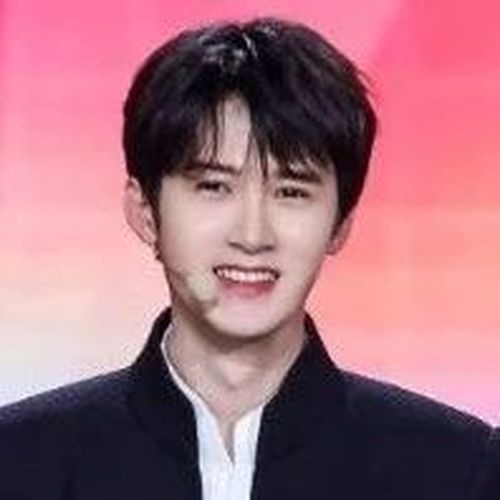百舸争流:进入21世纪的全球太空竞赛
作者:刘怡
2021-01-07·阅读时长11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704个字,产生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法属圭亚那,阿丽亚娜系列火箭模型前
新角色,新模式
“到2024年,我们将会实施阿拉伯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探月行动。我们的月球车将会光顾此前其他国家的月球探测器未曾抵达的地点,从那里发回图像和数据。全世界的科研机构都可以分享这些采集来的数据。”
放在50年前,哪怕20年前,这样自信满满的表态都只会被当成一则来自波斯湾的愚人节笑话。是的,信息的发送者是阿联酋总理兼国防部长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亲王,一位身家超过40亿美元、拥有两艘私人游艇的中东富豪和国务家。但阿联酋从来都不是一个与“探月”或者“太空”存在多大关联的国家:尼尔·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那一年,它还只是一个半独立的英国保护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是珍珠采捞和捕鱼。在那以后,油气开采、银行业乃至房地产交易的勃兴使得阿联酋逐渐跻身海湾“土豪”国家之列;然而直到2006年穆罕默德·本·拉希德航天中心(MBRSC)在迪拜落成为止,依旧没有人相信他们可以在短期内收获成绩。
不过,到了2020年9月29日,当穆罕默德亲王在“推特”上发出那段豪言壮语时,人们已经开始把阿联酋当作“太空竞赛2.0”中的第二梯队要角加以看待了。通过高薪聘请全球顶尖人才培养属于本国的科研团队,并在精密制造方面投下重金,阿联酋航天事业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实现了腾飞。从2009年到2018年,迪拜先后将4颗地球观测或通信卫星发射入轨,其中“哈利法星(迪拜3号)”完全由本国团队研发和制造,租用日本火箭升空。2019年9月,阿联酋第一位宇航员阿尔·曼苏里乘坐俄罗斯“联盟MS-15号”飞船抵达国际空间站,在其中停留了8天。就在穆罕默德亲王公布本国的探月计划之前不久,2020年7月19日,迪拜自行研制的“希望号”火星探测器在日本种子岛宇航中心成功发射,它将在2021年2月进入火星轨道,开始执行任务。
后发国家阿联酋的异军突起,正是21世纪太空竞赛方兴未艾的缩影。与“冷战”时代美苏航天竞赛的“二人转”模式不同,新一代参与者在主体的性质和介入活动的层次方面都变得更多元了。中国和印度已经先后发射了自己的火星探测器,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探月计划。它们也与俄罗斯、日本以及欧洲航天局(ESA)一道推出了针对国外客户的火箭租赁发射服务。波音公司研发的7人飞船“星际航班”(Starliner)已经在2019年底进行了第一次轨道飞行测试,它可以反复回收利用10次,与四种大型运载火箭兼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私人企业成为了和国家计划并行不悖的参与者——硅谷巨头马斯克(Elon Musk)创办的SpaceX公司在2020年成功完成了“龙2号”载人飞船的两次发射,将6名宇航员送入国际空间站。这两次发射使用的是SpaceX自行主导研发的“猎鹰”(Falcon)系列运载火箭,它标志着私营科技公司已经崛起为商业航天活动中的要角。无独有偶,亚马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Jeff Bezos)也在2019年公布了自己的探月计划。由他创办的航天制造和服务公司“蓝色起源”(Blue Origin)已经开发出多个型号的第一级可回收式运载火箭,即将进军租赁发射业务。
既重视科技含量和安全性,又致力于降低成本;既强调研究意义,又视之为商机和盈利手段:这正是2.0时代太空竞赛的新特征。它使得对未知宇宙的探索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连接得更加紧密,同时丝毫不曾折损我们对广袤空间怀有的好奇心。就像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斯蒂芬·卡特在2020年9月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的那样:“未来或许永远不会像库布里克在《2001:太空漫游》中想象的那样乐观,但月球这个离我们最近的邻居依旧令我们着迷。哪怕一天只盯着它看上几分钟,你也会去思考人类在一个更大宇宙中的位置。”

2019年9月25日,阿联酋首位宇航员苏丹·尼亚迪(右二)将搭乘俄罗斯“联盟MS-15”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
NASA的误算
“土星5号”(Saturn Ⅴ)火箭并没有留下多余的实物。在今天的休斯顿和亨茨维尔,博物馆中陈列的是用结构强度测试之后的破损壳段拼接起来的4具“伪”成品。但即使是它倒卧在陈列架上的躯体,也足以令人惊叹其庞大程度。实际上,直径10.1米、全长110.6米的“土星5号”乃是人类航天史上推力最大的发射载具,它理论上的有效载荷高达140吨,是苏联同一级别的运载火箭N1的1.47倍。从1967到1973年,正是“土星5号”完成了“阿波罗”系列载人飞船以及“天空实验室1号”(早期空间站)的总共13次发射。6批美国宇航员曾经借助它的巨大推力登上月球表面:这也是迄今为止人类航天史上的纪录。
但在1972年底最后一次“阿波罗”登月任务结束之后,“土星5号”迅速被打入了冷宫。体形过大导致的不经济性是它失宠的直接原因:在载人登月计划终结之后,频繁使用载荷过于“富余”的超重型火箭未免显得太奢侈了。发射卫星或者小型探测仪器这样的常规任务,动用载荷仅为其1/3甚至更小的两级式火箭就可以很好地完成。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已经决定放弃“重型火箭+单次使用飞船”这组看似成本偏高的载具方案,转向一种可以部分回收使用、内部空间也更大的外挂动力轨道飞行器——航天飞机。
作为“阿波罗计划”的最后几项遗产之一,航天飞机反映了NASA将载人航天活动的整个流程加以标准化的努力:里根政府不赞成NASA将美国火箭外租给其他国家用于商业航天活动并借以增加收入的举动,这意味着当时型号过于庞杂的火箭和飞船必须被削减。而航天飞机最好地满足了这种控制成本的需要:它可以一次性搭载多名宇航员以及大批设备前往空间站,每次飞行后不必更换全部零配件,联邦政府还会为每次飞行支付5000万美元的津贴。按照最乐观的想法,整个美国航天业只须建造5架航天飞机,每年完成20次到60次不等的飞行,便足以胜任过去由好几种型号的火箭和飞船分担的太空任务:不仅标准化,而且多功能。
在这种激进理念的推动下,从1981年到1987年,NASA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完成了5架航天飞机的制造和整备,同时暂停了一切独立研发的重型火箭项目。然而,灾难接踵而至:1986年1月28日,搭载着7名宇航员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73秒后爆炸,震惊了整个美国的电视观众。到了较晚的2003年,又发生了“哥伦比亚号”因为燃料箱隔热层破损、再入大气层失败后彻底烧毁的悲剧性事件。NASA终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航天飞机存在的风险:由于以搭载尽可能多的人员和设备、从而提升经济效益作为设计理念,每次航天飞机发生事故,都可能导致极其惨重的损失,尤其是有经验的宇航员的损失,而并不是每项太空科考任务都需要通过人力来完成。另外,一切材料都有疲劳性和寿命周期;尽管航天飞机上的一部分零件不必在每次任务结束后就更换,但对重新整备后的飞机进行测试依然需要耗费可观的成本,还无法杜绝疏漏。
文章作者


刘怡
发表文章196篇 获得4个推荐 粉丝2499人
身与名俱灭、江河万古流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