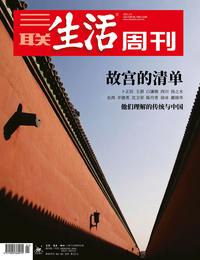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
作者:蒲实
2020-12-30·阅读时长9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4854个字,产生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主笔/蒲实
实习记者/王鸿娇
“城”与“市”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刺桐城》一书里提到,泉州经历了从一个地方的、边缘性的城市转变成一个非边缘的、被纳入官方体系的过程。它大致是一个怎样的转换过程?
王铭铭:现在我们叫泉州的地方,远古生活着“百越民族”,可想而知,那时,“原住民”也有自己的中心-边缘区位体系。但从“国史”角度看,泉州区位系统的形成,与永嘉之乱和安史之乱相继导致的华夏文明中心南移是紧密相关的。泉州首先是这一转移的结果,此后,它从“越地”变成了一座华夏世界的区域性城市。一旦有了城市,就有一个以华夏为模型的区系制度。北方衣冠南渡及更多人口在唐中叶后的南迁,给南方带来财富、“社会”和文明。这大概便是我们所说的“非边缘化”的意思吧。
到了南宋,以开封为中心的历史变成以杭州为中心的历史,进一步地抬升了泉州的地位。按照人类学前辈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说法,浙江、福建和广东东部基本上属于一个经济区。南宋首都区位的转移,使着整个经济“中心化”了。泉州从中获益颇多。那时的泉州有点像南宋的一个经济特区,南宋有很多财政收入是从泉州来的,同样,泉州也受益于朝廷给它的特殊制度。南宋在泉州有皇族的一支,南外宗。他们一方面从海外贸易中收税,另一方面依赖泉州的经济收入养活自己。
泉州史接着的转变跟元帝国的兴起有关。这个帝国的粮食依靠南方,南北海上运输(漕运)对朝廷很关键,而这一运输大大仰赖泉州海船和船帮。加之元朝统治者似乎比较习惯文化多样性,对于泉州商贸和宗教的“世界性”乐见其成,这给了它新的机遇。
区系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比如说几个小村庄之间需要有一个市场,不然无法互通有无,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以市镇为中心的小区域体系。再往上,市镇之间出于互通有无的需要,会形成一个更高的区域体系。但中国的区域体系有民间自然而然的发生史,也有朝廷通过建立州县建立一个更正规化的系统给予的推动。从泉州的经济区系发展史看,动力是复合多样的,它的“非边缘性”的获得,原因也是复合多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之后泉州又有一个被边缘化的过程。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这种空间转移?
王铭铭:我自己的看法是,从明初开始,泉州城市的繁荣面貌就慢慢走向灰暗了。明以前,泉州亦儒亦商,明初,城中儒商中的“商”的气质不大受朝廷喜欢,朝廷喜欢的是“儒”。在宋元这段时间,当地尽管建立了州府,有行政区系,但还是相对自主。到了明初,朝廷很焦虑,觉得之前朝代有点以夷乱夏,外国因素太多,特别是像泉州这个地方,在国际贸易上的地位很重要,夷的文明因素——如各种世界宗教因素——也很多。明初的朝廷更鼓励用儒家教化来改变这种文化上混乱的自我认同和流动性过强的局面。此时,这座城变成一座象征着华夏文化的地点,很多礼教空间得以建设,那些不大相同的因素被压抑。朝廷还有很多反对商业贸易的政策,排斥民间的商业功能。这些商业功能迁出城外。沿海出现很多从事海上贸易的民间城镇,靠传统上自己善于做的那些事营生。泉州自身的海上贸易功能下降,社会治理功能上升,不再是“市”,而是“城”,代表的是“治”。
有一个短暂的阶段,地方精英努力想复兴它原有的繁荣。大概是在清初,地方上有一些人在朝廷当了大官,他们跟地方的这些派系关系比较密切,都对家乡有一种感情。他们设计的一些政策比较倾向于道教思想,重视民间社会生命力的培植,但为时已晚。后来鸦片战争给了泉州另外一个打击。此后建立五个通商口岸。泉州这座老通商口岸的地位与福州和厦门相比,在世界经济体系格局里变得次要了,可以说几乎彻底边缘化了。
文章作者


蒲实
发表文章153篇 获得1个推荐 粉丝1984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