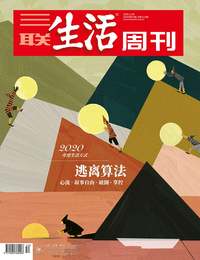又坚强又脆弱又敏感的玻璃
作者:张星云
2020-12-24·阅读时长11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707个字,产生16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上海玻璃博物馆的工作坊
退火
退火是玻璃制作中的重要环节。在上千度的高温中,玻璃熔料变得像蜂蜜软糖一样柔软,然后被塑型,再在重热炉里被反复加热、保温、慢冷、快冷。退火不可或缺,在减缓冷却速度的同时降低玻璃的永久应力,让玻璃最终获得稳定和持久的特性。
不过艺术家杨心广最初没有意识到这点。他向我回忆说,为了做出玻璃丝“缠绕”在金属栏杆上的效果,他将绵软的玻璃熔料从重热炉中取出后直接挂在了栏杆上。效果看似很好,但等第二天再回工作室的时候,他发现玻璃丝全都碎了,碎了一地,就因为没有退火。他很崩溃,不过就此稍微了解了一些玻璃的脾气。
那是上海玻璃博物馆“退火”项目的第二年。自2015年与艺术家张鼎合作举办了一场用玻璃创作的现代艺术展览之后,博物馆决定每年邀请两名当代艺术家来创作,规则很简单,只有两个要求:以玻璃为创作材料;作品在博物馆的空间内展出。
玻璃是一种门槛极高的材料,需要有物理、化学的专业基础知识以及相当高的操作技术,但像杨心广一样,大部分受邀的艺术家此前从没有接触过玻璃这种材料。这也是项目的初衷,为玻璃寻找一种不受制造业束缚的感性表达。项目取名“退火”,将艺术家们的每次试验比作玻璃退火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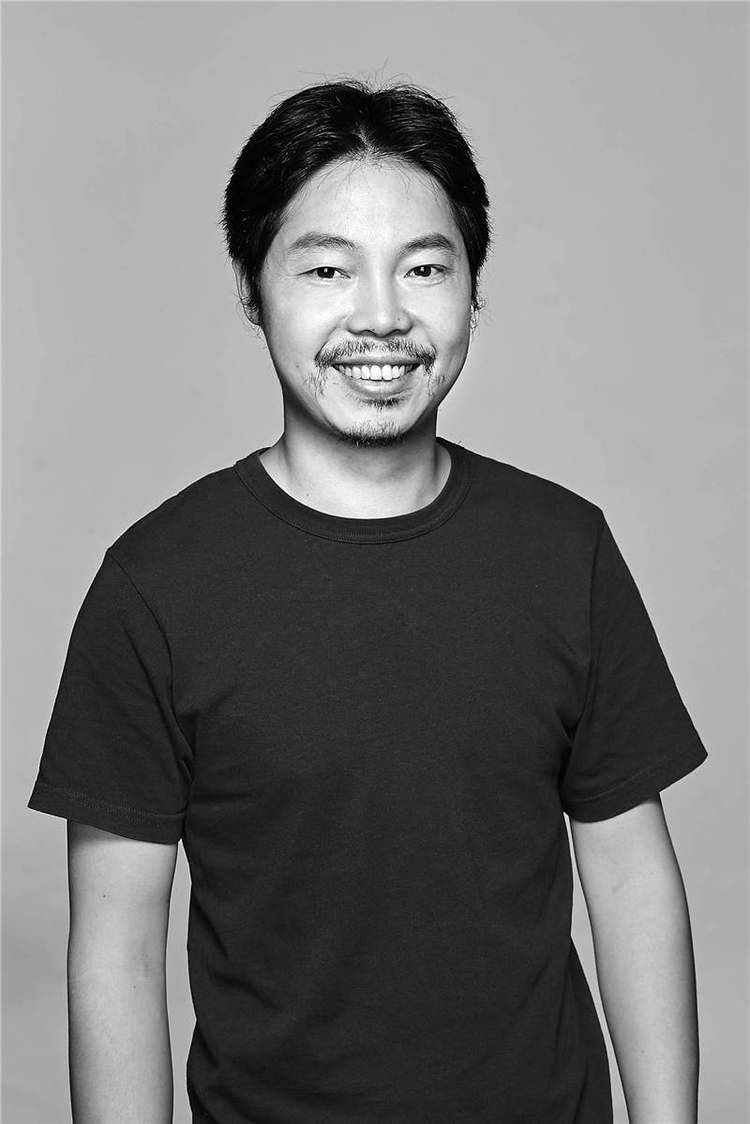
艺术家杨心广
5年里,8位艺术家先后参与了“退火”项目。近日上海玻璃博物馆举办“退火”5周年特别展“重置”,选取了每位艺术家制作的一两件玻璃作品,将它们分布在整个博物馆园区,每个作品背后,都是一段艺术思维与工业生产逻辑相互角力和吸收的故事。
尤其对已经成名的艺术家来说,这个项目有着很大挑战。“玻璃不像雕塑、绘画、新媒体,只要在工作室里闭门造车就行了。”博物馆学术研究经理阳昕对我分析说,“他们需要去玻璃工厂,与工匠合作,真正地与这种材料以及这种材料背后的制造行业发生关系,让材料本身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最后这些艺术家制作的玻璃作品往往与他们之前的创作风格有很大区别。”
博物馆设计了一套“教学程序”:受邀的艺术家,首先被带去参观博物馆常设展,建筑玻璃、精密科学仪器、古玻璃文物、国内外当代玻璃设计作品,无所不有。了解完玻璃的历史,在专门的工作室里,博物馆自己的玻璃工匠向艺术家展示吹制、铸造、冷凝、切割、打磨等玻璃制作最重要的几种工艺。随后,艺术家再被带去上海周边的大型玻璃工厂,真刀真枪地使用大型窑炉和机械做尝试。
杨心广2007年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算是个年轻的艺术家。他对大自然中的天然材质很敏感,曾将整棵树干削成锯齿状取名《剩余体积》,将沙土摊成特定形状取名《坏土》。在南法普罗旺斯的山顶,他用小石头围成一个不高兴的圆脸网络表情符号。他还用水泥混凝土浇铸成小山的形状,摆在阿那亚的海滩上,通过作品探讨自然与人们所处的周边世界的关系。
在杨心广看来,玻璃与人很相似,火焰之下,玻璃柔软,可冷却之后,它会变得坚硬。看似晶莹剔透,但又脆弱冰冷,稍有外力就可能直接崩裂,锋利的断口会划伤接近者的皮肤,造成切肤之痛。
在工作室里,第一次接触玻璃的杨心广,看着因为没有退火碎了一地的玻璃,突然想到古代文人笔下经常出现的抒情意象“断肠”。人的七情六欲与身体的五脏六腑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成语“猿肠寸断”出自东晋文学家干宝的《搜神记》:人捉住猿子,猿母便悲号而死,肝肠寸断,此后人们便用“断肠”来表达思念和悲痛。诗人们会在山水之间触景生情,感慨“断肠人在天涯”。
善于雕塑的杨心广选择了玻璃铸造技术,先用雕塑泥做模子,然后将滚烫的玻璃水浇铸在模子中,将玻璃铸造成一条条人体大肠和山石的形状,玻璃山石中间,穿梭着透明的玻璃大肠,就像“断肠”可以容纳周围山水所激发的诗人情怀一样。
文章作者


张星云
发表文章193篇 获得2个推荐 粉丝1035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