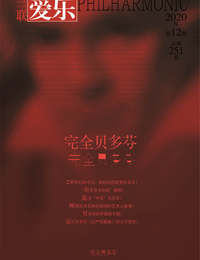定位贝多芬《庄严弥撒曲》的五个维度
作者:爱乐
2020-12-23·阅读时长10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307个字,产生9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文/鸦趴趴
19世纪作曲家路易•施波尔在自传中谈到贝多芬时写道:“(《第七交响曲》之后)他的耳聋愈发严重,完全不能听到音乐,这对于他的幻想力必然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他总是努力摆脱陈规,开拓新路,然而现在他的耳朵不像过去能使他免走歧路。因此,他的(晚期)作品愈发巴洛克,愈发缺乏内在联系,愈发难以理解。……他经受的严酷命运使我非常悲伤!耳聋对谁都是巨大的不幸,何况是一位音乐家,他怎么能够忍受住而不陷于绝望呢!”
今天,贝多芬晚期作品已经被论者公认为复杂而深邃的伟大之作,因此爱乐者可能不大能理解施波尔的评价。然而如果回到19世纪上半叶,施波尔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不少人认为这些作品病态、费解,而首要对此负责的,就是贝多芬的耳聋和由此导致的心理上孤寂、隔绝的状态。
那么,对贝多芬晚期作品评价为何会产生如此大的改变呢?美国音乐学家尼特尔(Knittel)在他的论文《瓦格纳、耳聋和贝多芬晚期的接受》中指出,瓦格纳对于这一变化发挥了重要的影响,而其中,更以瓦格纳对贝多芬“耳聋”的重新评价尤为重要。
不过,瓦格纳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欣赏贝多芬晚期的,19世纪50年代以前,瓦格纳对于贝多芬的晚期作品(除了《第九交响曲》之外)的接受,也大体上不出施波尔那种不理解但同情的路子,比如在《歌剧与戏剧》中,瓦格纳写道:“(晚期)贝多芬让我们觉得他有话要告诉我们,但是却无法传达。”
1853年左右,瓦格纳于巴黎短暂停留,在那里听到了莫兰-舍维拉尔(Maurin-Chevillard)四重奏演奏的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由此,他对贝多芬晚期作品的印象有所改观。其中尤其是Op.131,对瓦格纳的触动很大。他在自传《我的一生》(1865-1880)中写道,在巴黎,Op.131的“真正形式,第一次展现在我的面前”。
文章作者


爱乐
发表文章834篇 获得2个推荐 粉丝18387人
三联书店《爱乐》杂志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