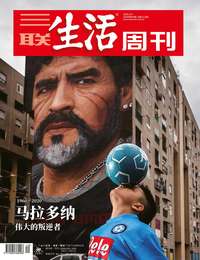当拳头挥向父亲:拆迁10年的“新老”之争
作者:王珊
2020-12-03·阅读时长18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9499个字,产生1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莫正才一个人居住在老屋里,每年只有在春节时才去儿子家吃一顿饭
本文摄影/张雷
城市身份
莫正才87岁,身高一米七左右,身材瘦削,脸上的皱纹堆叠在一起,太阳穴旁青褐色的老年斑被帽子遮住了一半,精神却是不错的,穿着一件老年中山装外套,里面露出洗得有些发黄的衬衫领。大门外面,拆迁的队伍已经蓄势待发。莫正才站在昆明市郊宏仁村的老宅院子里,像一根倔强的火柴棒,随时准备战斗。莫荣也在院子里,他是莫正才的儿子,出生于1962年,也是当了爷爷的人。他比莫正才高出一头,体重超过170斤,长相上并不随父亲,一张长圆脸,下巴有点兜,肩膀壮实宽阔——虽然村里十多年前就没了耕地,但往日数十年田间劳作的印记依然在。
这一天是2020年10月10日。莫荣并不是来声援莫正才的,他从一进门就要求父亲答应拆迁。从2010年以来,这是他们父子间为数不多的话题。两个人嗓门都很大,气势上谁也不让谁。就在这时,58岁的莫荣当众向父亲莫正才的胸口打了一拳。这一幕被正在老宅做直播的高菲记录下来。她是昆明一所院校的老师,长期关注云南地界的老宅保护情况。她来到莫正才的家里,就是为了记录当天老宅被拆的过程,不承想却记录下这么激烈又有戏剧性的冲突场面。

石猫猫是村子里每家每户的必备品,从村里搬出后,人们会将它留下
莫正才的老宅是一座四合院,由其曾祖父修建于1915年,院子的空间并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被称为“天井”。天井里最显眼的是一棵六七米高的桂花树,底层树干笔直,伸到半空才发了枝杈。天井周围三面是木材搭建的房子,均为两层。房子的门窗上雕刻着花卉、叶子,还有神兽的镂空图案,斑驳、败落挡不住精巧、细致的韵味,能看出当时建造者的匠心。如果从上空看,会发现整个老宅的布局是一个四方形,方方正正像一颗印章的形状。也因此,这种建制被称为“一颗印”。
莫正才是这座宅子的户主。他和儿子莫荣之间的矛盾正是因为这座老宅。2010年,宏仁村被列入昆明市城中村改造计划名单,莫荣在父亲不答应的情况下,签署了同意拆迁老宅的协议。在这次冲突前,莫正才向官渡区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将村庄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和改造指挥部告上了法庭。他认为,儿子与拆迁办签订的协议没有得到他的授权,协议不应该生效。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认为,莫荣与案件密切相关,将其追加为第三人。在直播中能够看到,莫荣手拿一张传票,对着父亲喊:“你将我告上法庭……人老了要有老的样子。”
虽然自2010年宏仁村拆迁开始,村里不乏儿女和父母吵架闹矛盾的例子,也有年轻人当着众人的面辱骂父母,但像莫荣这样公开对父母动手的还是头一例,围观的人一脸错愕。这个尖锐、极端的行为背后,是一个村庄在过去10年里逐渐城市化的复杂历程。想要了解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还要从宏仁村说起。

老屋二楼是莫正才的书房和卧室,他喜欢看《民法典》
宏仁村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在滇池北岸,位于广福路和彩云北路的交叉口位置。前者是昆明最宽、最长的城市道路之一,连接昆明主城与呈贡新区;后者是昆明市投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城市道路工程。这两条道路都是2003年后修建的。2003年之前,宏仁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区域,拥有1700多亩耕地,种植粮食、蔬菜、花卉,被称为昆明市的“菜篮子”。2003年提出的“大昆明”总体规划,一步步结束了宏仁村作为农业村庄的历史。根据这个规划,昆明市一改曾经以五华区为中心的格局,用18年时间建设以滇池为核心的“一湖四片”的现代新昆明。届时,官渡区将作为主城区的一部分,原来的呈贡县将成为未来昆明市的政府机关所在地和大学城。
宏仁村就处在这两个区域的中间,宏仁村的村民将村庄的位置称为“肚脐眼”,连接着昆明市区和未来新城的城市大道。拆迁刚开始时,村民们几乎是热烈拥抱这个计划的。1998年修广福路时政府向宏仁村征地61亩;2005年广福路扩建,又征地113亩;随后,政府以建设新亚洲体育城住宅区和彩云北路的名义又划走了宏仁村686亩耕地;2008年以后,为了支持政府打造西南地区最大的商品批发交易市场——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宏仁村交出了村里最后的700亩耕地。没人对此激烈反对。
一位村民告诉我,征地补偿款并不高,每亩地只有12.6万元,由村集体扣除后,村民到手仅为5万元/亩。但作为交换条件,政府承诺将所得耕地纳入“规划红线”后,按照已征土地15%的比例,留给村民一块作为宅基地。扣除村里的公共建设用地后,这块占地260亩的土地被分割成503块,分给村民。另一点吸引村民的是,征地后的城市居民身份。以往,村民们成为城里人只有一个办法——考大学。宏仁村村民莫琳今年50岁,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他告诉我,1990年,整个官渡区只有他一个人考上本科。“那时,农民子弟要想出去,变成居民户口,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情。”莫琳对我说,他还记得亲戚邻居送行时说的话:“你有这个命,终于能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这些祖辈耕种在土地上的村民,早就希望摆脱与土地打交道的生活。“早些年大家都种菜,但菜价不高,一亩地也就收入两三千元。后来又种花,利润高了些,可风险也高,一切都随着市场走,有时候同一品种的花太多,就卖不出去,只能丢进垃圾箱。”村民老王今年60岁,家里以前有5亩地,他告诉我,种花那些年,每天晚上要修剪花,早上四五点钟他就要用电动三轮车将花拉到花市,有时候花都卖完了天还没亮,“那时日子是真的苦”。由于城市建设和修路的原因,宏仁村一带的农田水利系统相继被破坏,种田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这也是让他们诟病的事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晓阳当时在宏仁村做人类学调查,他记得村民们对他抱怨最多的就是,“地已经种病了”。
对于离开土地后的生计,村民们并不担心。新亚洲体育城和螺蛳湾商贸城建设以后,吸引了一大批外来务工人口,他们需要在附近村庄租房子。租赁经济已经在当时显现出庞大的市场潜力。在宏仁村村民的设想里,耕地被征收后,政府新划给的宅基地距离城市更近,在新宅基地上建好房子,也能走这样的模式。
文章作者


王珊
发表文章155篇 获得10个推荐 粉丝838人
哈哈,天下天鹅一样白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