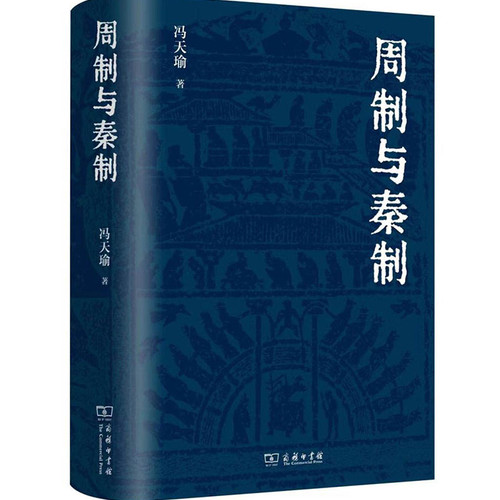“全球化”诞生的年代
作者:维舟
2018-02-03·阅读时长5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2930个字,产生6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 与他的著作《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 )
当今世界的重大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归根到底往往是经济问题——“全球化”便集这三者于一身。由于资本、物资甚至劳动力本身,都越来越趋于跨边界流动,因而现代工商业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国际性的,必须从全球视角才能予以正确认识。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么说:在这相互紧密联结的世界里,不同国家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整个体系的变化所做出的回应,因而仅将目光聚焦在一个局部的地方是不够的。
这并不是到今天才出现的新状况,而是自15世纪末大航海时代以来不断加速的现象。地理大发现不仅只是“一些白人跑到遥远的世界各地寻找财富”的故事,它也意味着在新的技术体系和经济结构下,各地的自给自足及其伴生的独立性自此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一条通往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的不归路,欧洲列强就像在一辆停下来就会爆炸的公共汽车上,必须在海外扩张才能确保不至于陷入自我毁灭。一如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所指出的,西欧各国“不得不或者组织、保护并确保世界性的供应基地,或者冒贫困并退返拙劣工艺的危险。……如果新生代技术经济要生存下来的话,只能让自己的工业和政策建立在国际化的基础之上,没有任何别的出路”。
这就是为何“塞尔登的中国地图”(原名《东西洋航海图》)会那么重要的原因——这份17世纪时最大的壁挂地图(长160厘米,宽96.5厘米)不仅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欧洲人对东亚的强烈兴趣,还证明了不知名的中国绘图者对东亚海域的了解。它因最初归英国律师约翰·塞尔登收藏而得名,但耐人寻味的是:塞尔登是出于对中国知识的兴趣而完好地收藏这份珍贵的地图,但他其实完全不懂地图上的汉字。1654年接受塞尔登这份捐赠的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在1604年首次开始收纳来自中国的手稿,但当时整个英国无人能识中文(话说回来,中国当时也无人懂英文),直至八九十年后,来自南京的中国基督徒沈福宗才翻译出了这部手稿,它自此成为英国研究东方学的重要文献基础。
文章作者


维舟
发表文章33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420人
涉猎驳杂,少时沉迷于古典文学与历史,长而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