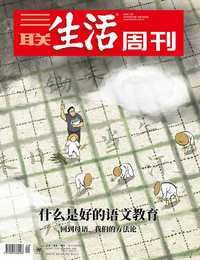现代诗歌:词汇试图打破的和创造的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2020-07-15·阅读时长11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892个字,产生189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诗人韩博在诗歌电影《哀歌》拍摄现场,上海皋兰路东正教堂遗址(戴长逸 摄)
文/韩博
母语的第一次震颤
我是一个没有方言的人,从小就生活在“普通话”的一马平川里。
我的爷爷奶奶是山东人,他们是参与建立新中国的革命者,作为军人从山东迁移到东北,后来一直以讲普通话来表达对革命的拥抱,我爸爸就成了一个只会讲普通话的人。我妈妈是一名老师,父辈是东北人,但她以讲普通话为自豪。普通话就像能在中国各地自由兑换的货币,它具备推动信息快速流动的契约基因。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趋政治口号化的普通话也近乎一种营房,其材料简省而流通迅速,更因发行超大面值语言货币——一句顶一万句——而形成掘地三尺的社会动员能力。
父母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一代。我读小学的时候,记得但凡跟他们住在一起,早上大抵会在广播声中醒来——父亲躺在床上收听电大课程,一个糯糯胖胖的声音,掰开了揉碎了解释《诗经》的句子。也许正是出于补偿心理,每个寒暑假,我都要被母亲逼着背唐诗,每天一首,过关之后方可看闲书,比如《水浒传》或《好兵帅克》。
作为“70后”,包围我成长的现代汉语,实际上应该算是汉语的现代简易住宅。它让我想起了包豪斯,尤其如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所言,“为收入最低的社会阶层提供最起码的栖身之所”这一社会理想映照之下的德绍多登住宅区,它体现出那一代建筑师追求形式服从功能、简化建筑语言的使命感。普通话有类似的功能,统一简化后的语言,大量使用标准化的预制构件,以便大干快上。它对于快速提高识字率功不可没,但与此同时,语言的历史河流被建起了大坝,汉语的丰富性受到不可避免的折损。
当我到了青春期,古诗背了不少,却感受到中国古诗程式化的一面。古诗里的固定意向很多,后人总是在重复前人的意象表达,真正有创造力的属于个人独特的感受很少。就跟水墨画一样——我涂抹了好多年,但是发现水墨画有非常固定的程式,所谓好的标准就是模仿古人。我忍不住开始到处搜寻“不一样”的读物。但即使这样,那时我认定古文也比白话文好,所以理解不了为什么要用白话文作诗。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
发表文章6066篇 获得7个推荐 粉丝47986人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