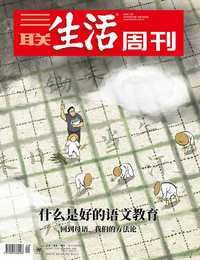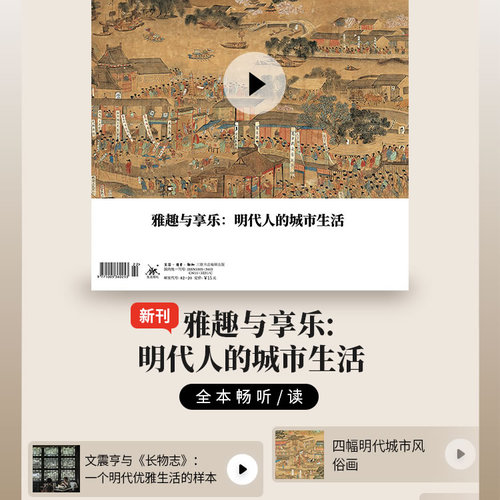高中语文:能否超越高考?
作者:丘濂
2020-07-15·阅读时长16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8120个字,产生449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高中是许多人最后一个系统学习语文的阶段
记忆中的语文课
因为这个选题,我和我的高中同学又凑在一起回忆了当年的语文课。我们所在的班有点特殊,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文科实验班,算是全国第一个得到教育部认可的文科实验班。2000年我们入学的时候,它还采取在全北京早于中考提前招生的方式获得生源。在这个30人的小班,从高一开始就有一系列教学设计鼓励大家在文科方向的发展。我的同学们,一致的特点是对文科都怀有浓厚的兴趣,有人极度偏科,有人理科成绩也并不差。总之,那时北京乃至全国都把“数、理、化”科目的表现作为区分学生的标准,文科实验班的存在就好像沙漠里的一片绿洲。
语文课无疑让我们有着生动的记忆。语文老师叫朱建军,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为人温和儒雅。我能想起第一节作文课,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让我们以此为题自由发挥。要知道数月之前,我在初中都还在练那种写人记事类型的传统记叙文,内容也经常是“我出车祸,妈妈献血救我”那种企图打动人的胡编。在不适应中我没能当场写出什么满意的文章,倒是记得朱老师赞赏的一篇叫做《一孔之窥》的作文,来自同学杭玫,讲一只王母娘娘的梳妆镜如何经过了密码锁、猫眼儿、镍币等几次变形后,最终成为一只教师的怀表。它让我开始琢磨应该把想象力用于叙事的“正道”,要放弃虚情假意的编造。
我还能想起朱老师讲语文书第一课《荷塘月色》,没有像初中那样针对课后习题一道一道给出答案,而是开放性地提问大家最喜欢文章中的哪个部分。一位同学说他觉得文章结尾很妙,“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生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这句,因为那让宁静的氛围一直延续下去。朱老师表扬了他,说那是他从未注意过的地方。
我的同学刘子超还记得在学校遇见朱老师的时候,他的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与课本无关的“闲书”,那似乎也是一种提倡学生进行课外广泛阅读的暗示。让他至今还会想起的是每周都要完成的札记,一种独立于课堂作文之外更为随意的训练,文体、内容和题目统统没有任何限制。他期待打开本子后去看朱老师清秀楷书写下的批注,也盼望着班里其他几位热爱创作的同学交换本子互看,那成为一种相互比试较量的激励。他现在是一名作家,刚刚完成一本中亚游记的写作出版。他把自己对写作的热忱和创作的自律归于高中时代这种“札记”机制的唤醒。
另外一位同学黄海,对语文课开头十分钟的“信息交流”难以忘怀。在那个环节里,会有同学轮流登上讲台分享最近正在阅读的书、听的音乐或者看的电影。他认为那非常具有仪式感,因此作为少年的他总会想着要精心准备,要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做一些有趣的事情,能给大家带来新鲜的观点。也是在这个过程里,他找到了比纸上文字更适合他的表达媒介。他和我回忆,有一次朱老师的语文课正赶上北京电影学院的独立影像展有片子放映,于是他尝试着和朱老师请假前往,没想到老师欣然同意。黄海在高中毕业前就打定主意要当编剧,大学毕业后也就顺利地进入了这个行业,如今已经是资深编剧。
以高考成绩来衡量,我们班的表现相当不错。那年北京市的高考文科状元阎天就出自我们班,考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也达到了16人。不过高考只是人生的节点,不是全部。后来大家的职业有作家、编剧、导演,也有学者、编辑、记者,大多数人都选择在人文社科领域继续自己的探索,而那些好奇心的种子,就在高中课堂上埋下。我们倾向于用开放、自由、包容、多元、思辨、跨媒介等等词语形容对当年语文课的印象。当课堂上那些具体课文的字词句已经淡忘,这些对我们的思维和认知仍旧有着启迪。
文章作者


丘濂
发表文章128篇 获得28个推荐 粉丝1490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毕业于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专业。美食、传统文化和城市话题爱好者。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