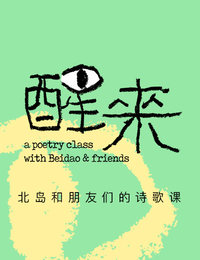北岛 | 特朗斯特罗默《写于1966年解冻》:诗与友谊
作者:北岛
2020-06-26·阅读时长8分钟
 伟大的诗歌如同精神裂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隆隆回声透过岁月迷雾够到我们。诗歌让我们醒来。
伟大的诗歌如同精神裂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隆隆回声透过岁月迷雾够到我们。诗歌让我们醒来。
——北岛
我现在口语也不太够,我一般都是要笔谈的。我自己不断地说明我自己中风,当时语言障碍专家跟我说过,说实际上我的50%不可能变化,后来我找了七八个大夫,这么多年一直在治疗,在恢复过程中,聊天还凑合,实际上在朗诵过程中每一个词咬得不准就会有问题,我能把它读下来就很不错了,但是我是其实语言真不够。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北岛,今天,我跟大家谈一首瑞典诗;《写于1966年解冻》,作者是我的好朋友,名字叫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我想讲的主题是:诗与友谊。
 瑞典文原诗:
瑞典文原诗:
Störtande störtande vatten dån gammal hypnos.
Ån översvämmar bilkyrkogården, glittrar
bakom maskerna.
Jag griper hårt om broräcket.
Bron: en stor fågel av järn som seglar förbi döden.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ömer)是瑞典诗人,被公认为自二战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职业是心理学家。一生中写下两百多首诗,被译成60多种文字。1990年年底,他患脑溢血导致半身瘫痪,失去了语言能力,仍坚持写作。2011年特朗斯特罗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他以凝炼、简洁的形象,以全新视角引领我们接触现实”。
特朗斯特罗默生于1931年4月15日。他的父亲是记者,母亲是教师,父母离异后,他伴随母亲,度过童年和青少年。他就读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心理学系,后来成为一所青少年拘留所的心理医生。他16岁开始写诗,《果戈理》写于18岁,收入在《诗十七首》的第一本诗集里。
1983年,我是托马斯的第一个中译者,其中的六首诗首次发表在1984年的《世界文学》杂志上。1985年4月,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们终于见了面。那天,我陪他去长城。在《蓝房子》的散文中,我这样写道:“那天托马斯很高兴,面色红润,阳光在他深深的皱纹中转动。他触摸那些城垛上某某到此一游的刻字,对人们如此强烈地要被记住的愿望感到惊讶。我请他转过头来,揿动快门。在那一瞬间,他双手交叉,笑了,风掀起他开始褪色的金发。这张照片后来上了一本书的扉页。那书收入托马斯诗歌的各种译文,包括我译的那几首。”
紧接着是1985年夏天,我第一次到瑞典,我和托马斯续上友谊。他有一栋祖传的小别墅,被称为“蓝房子”,坐落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小岛上。借用此名,我写下一篇关于他的散文,书名为《蓝房子》。
1990年年初,我获得瑞典笔会文学奖,用奖金居住在斯德哥尔摩,住了八个月。他们夫妇住在另一个城市,离斯德哥尔摩不远,我们常来常往。1990年8月我搬到丹麦的第二大城市,在奥胡斯大学教书。
我在《蓝房子》一文中写道:“11月初,我在丹麦奥胡斯刚落脚,托马斯就跟过来朗诵。我像傻子一样,坐在听众中间,现在想起来,那是天赐良机,在托马斯即将丧失语言能力以前,他嗓子有点儿沙哑,平缓的声调中有一种嘲讽,但十分隐蔽,不易察觉。他注重词与词的距离,好像行走在溪流中的一块块石头上。”
1990年12月,得到托马斯中风的消息,我很难过,写了这首诗给他,题目是《致特朗斯特罗默》》莫妮卡说他看完掉了眼泪。
“你把一首诗的最后一句/锁在心里——那是你的重心/随钟声摆动的教堂的重心/和无头的天使跳舞时/你保持住了平衡”
我接着写道:“1991年夏天我来看望他们,托马斯显得惊慌而迷惘。他后来在诗中描述了那种内在的黑暗:他像个被麻袋罩住的孩子,隔着网眼观看外部世界。他右半身瘫痪,语言系统完全乱了套,咿咿呀呀,除了莫妮卡,谁也听不懂。只见莫妮卡贴近托马斯,和他的眼睛对视,解读他的内心。她也常常会猜错,托马斯就用手势帮助她。比如把时间猜成五年,手指向右增加,向左减少,微妙有如调琴。‘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在托马斯和莫妮卡的现实中是真的,他们跨越了语言障碍。”

在瑞典也有诗江湖。托马斯是一个优雅而温暖的人,既沉静又幽默。在历史潮流的裹挟下,要敢于面对自己。“六七十年代,不合时代潮流的托马斯受到同行们恶狠狠的攻击,骂他是‘出口诗人’、‘保守派’、‘资产阶级’。记得有一次我问他生不生气。托马斯说:‘我倒想说不,可我能不生气吗?’如今时代转过身来,向托马斯致敬。莫妮卡告诉我,前不久,他俩去斯德哥尔摩美术馆,被一个导游认了出来,他大声向观众们说:‘这是我们的托马斯!’全体向他们鼓掌。”
他中风后,我们常来常往,甚至绕道专程去看望他们夫妇俩。2011年早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参加诗歌节,结束后我乘夜船从塔林到斯德哥尔摩,住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我和托马斯夫妇一起前往“蓝房子”,在那儿住了三四天。我和莫妮卡一起做饭,陪他在小花园晒太阳,晚饭后我们一起听古典音乐。我和莫尼卡商量,下个月给他过八十岁生日。谁都没想到,他的生日礼物是诺贝尔文学奖。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在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仪式上,莫妮卡代表他接受简短的受奖词,借用他的一首短诗,用英文和瑞典文朗诵了《自1979年3月》:
厌倦了所有带来词的人,词并不是语言,
我走到那大雪覆盖的岛屿。
荒野没有词。
空白之页向四方展开!
我发现鹿的偶蹄在白雪上的印迹。
是语言而不是词。
在1990年8月4号,我和李笠一起乘船去“蓝房子”作客。李笠向托马斯提问,我正好在场。我摘选了访谈中托马斯的要点:
问:你认为诗的特点是什么?
答:凝练。言简而意繁。
问:你的诗是否和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
答:我的诗深受音乐语言的影响,也就是形式语言、形式感、发展到高潮的过程。从形式上看,我的诗与绘画接近。我喜欢画画,少年时我就开始画素描。
问:你对风格是怎么看的?
答:诗人必须敢于放弃用过的风格,敢于割爱、消减。如果必要,可放弃雄辩,做一个诗的禁欲主义者。
问:你的诗,尤其早期的诗,试图消除个人的情感,我的这一感觉对不对?
答:写诗时,我感受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不是我在找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现它。完成一首诗需要很长时间。诗不是表达“瞬间情绪”就完了。更真实的世界是在瞬间消失后的那种持续性和整体性,对立物的结合。
在《蓝房子》接着写道:“托马斯给我看了他刚刚完成的诗作《上海》(题目后来改成《上海的街》)。开头两句是:‘公园的白蝴蝶被很多人读着。/我爱这菜白色,像是真理扑动的一角。’这意象来自他上海的经历。从北京到上海,没人陪同,使馆要他把所有发票都保存好。发票多半是中文的,他正着看倒着看都没用。那上海闲人多,估摸这奇怪的动作招来看热闹的,于是发票变成了白蝴蝶,被很多人读着。”
他写作的高峰时期,一年平均三四首短诗,反复修改。其中一首短诗花了七年的时间。这就是他所说的,完成一首诗需要很长时间,他特别强调的是,在瞬间消失后的那种持续性和整体性。
最后,我想试图阐释这首短诗,只有五行。
写于1966年解冻
淙淙流水;喧腾;古老的催眠。
河淹没了汽车公墓,闪烁
在那些面具后面。
我抓紧桥栏杆。
桥:一只飞越死亡的巨大铁鸟。
这首短诗只有五行,却写得惊心动魄。开篇时相当宁静:淙淙流水;喧腾;古老的催眠,用流水声勾勒出冰雪消融的景象,声音成为动力推动着诗继续向前:河淹没了汽车公墓,闪烁/那些面具后面,如果说第一行是声音的话,那么第二三行是画面,在这画面中出现了不祥之兆:汽车公墓和面具,汽车公墓即废车场,面具即报废的汽车。自然意象和工业文明的意象在这里交汇,且在一种相当负面的阴影中。接下去,我抓紧桥栏杆,叙述者终于现身¾在桥上。动作的突然性构成了紧张,暴露了叙述者的内心恐惧¾桥:一只飞越死亡的巨大铁鸟。这是个多么强烈的意象,首先在于其准确生动,再者充满动感而更紧迫更具威胁性。桥,这工业文明的象征竟意味着死亡。全诗从淙淙流水到桥,从缓到急,从和平到死亡,从古老到现代,戛然而止。
托马斯自己说过:“我的诗是聚合点。它试图在被常规语言分隔的现实的不同领域之间建立一种突然的联系:风景中的大小细节的汇集,不同的人文相遇,自然和工业交错等等,就象对立物揭示彼此的联系一样。”他谈到他的创作过程时说:“我常常从一个物体或状态着手,为诗建立一个‘基础’。这基础有时是一个地点。诗从一个意象中渐渐诞生……我用清晰的方法描绘我感受到的神秘的现实世界。”
按托马斯的说法, 那是从流水开始,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建立一个所谓的“基础”,那是一个地点。这首诗的题目是《写于1966年解冻》,既是日期,也是地点,合二为一,而留下稍纵即逝的痕迹。流水从解冻中引出主题,构成主题与变奏。结尾突兀,令人震惊,可谓诗中上品。
在托马斯中风前不久写下回忆录《记忆看见我》,关于他的童年和青少年的记忆。开篇这样写道:“‘我的一生。’一想到这词句,我就在眼前看见一道光。再细看,它形如有头有尾的彗星。最明亮的终点,是头,那是童年时代及其成长。核心,最密集的部分,是幼年,那最初的阶段,我们生活最主要的特征已被决定。我试图回忆,试图从中穿越。却很难进入那密集的领域,那是危险的,好象我在接近死亡本身。彗星越往后越稀疏¾那是较长的部分,是尾巴。它变得越来越稀疏,却越来越宽。我现在处于彗星尾巴相当靠后的部分,我写下这时我六十岁。
我们最早的经验是最难以接近的部分。复述,关于记忆的记忆,突然照亮生活的情绪的重建。”
接近于他的岁数,我也写下一本关于我的回忆录《城门开》,也是关于童年和青少年的记忆。写作往往追溯到每个人的童年,即生命的源泉。那是人类的神秘的通道,尽管历史,国家和语言完全不同,而个人经验和内心的秘密互相勾连。他中风时近六十岁,他因左脑溢血偏瘫,失去了语言能力;我62岁中风,因右脑溢血,不过我的运气还好。这两个人有着某种对应关系。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于2015年3月26日去世。我从香港去斯德哥尔摩专程参加他的葬礼。葬礼订于4月28日下午两点钟,在老城王宫旁的大教堂。在牧师弥撒的仪式后,每个人带一支玫瑰,缓缓排队向他致敬,把玫瑰放在棺柩前。那一瞬间,我喃喃低语,却不知道想说什么。打开沉重的教堂小门,阳光明媚,水仙花幽然开放,在大教堂的小花园里,孩子们正在画画。生活在继续。
我们的友谊,自1985年4月起,整整三十年了。
后天晚上,莫妮卡请我和几位老朋友在家小聚。自从中风后,他每天都用左手弹琴,为在场的朋友们演奏。三角钢琴静静靠近阳台的窗口,打开键盘盖,乐谱放在支架上,弹琴的人永远不在了。
转发海报分享
北岛和朋友们的诗歌课

文章作者


北岛
发表文章40篇 获得48个推荐 粉丝220人
著名诗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