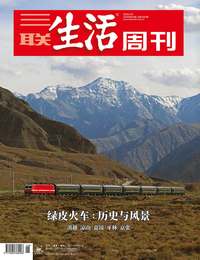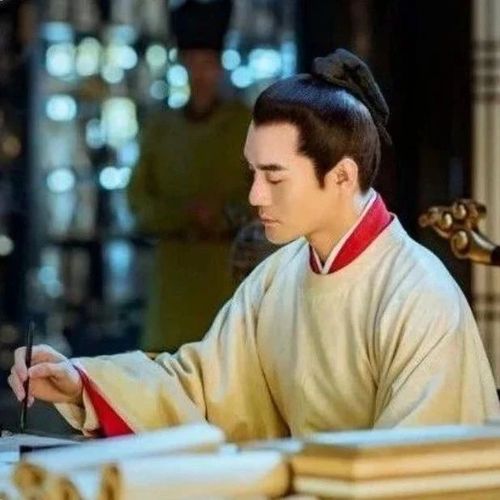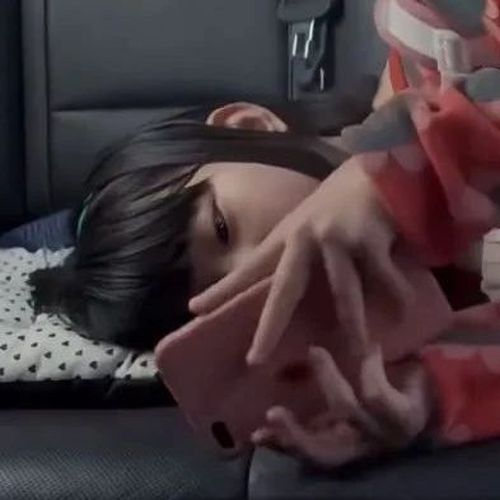牙林线,通往森林深处
作者:艾江涛
2020-06-24·阅读时长14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7269个字,产生47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牙林线上的秋天虽然短暂,却最为绚丽,乘一列慢火车,徜徉在层林尽染的林海深处,足以让人忘却时间(王璐 摄)
摄影/黄宇
森林的诱惑
一到呼伦贝尔,天空立刻变得高远起来。在内蒙古狭长的地图上,这里以绵延不绝的大兴安岭林区而闻名。整个大兴安岭林区,位于内蒙古东北部与黑龙江西北部,全长约1400公里、宽约200公里。最初将这片森林秘境与外部世界相连的,是沙俄1896至1903年修建的中东铁路。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以及八十多公里外的牙克石市,都是这条从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干线的重要站点。
从牙克石往北,经伊图里河、根河到达满归,全长约446公里的牙林线才是唯一一条真正深入大兴安岭北脉腹地的铁路。与铁路的习惯命名不同,“牙林”二字,“牙”指牙克石,“林”则指大兴安岭林区。与之相仿,还有与大兴安岭相系的博(克图)林线、嫩(江)林线。单从名字,我们也不难发现这条林区铁路的特殊性:以林场为龙头向茫茫林海铺设铁路的初始,其终点站常难以确定。
这条因林业而兴的铁路,历经沙俄私营铁路、伪满中长铁路到新中国森林铁路的整个历史,从1966年全线通车,直到2015年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全面禁伐之前,一直承担着共和国木材运输的大动脉。2015年之后,这趟森林铁路继续维持客车运营,成为铁路迷心中经典的慢火车线路。在Lonely Planet新版的《惊奇火车之旅》中,牙林铁路便作为中国火车旅行的代表线路而入选。
一切的吸引,来自于那片森林。每年秋天,大兴安岭都会迎来大批自驾游者,但很少有人知道,你其实只需要花费几十元,就可以坐火车深入大兴安岭腹地,体验森林中一年四季的美妙风景。
受北京突然暴发的疫情影响,我们在到海拉尔两天后才登上这趟从海拉尔发往满归的4182次列车。火车到了牙克石,可算要“进沟”了。
过了牙克石,铁路与滨州线分开,徐徐向东北方向延伸。与铁路如影随形的是海拉尔河,这条河一直蜿蜒到牙林线的岭南站以北。伴随连绵不断的大兴安岭,铁路线所设立的站点,多是依河而居的市镇,诸如图里河、伊图里河、金河、根河、牛耳河,数不尽的河流与森林。出发前,海拉尔车务段技术科科长张洪巅向我介绍呼伦贝尔“三分天下”的地貌:博克图到扎兰屯一带,基本属于农区;牙克石往西到海拉尔到满洲里,属于牧区;沿着牙林线,牙克石往北走,是林区。
尽管已是林区,但图里河往南,基本属于草原向森林的过渡地带。早晨七点左右,过了汇流河小站,树木开始多起来了,一团团落叶松出现在草地上,不时可见点缀其间的牛羊,草地上各种野色的花开得正好。偶尔,你还能看到草地中间新垦出来的一块田地,种些土豆油菜之类的作物。
列车长张所有,就出生在这条线上一个叫艾林的小站。已在这条线上跑了15年的他,对铁路两旁的景色最为熟悉不过。“春天来的时候,漫山遍野全是达莱香,就是映山红,兴安岭杜鹃花。夏天这个季节,打开窗户,都是绿色,从根河开车以后,刮进来的空气都是松香味。秋天各种颜色的叶子,有变红有变黄的。冬天到处都是大雪,树上挂着雪挂,尤其二三月份刚近暖的时候,上面挂一点小冰溜,是最好看的。”

牙克石站处于牙林线与滨州线交汇处,火车站一旁的木制水塔,由俄国人在1903年修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林区铁路建设,一大批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建设者来到这片林区。他们当年的心情,大约可从曾在这里下乡插队的作家乔雪竹笔下感受一二。在80年代发表的小说《北国红豆也相思》中,她这样写道:“火车在牙林线上行驶,牙林线在大兴安岭中蜿蜒伸展,当它伸展到大兴安岭的深处,也就伸展到了秋天的深处。大兴安岭的秋天是短暂的,仿佛是头一阵风把它吹来,而下一阵风就又要把它吹走。于是它就毫不吝啬地用最鲜明的颜色铺泻着山林:浓绿旁边勾勒上淡黄,淡黄上面点染上桔红,桔红上面涂抹着深紫,最后索性是大片的黄,无涯的黄,阳光的色泽,金子的色泽,就像海潮铺泻在沙滩上一般,铺泻在大兴安岭上。”
尽管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仍不难想象,那些初到这里的年轻人一定同样为小说中所描绘的如诗如画的森林所蛊惑。王宇新是《林海日报》的资深记者。1963年,他的父亲在北师大毕业后,被林业部直接招收到牙克石林业中学教书。“我们这边林业单位的人有两个特点,一些是学校里面的积极分子,还有一些是家庭成分不好的。我父亲在学校就入了党,属于前者。”王宇新说。后来在编写林区材料时,他发现那时从全国各地过来好多大学生,1953年最早过来的一批大夫中,就有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原型吴石将军的女儿吴兰成。由于这些年轻大学生的引进,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牙克石的教育、医疗水平,要远高于呼伦贝尔其他地方。
1958年,国家开始大规模开发建设大兴安岭,在牙克石林业管理局下,一口气设立了8个林业局。同年,大批从朝鲜战场撤回的战士,成建制转业分配到各林业局。随后三年困难时期,林区工人又带过来好多在家乡吃不饱饭的人。“别看这个地方冷,种粮食不行,土豆产量可以,只要勤快,开块地就能活下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其他地方比,这边能吃上饭,很有吸引力。”王宇新说。
几次大的移民涌入,为林区开发带来活力,也在整个林区形成一种移民文化加民族文化的森工文化。所谓民族文化,是因为林区一直生活着两支人数极少的少数民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林子边上还生活着达斡尔族,额尔古纳河边还有一支华俄后裔。
新中国成立初,百废待兴,无论是铁路枕木、房屋大梁,还是电线杆子、煤矿撑架,都要用到大兴安岭的木材。林区工人生活非常辛苦,正如当地流传的俗语所描述:“吃水用麻袋,开门用脚踹”“五荒六月吃干菜,一间小屋三代住”,可在那个年代,林区依然是一派热火朝天、生机勃勃的图景。
1980年之前,林区的木材生产,完全为支援战争需要和国家建设,严格按照调令生产运输。1980年开始,国家对林区实行统配材与非统配材相结合的“双规制”,林区完成计划任务外,还允许自己在市场销售。林区也因此迎来了最后的辉煌,王宇新至今记忆犹新:“80年代这边好到啥程度?大米成麻袋往家拿,到冬天半拉猪、一只羊、三四十斤牛肉,都是林业局分的。”
衰落的迹象出现在80年代后期。一方面,经过几十年开采,优质森林资源开采殆尽;另一方面,钢筋水泥材料对木材的大量替代,使得市场需求萎缩。随着满洲里口岸的开放,来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优质木材,进一步冲击着林区的木材市场。张洪巅回忆,“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将近20年,满洲里口岸每天要从俄罗斯进口十几列火车木材。”
文章作者


艾江涛
发表文章131篇 获得17个推荐 粉丝679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