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些“坏女孩”到30岁都成了“好女人”?
作者:宗城
2018-03-08·阅读时长6分钟
在中国,广义的女性文学写作能追溯到五四时期,茅盾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中的《导言》指出,1921年5—7月三个月间,刊载于各类杂志的新小说有115篇,其中爱情小说有70篇,农村生活只有8篇,城市生活的3篇,家庭生活9篇,学校生活5篇,社会生活的计20篇,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实在乃是描写了男女关系”。民国时期,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张爱玲的《传奇》短篇小说集,还有茅盾笔下的孙舞阳、曹禺刻画的陈白露等,都可作为早期大陆女性文学的样本。而狭义的女性文学(也称女性主义文学,后文的“女性文学”皆指向狭义概念),往往是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陈染、林白、铁凝、王安忆、卫慧、棉棉、廖一梅和海男等作家为代表所掀起的女性文学写作风潮,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作家张洁于197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
1986年,当波伏娃的代表作《第二性》被引入国内时,出现了一件尴尬的事情:出版社为了迎合市场,将原书第一部分“女性主义理论历史”删掉,只保留了第二部分“女性身体和心理的发育演变史”,毕竟,对大多数好奇者来说,第二部分显然比第一部分更能满足他们对女性的“猎奇感”。“女性文学”写作也出现同样的尴尬。《“女性文学”:繁荣背后的危机》一文写道:“女作家试图通过写身体获得女性表达的权力,引来的看客却只对女性身体感兴趣,至于女性地位,几乎没有改变。如果说有所改变的话,仅仅是女性把对自己身体的发言权“夺”了回来,写出的“身体”更加真实与暴露,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进步”。”但这只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大陆女性文学写作的第一重尴尬,除了“身体写作”的怪圈,大陆女性文学还面临第二重尴尬,那就是,这些文本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往往都敌不过岁月的冲刷,文本中特立独行,彰显新时代女性特色的人物,被局限于一定的年龄阶段,而过了这个阶段,她似乎又会返回传统。她们往往是“坏女孩”,却无法坚持为“坏女人”。
之所为为“坏女孩”打上引号,是因为她们的坏,是基于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主流写作的视角。如果说以珊珊、梁倩、荆华、柳泉等为代表的早期女性文学文本所塑造的形象还相对保守,更侧重于彰显人格觉醒,那么陈染、林白、卫慧等人笔下的女性形象,就在与传统女性形象的对立上走得更为决绝。《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是“一个残缺的时代里的残缺的人”,“她不过是长了一张敏感而偏执的脸孔”;《上海宝贝》中的倪可(CoCo),流连于假面舞会、高级休闲交际会所、酒吧、歌厅,肆意宣泄自己的欲望,在小说中一出场,她就说:“每天早晨睁开眼睛,我就想能做点什么惹人注目的了不起的事,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如绚烂的烟花噼里啪啦升起在城市上空,几乎成了我的一种生活理想,一种值得活下去的理由”;而《一个人的战争》中的“我”,童年就已经“喜欢镜子,喜欢看隐秘的地方......在单独的洗澡间冲凉,长久地看自己,并且抚摸”,甚至认为看人生孩子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诚如刘剑在评价陈染笔下的“城市边缘人”时所说:“90年代知识女性在文学中的形象,更接近于文艺青年,蔑视主流价值观,徜徉于幻想世界。她们叛逆、忧郁、感伤。有着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切前兆,蔑视那些容易和生活妥协的人。”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坏女孩”和“坏女人”的区分,自然不是以成年与否为划分,如果硬要有一个划分界限,不妨以结婚与否做区别。梅艳芳的歌迷看到“坏女孩”的称法,肯定会联想起那首同名歌曲《坏女孩》——“没有办法做乖乖,我暗骂我这晚变得太坏。”有趣的是,当我们翻阅八十年代中期后那些女性文学文本所刻画的“新女性”时,我们会发现,她们“变得太坏”也往往是在婚姻之前。
《一个人的战争》中,围绕女主人公的叙事从“在幼儿园里,五六岁”开始,一直到三十岁,“我”一度渴望和爱的人结婚,所爱之人却是个不婚主义者,结果,“我不要孩子了,也不要结婚”;《私人生活》中的刻画的倪拗拗,叙事主要围绕的也是她在“学生时代”的内心独白;《上海宝贝》中的倪可,“还只有25岁”,作者描写了她与与中国男友天天、德籍男友马克的恋情,但最终天天因吸毒死亡,马克返回德国,倪可则在葬礼时不断问自己:“我是谁?”;而《悲观主义的花朵》中,“第一次见到陈天,我差三个月满十八岁”,“八年以后,我和他第一次上床的时候,他对我的印象还是那个稚嫩幼小,没有发育好的小女孩”。少女、女孩,这就是女性文学写作者创作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她们笔下的“新女性”设定的年龄阶段,一切的反叛、幻想、特立独行、自我的反思乃至性的张扬,都发生于未婚前的阶段,似乎以结婚为标志,她们阅尽沧桑、看清世事,也意识到对现实妥协的必要性,她们是成长了,却也消解了自己反叛的勇气。讽刺的是,兜兜转转,她们的未来,与自己不吝笔墨讽刺的形象,何其相似。
事实上,我们回到文本之中,就会发现作者已经在字里行间给予了我们这种转变(或者说后退?)的暗示。《悲观主义的花朵》中有这么一段:“我们从年轻变得成熟的过程,不过是一个对自己欲望、言行的毫无道理与荒唐可笑慢慢习以为常的过程,某一天,当我明白其实我们并不具备获得幸福的天赋,年轻时长期折磨我的痛苦便消逝了。”曾经写出过长篇小说《糖》的棉棉后来也说:“八年以后的现在,我依然生活在上海,爱情依然在别处,而我依然爱着那些赤诚的才华横溢的朋友,我有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女儿,并且成为一个佛教徒。”
同时,我们回到那些文本的结尾,无论是作者的叙述语言,还是那些承载着“新女性”们强烈欲望的对象,它们最终却总是走向灰色、走向怀疑,甚至是抹杀与否定。《糖》的最后一章,棉棉写道:“无论我怎么努力,我都不可能变成那把酸性的吉它;无论我怎么努力更正错误,天空都不会还给我那把我带上无空的嗓音,我失败了,所以我只有写作”;《上海宝贝》的结尾,马克离去,天天死了,我怀疑自己的身份;《悲观主义的花朵》,陈天最终也死了,“我”恍然大悟陈天那个从未露面的女友是谁,竟然是比自己还要小五岁的女孩沈雪;《私人生活》的最后一章的名字则值得玩味——孤独的人是无耻的,阅读文本,最孤独的人恰恰就是敏感而偏执,对自己的身体有强烈好奇的倪拗拗;而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我”打掉了孩子,放弃了结婚,最终换来了什么?他远去了,“我想我此生再也不要爱情了。我将不再爱男人,直到我死。”
《陈染女性形象的现代性建构》一文提到:“按照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的观点,现代是一种与古代相对应的概念,“‘现代’主要指的是‘新’,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求新意志’——基于对传统的彻底批判来进行革新和提高的计划,以及以一种较过去更严格更有效的方式来满足审美需求的雄心。”如果我们将80年代中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写作所刻画出的鲜明形象,如倪拗拗、倪可等,定义为不同于过往的“新女性”,一个尴尬的事实是,作者在不予余力地渲染她们的与众不同时,却又在最后给她们毫不留情“补上一刀”,她们的“坏”,不但没有能带给她们长久的快乐,反而使她们滑向痛苦的深渊,在欲望的洞窟中一个人不被理解地自白。她们最终或是选择结束“坏女孩”,成长并归入“旧女性”,或是永远在路上,可我们似乎在这条路上看不到希望,只看到这些新女性求救般的“呓语”。由此,我不禁产生一个问题——这些女性文学写作者是否坚定自己的主张?还是说,其实她们也和自己笔下的女主人公一样“在路上”,她们在内心尚不能认同“坏女孩”能延续到“坏女人”?
就像学者刘卫东说的:“我想看到瑞典影片《永远的莉莉亚》里莉莉亚的毫不妥协。但是我也理解,我们的文学中(尽管是虚拟的文学)少有决绝的思想,也少有决绝的人...”也许,倪可们之所以无法决绝,“坏女孩”之所以无法冲破年岁的束缚,根源还在于书写者们自我的矛盾,一如卫慧在《上海宝贝》的后记中说的:“我不知道这本书的最终命运会被引向何方,但我知道它一旦完成,就会走出我的视野,不再由我控制...”
只是,这样的矛盾,不免让女性文学在一次次重新审视中,始终跳不出尴尬的境地。
文章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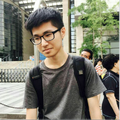

宗城
发表文章15篇 获得7个推荐 粉丝105人
云在青天水在瓶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