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攒下25万,名校毕业的00后女孩决定去加拿大小镇打零工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1-29·阅读时长21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经过两年的探索,李雪雪也在慢慢确认,她的选择不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而是一种目前对她来讲可持续、又能回应内心需求的工作与生活方式。
以下是她的讲述:
口述|李雪雪
记者 | 佟畅
编辑 | 王珊
困惑
我生活在多伦多,已经做了两年自由职业者。从2023年大学结课开始,我辗转于加拿大各地的偏远小镇、海岛打工,这些工作大多包食宿,我陆续攒了5万多加币(约合人民币25万元)。这个钱都没有达到一个普通全职工作者的平均年薪,但已经足够我生活。

《鬼怪》剧照
我租住在一个来加拿大生活多年的中国家庭里。房子位于多伦多的郊区,周边都是安静的民宅,有不少印度人住在这里,阳光好的时候他们会在公园草坪上野餐、烧烤。步行十多分钟,才能到商业区。家里男主人是个卡车司机,不常回来,我和女房东相处得很好,有时还帮她接送孩子。我的卧室在二楼,租金比市价收得低。房间不大,窗边靠墙摆着一张小床,对面是一张书桌,门边是柜子和衣橱。不工作的时候,我就在屋里做钩织手工、看剧,或是外出运动、去图书馆学法语。
最近我在做一份零工,到独居老人家里铲雪、扫落叶,或是入户简单打扫,每次工作一小时左右。我还在社交平台上接“陪伴师”的单子,陪附近的女性客户外出问诊、散步、拍照、聊天,或者分享一些我的技能与经验。她们大多很孤独,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难以交到朋友,有的人会参加社交活动,但没有机会谈心。比如有一个客户说自己有三个月没出门和人交流了,叫我到她家吃一顿她做的饭。

李雪雪曾打工生活过的地方(受访者供图)
这样松散和闲适的生活状态,与我刚来加拿大那几年截然不同。我是高二独自一人来到加拿大温哥华的,父母说是为了让我见世面——他们对我的期待和我的目标是进入名牌大学、入职大公司。我住在一个教育局随机匹配的寄宿家庭。那时我才17岁,从来没有出过国,甚至没有独自旅行过。
照顾我的是一对来自江苏的夫妻,这对夫妻是“老移民”,活得努力又谨慎,正职工作以外还在家里开补习班,家里接收了三个留学生。他们来机场接我,但又说接我是他们“义务之外的事”。自此我就有种寄人篱下的感受。他们还提醒我们不要踩邻居白人家的草坪,会被骂。女主人在餐食上也苛刻,早餐是夹了一片芝士的面包,午餐是前夜的剩饭。平时我尽量不打扰他们,却被女主人指责说我冷漠、疏离。

《九部的检察官》剧照
后来我换了个家庭,一开始相处得很好,不过女主人在怀孕后开始对气味敏感,非说闻到我身上有“老人味”,不喜欢我。后来又换了一家寄宿家庭。我那时痛苦而孤独。刚来加拿大,我对如何坐公交车、如何选课都不熟悉,没人能教我,一切只能靠我自己摸索。但这些东西,我不知道该跟谁说。我认识一些中国留学生,我们会一起出去玩,却不会倾诉这些话题。父母我更不指望。他们一直对我期望很高。我初中时一度为青春痘长了满脸而困扰,他们叫我不要管,专心学习。我想他们也接受不了我因为在寄宿家庭受委屈而回国。那段时间,学校老师判断我有抑郁的倾向。
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自己的日程填满。从小我就是这么做的。在温哥华,下午3点钟放学后我到图书馆学习、做兼职、义工,尽量晚回家。后来我申请到了多伦多大学,主攻统计学、辅修心理学。身边的同学都很“卷”,留学生的压力尤其大。我参加过不少教育机构举办的讲座,都在强调大学期间要尽早实习,为日后申请“永居”做准备。从大一开始我一边上课一边实习,做过市场、咨询类的工作,还给心理咨询平台写公众号文章。我的社交也几乎都围绕着为了给工作增添人脉而展开。一切都是为了让简历更好看。

李雪雪在加拿大生活时看到的景象(受访者供图)
直到大二的暑假,像是写定的乐章滑入一个意外的音符,我第一次看到生活不同的可能性。我到意大利读暑校,开始尝试在周末独自去附近的城镇旅行。惴惴不安地坐火车启程,遇到过种种突发情况,错过末班车,走夜路,遇到看起来危险的流浪者,这些既往生活鲜有的经验每次都让我觉得恐惧、庆幸,回家后却又兴奋。有一次我在佛罗伦萨的一座桥上看日落,夕阳即将沉入湖水,桥面上聚集着形形色色的路人,一个人在弹吉他,其他人自然地跟随着音乐舞动身体,暖黄色的余晖在他们身上勾起轮廓,所有人看起来都是那么自在和纯粹。我在一旁看了一会,眼泪不自觉地就流了下来,有人上前关心我,拉我一起跳舞,叫我“别哭了,开心一点”。
回去后我时时回味起那个黄昏,意识到自己一直都在埋头苦干,只有那个时刻真正感受到了世界。我开始试着让自己慢下来,享受阳光与大自然,不再每天冲着去图书馆。但父母、身边人不时的询问,还是会把我拉回到现实。
生活的“实感”
2022年11月,怀揣着“看世界”的愿望,我第一次尝试“打工换宿”,去了加拿大东南部的一个偏远农场里,连网络都没有。30个从世界各地而来的人生活在这里,有夫妻、情侣,也有老人和孩子。他们穿着自己做的相同样式的衣服,晨间一起唱歌、跳舞、诵读圣经,之后在农场劳作,还在城里经营一家非营利餐厅。工作并不劳累。我和他们聊起这几年上学、实习的疲惫,说起在学校里我和室友很少交流,甚至很难碰面,自己为人际关系而困扰。农场里的人说很心疼我。在这片隔绝互联网的土地上,人与人间反而更有社群的温暖,相比之下城市才像真正的荒野。

2024年,李雪雪在码头的餐厅打工(受访者供图)
这样的体验深深吸引着我。第二年12月,读大四的我提前修完了大学课程,结束最后一门考试后立刻收拾行李前往新一个目的地。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几乎没有停歇,一站一站地去往不同的偏远小镇,尝试各种不同的工作,结识不同的人。进入广阔的天地,我最先感受到的却是匮乏。我发现自己好像不会和人聊天。我以为自己有很多工作经验,比同龄人优秀,但在打工的地方每每和陌生人寒暄时,我常感觉尴尬和僵硬,而寒暄又是做服务行业必备的技巧。
我发现自己常不自觉地用傲慢掩盖自己的匮乏。在一个偏远小镇的机场打工时,雇主常带我去和他的朋友们聊天,我听着他兴致勃勃的讲述自己新铺了地板,在一旁插不进话,觉得这些琐事没什么好聊的。我总希望与人探讨一些深入的话题,比如彼此的文化背景。雇主对于我在中国的生活很感兴趣,他问起我父母的工作,但我发现自己只是模糊地知道父母做生意,对于他们创业的细节、具体的工作内容并不了解——我习惯了按部就班的学习、工作,对生活的细节缺乏感受。

李雪雪在农场打工时所拍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在一个农场里我和一群德国年轻人一起包饺子,我看到他们并不擅长,就让他们不要包了,都由我来做。一个人却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点鼓励?”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事方式带上了令我讨厌的父母的影子。我和父母的关系一直都是比较远的。自我记事起,我就看到父母总在为生意忙碌。他们有时把我带到城郊的外婆家,骗我说很快来接我,结果没出现。小时候我很活泼,总发出魔性的笑声,还调皮地踩碎过街上一家卫浴店的陶瓷便池。父母几次表露出不满后,我渐渐地变得内敛,学着让自己变得懂事,觉得这样父母会更喜欢我。
我用功学习、从不出门乱交朋友,也不早恋,成绩一直在班级前十。身边的亲戚都称赞我是“别人家的孩子”。父母倒又觉得我变得太内向了。我想努力变外向但不知道要如何实现,反而更自卑了。我父亲一直是冷淡疏离的,每次跟他分享事情他都不怎么回应。有一次他开车顺路送我去一个地方,却没提前问我具体的地址,只从我和母亲的对话中猜测了一个大概的位置,当我告诉他送错了,他索性把车撂给我和母亲叫我们自己开车去。我察觉到他其实很内耗,即使是面对亲人,错过了沟通的时机后就不愿意再开口,哪怕只是简单地问一句。

《爸爸是女儿》剧照
我也继承了一部分他的压抑与克制。初二,我脸上长满了青春痘,不仅看着别扭丑陋,还经常疼痒难耐。我变得自卑,对于路人震惊地打量我的目光很敏感。班主任安慰我说,这样就没有早恋的机会,可以专心学习了。母亲周末给我带来她在网上看来的偏方药膏,我觉得这不管用,希望她能带我去医院治疗一段时间。但又想,母亲肯定认为学业为重,去医院浪费时间。我没有向母亲开口。
自我
刚开始旅居打工的几个月,我也时常怀疑自己一个名校毕业生成为了没有社会身份的人,这样的选择是否正确。我也担心如果自己一直这样做,到30岁可能会成为一个生活经历丰富但缺少专业技能的人。当我向母亲谈起自己的迷茫时,她总会趁势劝我回归寻常的轨道,父亲也评价我所做的工作都是在“玩”。我感受不到他们的支持,一度和他们减少联系。父母很希望我能拿到加拿大的永居,但我实在不想为了一张纸而花时间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旅居的过程中,李雪雪会做帮人遛狗的兼职。不只获得了报酬,她也很喜欢和不同的狗相处、与它们的主人交流(受访者供图)
四处打工后,我接触到了不少鼓励、包容的环境。在我去的第一个农场,我只是随口提到我喜欢吃面条,他们就去当地的亚洲超市买来米粉给我煮着吃。包饺子时我说中国的习俗会在饺子里包硬币,吃到的人有福气,他们拒绝了这个提议,怕小孩吃到不安全。但饺子出锅后他们把我支开,等我回来时发现他们专门包了一个带硬币的饺子放在我的碗里。离开那个农场时,有四个人开着面包车送我去公交车站,他们从面包车里探出头,向我挥动手臂与我告别,还跟我说如果我在外面累了可以随时回来。
在一次次的鼓励中,我越来越清楚地了解自我,也学会更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路上碰到工人在装罐三文鱼,我想去体验便直接去提议帮忙,最后得到两大袋边角料回去熬汤。在一个跳舞派对上,我安静地坐着享受音乐,有人拉我去跳舞,叫我“放开自己”,我大方地告诉对方我并不喜欢跳舞,我选择不跳就是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了。我旅居的行李很简洁,只有一个皮箱和一个背包,装着电脑和必备的衣物,但有一个收集朋友给的信件和纪念品的文件袋越装越满。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像是在度假村、民宿这样的工作场合,人与人的距离很近,天然地容易出现摩擦与矛盾。去年夏天我工作的钓鱼小岛上,领导总是要事无巨细地要求我们一切按照她的想法来,哪怕是餐布铺多长、给客人准备什么样的菜。以前我遇到争吵总会在内心烦恼很久,但也是在那个团体里,我看到一个女生总能很好地“对事不对人”,只解决具体的问题,不把情绪迁移到人身上。我试着向她学习,渐渐地也感受到自己的改变。我不再是一个没有爱好与情绪的“空心人”。
大学毕业后我和大部分同学都没了联系,只偶尔刷到他们的社交动态,他们不是读研就是在常规的公司上班,为获得永居身份奔波,不少人也会在帖子里提到自己其实很迷茫。去年10月回到多伦多后,我去见了读大学时的朋友。之前我有点害怕见她们,觉得自己选择了不同的路径,怕彼此聊不到一起。和她们见面后,我发现虽然我们生活的场所不同,境遇却是相似的。有个朋友在我出发前在银行工作,她说这两年她从银行辞职后做过销售、市场部的工作,现在也在做各种兼职和自媒体。大家都觉得没必要勉强自己,要去寻找自己真正喜欢的事。

李雪雪在旅居打工地居住过的房车(受访者供图)
想来想去,我觉得我的选择并非逃避现实,纵使现在的工作经历确实不能给我的简历增光添彩,但我获得了一些技能与人格上的成长。比如我修了心理学,如果我未来真的决定做一个心理咨询师,这几年积累的与人沟通的能力也能派上用场。我也意识到我享受了旅途给我的爱与疗愈,也要接纳自己没有社会身份的事实,接纳负面情绪与可能遇到的伤害。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6年第4期。应采访对象要求,李雪雪为化名)

排版:小雅 / 审核:雅婷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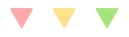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2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6679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