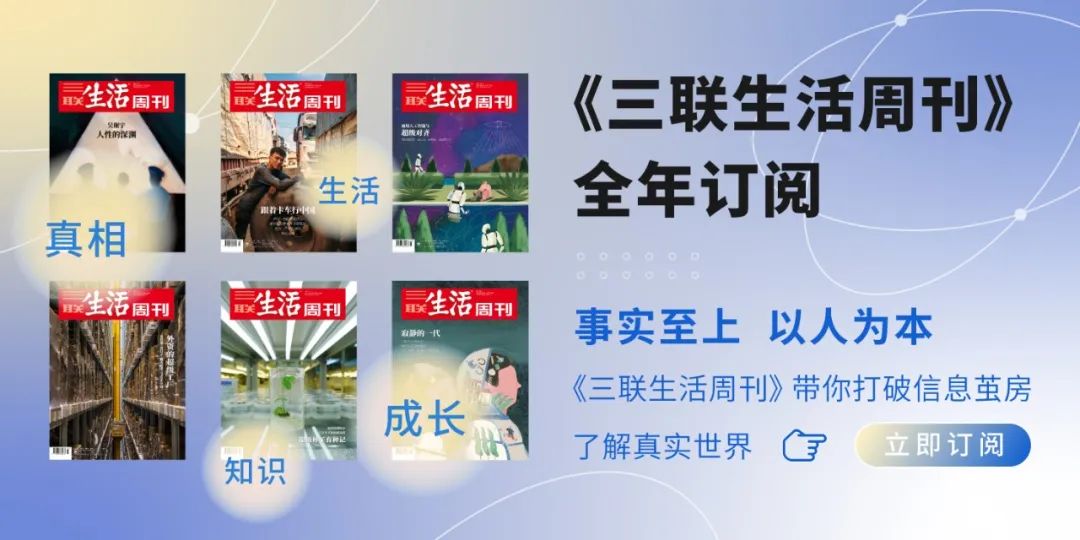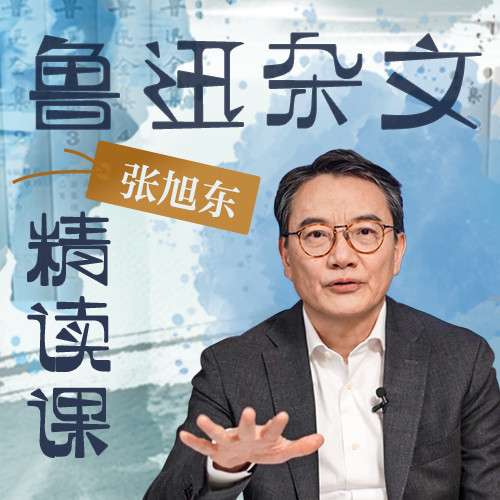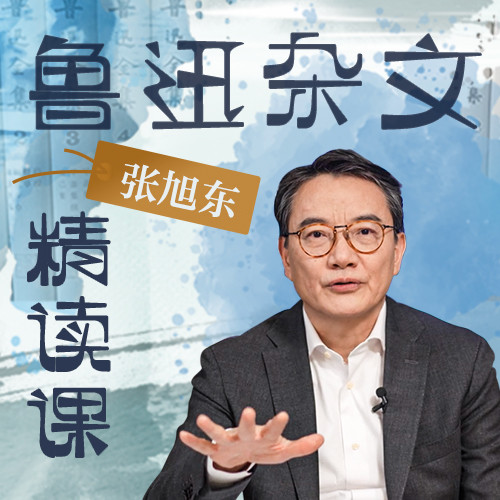想睡个好觉的人啊:越努力,越徒劳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今天·阅读时长23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宋磬
编辑|王海燕
被剥夺的睡眠
被剥夺的睡眠
被剥夺的睡眠
“焦虑症”,北京一所三甲医院的睡眠门诊里,医生在病历上写下这行字。
“我没有任何烦心事值得焦虑。”我否认。“你肯定有,睡不着的人都会有,现在没有,随着你长时间睡不着,也会出现,因为你会陷入担心自己睡不着的情况。”医生回复说。

那是2020年10月,我刚失眠一个半月。过去,我的睡眠质量一向很好,也几乎从不熬夜,即便到达有漫长时差的地方,一旦躺下也能立刻睡着。再严重的事情,也绝不担忧进梦里。我曾住在北京四环一座隔音糟糕的建筑立面,能听得见咳嗽、喷嚏、烧水声和孩子整夜哭闹,但那也只是让我有些心烦意乱,并没有真正摧毁我的睡眠。
后来我才知道,这既是种能力,也是创伤后导致的情感隔离。青少年时期长时间的严重创伤,导致我长年处于生存模式,从来不用情绪去感受压力、艰难甚至残酷,只把很多难题仅仅当作信息去分析处理,并集中精力解决问题,可谓关关难过关关过。即便曾一度出现震颤的躯体症状,我也没有在心态上觉得有什么起伏波动。
现在想想,经历了诸多的复杂创伤后,我仍能数次重建生活,一直是因为睡眠能力在给我托底,让我至少在生理层面能够保持规律的作息和生活质量,得以撑过修复期,不至崩溃。
从北四环从不肯休息的小区里搬到北五环的新小区后,我的睡眠很快就恢复了。但一年后的疫情期间,楼下邻居请的装修工人急于赶工,索性偷偷住在房间里,昼夜工作。深夜两三点,锤子的巨响常常击穿楼层,让天花板和窗户摇摇欲坠,也击穿了左邻右舍的睡眠。

投诉、愤怒的敲门和报警电话,都没能让这个睡在粉尘里急于回款的装修工人停下。警察上门,他就用“打扫卫生”的理由轻轻带过。而我长达五年的睡眠障碍就此开始了。最初因为担心被吵醒,我索性推迟了入睡时间,随着各种维权手段失效,我恐惧“被吓醒”,变得甚至不敢睡觉,入睡也越来越困难。
在又一次被惊醒,在心脏狂跳中怒拍对方大门无果后,我加入一个名为“安静之家”的微信群,想找出解决方案。我才知道,人的生命力会被无尽的小难题折磨得无比倦怠——孩子在地上踢球,老人在凌晨5点剁菜,一场又一场的和平谈判和暴力还击——这些“小”问题难以解决、也难以承受,同时考验着每个人如何处理边界的侵犯和捍卫,保护生活的权利。
众说纷纭里,共情形成了,执念形成了,绝望也形成了——“大道如青天,独我不得出”——无路可走了。继而有500张嘴问你该怎么办?后来我不得不离开那500种绝望。
在聊天群里,很多人已经失眠十几年,或因家人尤其是父亲从早到晚大动干戈,摔门砸柜,随时把电视音量开到最大,邀请朋友彻夜不醉不休,麻将机器震耳欲聋,理由是“我的家我怎么舒服怎么来”,沟通永远无效;或因邻居标榜自己“只是在正常生活”,各种沟通都宣告失败后,即便在自己家里也会感到被入侵的恐慌——在一次强烈的噪音后,我甚至缩在被子里紧张颤抖,退行成婴儿状态;也有的人因过载的工作或学习昼夜颠倒,尤其是医生、护士、司机、24小时服务从业者,我第一次去医院开安眠药的时候,医生为了打消我对药物副作用的担忧,告诉我,睡眠门诊和急诊科的医生服用安眠药是常态,“睡不着和睡不好的害处比药物的副作用大多了”;新手父母尤其是母亲,经常在婴儿到来那一刻,就已开启漫长的失眠史;罹患慢性病或本身有焦虑、抑郁症的人睡眠质量也很糟糕。在这些故事里,人们的失眠都指向了同一点:睡眠往往是被剥夺的。
在各种失眠的群里混多了,我深感绝望。群里的人几乎都睡不着觉,至少500张嘴在诉说故事,500张嘴在交代心思。

失眠是全球常见的睡眠障碍。短期睡眠问题在全球人群中都非常普遍,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约有30%的人经历过短期失眠。而符合慢性失眠障碍严格标准的成年人约占10%-15%——每周至少三天失眠,持续至少三个月,并造成明显的白天功能受损。研究表明,女性、老年人,有抑郁、焦虑、PTSD等疾病、慢性疼痛或多种慢性病的人群失眠比例更高。近年,城市化、晚间电子屏使用增加、工作与学习压力、新冠疫情影响等因素使得失眠问题有上升趋势。
反过来,慢性失眠又会导致抑郁、焦虑、心血管代谢风险、认知下降与免疫功能受损、工作效率下降、出勤困难、工伤风险上升与医疗费用增加,这甚至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经济负担之一。
如我第一次就诊的医生所言,在转成慢性睡眠障碍后,我真的罹患了焦虑症。
越努力,越难以入睡
越努力,越难以入睡
越努力,越难以入睡
我的失眠完全出于被动。但邻居半年的装修期结束后,我的失眠也不见好转。

入睡成了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和那些热衷睡前玩电子产品与忧虑过度的患者不同,我躺在床上,脑子里空无一物,没有任何事情等待分析和担心,不明白内心一片平静怎么还有理由睡不着觉。
11点躺在床上,以为只过去了五分钟,一睁眼已经早上8点。没办法,只能穿上衣服就去公司开会。
2020年到2022年,我度过了“睡不着觉,生不如死”的状态。每周有2天能睡着就非常满足,四、五个小时才能入睡是常态,两个小时能入睡是““上天慈悲为怀,厚德载物”,深度入睡则相当罕见。
我的情绪波动越来越频繁,每天上床前都叹一口气,早上又是灰心丧气。我的大脑逐渐变得混沌、沉重、迷雾泛滥,经常记忆错乱,说话卡顿,记不住人名、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当时我的工作还是采访,经常在对方说完一句话后,无法立刻理解,只能通过录音追溯。我发现自己低沉、难过的情绪越来越多,白天的工作和社交结束后,意志力再也坚持不住,回到家很容易流泪,刷牙、洗脸、打扫房间成了长征一般的艰巨任务。身体总是感到疲惫,耗电极快,我只能停下了所有剧烈运动。
最长有26天,我几乎没睡或短暂浅睡,以为自己会因此死掉。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因为走神而步伐摇晃,常常担心出车祸。

一段时间以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已忘记如何入睡。我不得不开始重新学习睡觉——但和走路、跑步、学语言不一样,谁能记得自己第一次是怎么学会入睡的呢?
我开始阅读不同文献、广告,尝试不同方式入睡。换益于颈椎的低枕、略有重量的棉被,吃(被过度宣传、监管宽松)的褪黑素软糖、GABA类,泡脚,下载助眠软件、听雨声风声海浪声等“白噪音”,游泳、散步、多晒太阳,白天坚决不睡觉以防夜里没有困意,停止咖啡因、酒精、奶茶等饮品,戴表监测睡眠质量——但会导致越来越紧张。偶尔有一两次能奏效,但没有一个能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努力可能注定失败,因为过去入睡,根本不需要任何努力。
过了半年,在承受了“40个小时没睡”的极端情况下,我去了三甲医院的睡眠门诊。
第一次拿到的药,说是副作用极小,不必每天服用,但只起效了两次,第三次就没用了,闭上眼没多久还掉入五彩斑斓的漩涡,第二天更加昏昏欲睡。

四个月后我再次去就诊,医生问我,为什么药不管用,你没有马上来复诊。我说,我觉得连安眠药都治不了,大概是失眠太严重了,而且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有任何效果。我心理压力颇大,不想再面对一次失败。
但医生说,安眠处方药和非处方助眠剂至少有几十种,每个人对药物的吸收和适应不同,许多药遵医嘱使用非常安全,副作用也会在一段时间后减轻或消失,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药。在实际治疗中,很多人都是在尝试几种药物后才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
但遗憾的是,我在这家医院换了三次药,每一种都无济于事。我的意志力向来顽强,所以料想大脑不睡的意志力也很顽固。医生开始建议我做心理咨询。
在一次入睡前,我发现自己再也放松不下来了。即便什么都不做,平躺的心率也能冲上130击每分钟。我的身体比床垫里张力十足的弹簧还要紧张,好像有什么人在我的血管里击鼓,投放原子弹,弹响最紧张的神经脉络,或是有什么人在我的心脏上发出短促的永不停息的通讯密码,焦急而难以破译。一时分不清是我在睡床垫,还是床垫在睡我。
那天以后,我好像要在紧张中才能完成呼吸。

我试图靠游泳找回放松的感觉,但一到泳池,我便沉底。游泳跟睡觉一样,是越拼命努力越做不到的事情。我也丧失了轻松游泳这项技能。
为了睡个好觉,我决定离开导致我失眠的环境——因为大脑在感到不安全的时候,是不会放心入睡的。我回到20岁时住的青年旅舍,那时候我在呼声雷动的八人房间,也仍能安睡。但只有前两天,我睡着了,第三天又一如既往。我几乎找遍了北京的老式居民楼、胡同平房、2000年左右的社区,希望遇到足够安静的居住环境。
2023年,我的人生梦想简化成“找个安静乡村睡一年”,收集了云南、四川等地的农村自建房,列出了“辞职后大睡特睡计划”。我当时想,收割失眠患者智商税的产品繁多,睡眠市场消费人群从2019年到2023年增长了23%,人均花费增长20%,怎么没有人开发能安静入睡的商业地产项目?
后来,我加入某大学心理学系开设的冥想课程,导师引导“感受你的眉毛放松,额头放松,太阳穴放松,肌肉放松,四肢放松”,我只有一次成功进入过冥想状态,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意识到每块肌肉的存在后,更难睡着了。当导师说,“你要先放松才能进入冥想”时,我略带嘲讽地回应,“我就是放松不下来才来学习冥想的,如果能放松下来,还来上课干什么?”这就像有人在一旁鼓励你“加油放松”,十分滑稽。

班级里的同学大多是中年人,看我在先进团体里暴露了落后性,如获至宝地开始教育我:“人要修心养性,怎能向外要求?世上本无物,心静自然凉。”我挥别了冥想MBA班,决定不再玩这种鸡生蛋蛋生鸡的游戏。
在几篇科学论文里,我看到与“努力入睡”背道而驰的建议:睡不着不用硬睡,可以起来走几步,吃点东西,看会儿电视,和朋友聊天,不要把它当成任务必须实现;睡不着也不用太担心,目前还没有一例因为失眠而死亡的案例;如果睡眠恢复了一段时间,但过了几周又睡不着,也不用焦虑,即便没有慢性睡眠障碍的人,一周有两三天睡不着也很正常;失眠和主动熬夜不一样,即便无法入睡或深度睡眠,闭目养神也能达到类似的休息效果;失眠后,连续的睡眠可能难以做到,但打盹、小憩、放空、碎片式睡眠,也属于睡眠的一种;失眠会带给人许多损害健康的影响,但人脑有自我修复功能,当睡眠逐渐恢复后,因失眠导致的认知下降等症状会逐渐消失;不要用完美主义看待睡眠这件事,不要横向比较过去的自己“沾床就睡”的特技,越努力入睡越会因达不到预期而焦虑、沮丧水平升高,焦虑和努力入睡的行为会导致身体的生理唤醒增加,加重失眠;如果失眠的原因来自创伤经历、高觉醒状态、过度思考、焦虑抑郁情绪等,要通过专业治疗介入,给自己营造有安全感的居住环境。
连续四年,我的生日愿望都是“恢复睡眠”,我的生命目标也从职业成功转变为“睡得着”。但也渐渐学会,在一夜睡不着后,打开买菜平台逐个下单安排明日菜谱,葱姜蒜、海白虾、五花肉、罗马生菜成了内心稳定平静的秩序。
失眠久了,你不得不接受,睡好觉就精力旺盛,如同瞬间回到20岁的自己,能够轻易快乐起来,睡不好就萎靡不振、唯唯诺诺,性格大变。你无法只拥有最好的那一面自己,只能用“完整性”去理解生命。

在能睡就睡,睡不着也无所谓的心态下,我的睡眠稍有恢复,但只要有外界压力刺激,或是有一天因为熬夜或晚睡打破规律性睡眠,就得花三周以上来恢复。
2023年,我换了一家医院,终于找到了适合的安眠药,但两个月后,药效就逐渐减退,换药又开始了。
2024年,我决定去做压力测试和心理测验,在一家三甲医院的心理科,医生根据情况为我制定了长期服药计划,每天睡前固定吃药,既稳定焦虑抑郁情绪,又能帮助入睡。
幸运的是,这种药终于奏效了,直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我的情绪消耗和失眠症状稳定消退,基本能做到服药后一小时内入睡,每天的睡眠时间恢复到9到10个小时。记忆力和体力虽然没有完全恢复,也改善不少。
与服药同步进行的,还有长期的心理咨询,以处理我过去的创伤,改变那已不适用于当下的我的生存模式。今年2月,我离开了从不停息的北京、噪音不休的居民楼和累积了无尽倦怠的工作。在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地区的一家青旅里,我爬山归来,放下装着一年用度的登山背包,跟刚认识的舍友拥抱,爬到床铺上酣睡。
也是八人间,也是各国的背包客呼声如雷。
睡眠是某种程度上的意识的暂停,清醒的暂停,创伤的暂停,忧虑的暂停,时间的暂停,价值的暂停,各种标准体系的暂停,过去、未来、现在的暂停,悲剧和喜剧的暂停,理念信念欲念的暂停,如果没有这种暂停,人是无法承受头脑和世界的重力的。
任何天分都有可能丧失,当失去睡眠这种自然暂停时,也是一种提醒,在不肯休息的信息流和时间流中,主动休息这件事,也需要练习。

排版:球球 / 审核:小风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大家都在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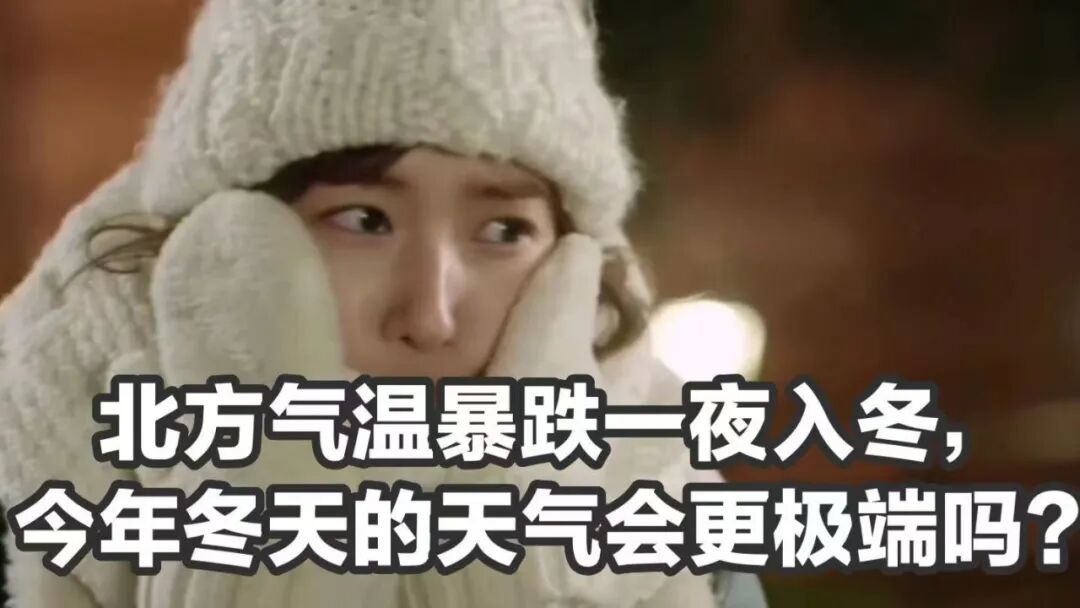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1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6160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