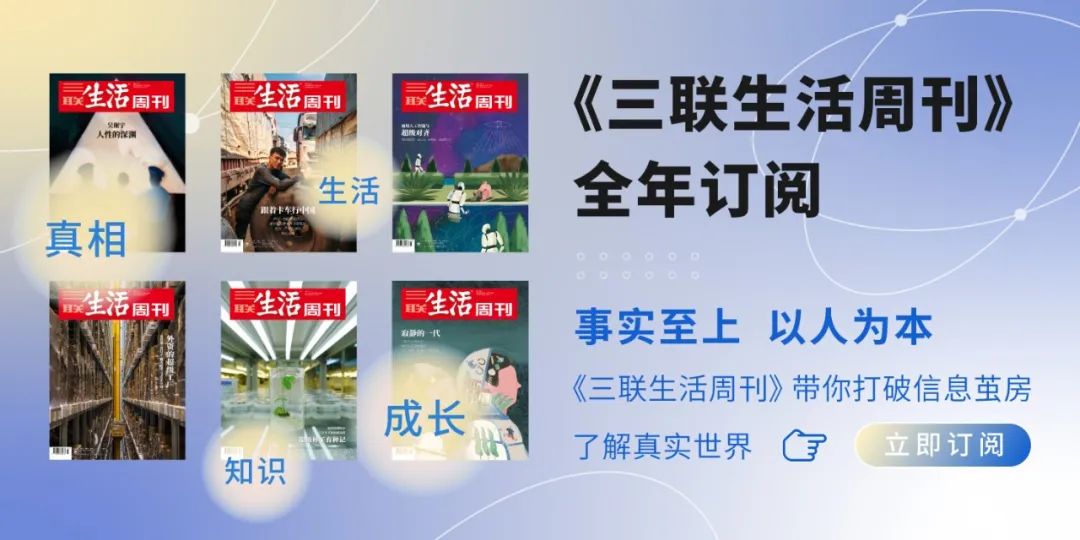落魄的“国民顶流”,在这座孤城抵达人生巅峰?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今天·阅读时长33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公元766年,55岁的杜甫抵达夔州(今重庆奉节),随后迎来他创作史上最惊人的爆发——在相对“静止”的这21个月里,他共写下430余首诗,占其传世作品总数的近三分之一,《秋兴八首》《登高》等不朽之作也诞生于此。生理的衰病、对家国历史的深观,以及夔州的山河,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白帝城或许有答案。
记者|驳静
摄影 | 张雷
公元766年,55岁的杜甫抵达夔州(今重庆奉节),随后迎来他创作史上最惊人的爆发——在相对“静止”的这21个月里,他共写下430余首诗,占其传世作品总数的近三分之一,《秋兴八首》《登高》等不朽之作也诞生于此。生理的衰病、对家国历史的深观,以及夔州的山河,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白帝城或许有答案。
记者|驳静
摄影 | 张雷
唐大历元年(766年)暮春,杜甫一家约十口人终于登上离开云安县(今重庆云阳)的一艘大船,打算“迁居白帝城”。白帝城就在今天的奉节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地处三峡库区的心腹位置,古称夔州。
因为生病,杜甫已经在云安县滞留了半年多,比他预想的时间要长许多。他从成都离开后,辗转多地,看上去,他的最终目的地并不十分明确。或许他依然没有完全放弃去长安求官的念头,或许他已经因为垂老转而想要落叶归根,沿着长江一路向下,“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他的最终目的地是大北方。大历三年(768年),依旧是春天,杜甫又启程了,与将近两年前刚入夔州时相比,最大的变化是手头多了430余首诗。刚到达夔州时的杜甫恐怕也想不到,他会在这里迎来人生的创作巅峰时期,更想不到,这会是他59年的生命岁月里最后一段安稳的时光。后世有记录的杜甫诗作总计1450余首,夔州诗占到了将近三分之一。不只如此,著名的《登高》《秋兴八首》等代表作,也都是在夔州创作。
既然杜甫离开成都,目的地是在北方,为何要在夔州久居长达21个月的时间?夔州的什么事物留住了我们年迈的诗人?他在夔州度过了怎样的两年?为何诗人人到晚年,疾病交加,反而迎来艺术创作的大爆发?我们来到夔州,依照诗作,踏访杜甫晚年的踪迹,并在这里试图寻找这几个问题的答案。
流寓夔州:创作巅峰
尽管唐代夔州下辖的区域还要包括上下游的云阳、巫山等地,但杜甫“入夔”后,居住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奉节县。他具体都在哪些地方住过?一到奉节,夔州杜甫研究会原副会长龙占明就给我报出了四个地名:西阁、赤甲山、瀼西、东屯。两年住了四个地方,频繁搬家,成了杜甫夔州漂泊生活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龙占明不这么想,他感到相当遗憾的事情反而是,居所虽多,但直到今天,奉节也没能够在任何一个旧址上建成夔州版的杜甫草堂。
搬到东屯,是杜甫到夔州后第二年,这一年春天,他先是搬到瀼西,在那获得了一片40亩的柑园。很快又迁居东屯,因为夔州府都督柏茂琳将100顷政府公田委托给他。杜甫成了水田管家,为了监督秋收,他只身一人搬到了东屯,与此同时,又会不时回到瀼西去跟家人团聚。

除了进行农事生产,偶尔去都督府参加社交活动,间或有友人远道而来,杜甫在夔州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是静止的。夔州雄踞瞿塘峡口,峡口两山对峙,历来是军事重镇,也因此相对闭塞,外面战乱从未真正停止,中央权力斗争还在进行,但基本影响不到夔州。就夔州这方空间而言,外部世界可以概括为一个词:无事发生。
但是杜甫的内心世界却翻涌不息。北京大学陈贻焮著作的《杜甫评传》,有一节小标题就称杜甫“天气像心情一样多变”,他心情多变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恋阙之情”,也就是对朝廷念念不忘,“他内心深处总忘不了立朝辅君的初衷”。在夔州的第二个秋天,杜甫身体好转,写了不少抒情小诗,其中有一句很好玩,说“莫看江总老,犹被赏时鱼”,鱼指“绯鱼袋”,是杜甫之前获得的检校工部员外郎这个官阶的凭证——借鱼符宽慰自嘲,我们的诗人对袒露这一点可真是毫不避讳呢。
但重返政坛的希望如何?大唐当时军阀割据,国家形势不容乐观。与此同时,他过去在政坛上的依靠都已经相继去世。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莫砺锋总结,正是在这样一种“前愁未已,后愁复至”的氛围里,杜甫展开了全面回忆,而这种回忆诗,正是杜甫在夔州期间的创作呈现出来的新的主题倾向。一是回忆生平,包括他的青年时代,也正是通过《壮游》《昔游》等诗,我们才能对他青年时期游历过的足迹有所了解;二是回忆他的朋友和历史,为此创作的《八哀诗》《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等,当然还有《秋兴八首》,都是杜甫夔州诗里的典型代表。
这些回忆作品,代表了杜甫晚年七言律诗创作的巅峰。对此,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明华表述得更干脆:七言律诗在杜甫手里实现了巅峰。
关于杜甫夔州七言律诗的历史地位,刘明华跟我做了一个形象的描述:旧体诗的走向,到“李杜”是高峰。再往后走,宋代苏东坡、黄庭坚等人是次高峰。元明清之后一路向下,走到今天是无限接近地平线。换句话说,李白和杜甫占据了旧体诗的最高峰。而杜甫的夔州诗,又是他所有留存下来的诗里最好的。
那么为什么恰恰是在夔州?

中国杜甫研究会常务理事左汉林教授,曾踏访过几乎所有杜甫游览居住的地方,奉节当然也去过几次,他的感受是,杜甫在这里迎来创作大爆发,恐怕确实受到三峡的激发。另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观点是,正是因为“无事发生”,给了杜甫足够多的时间去创作。七言律诗是古体诗里难度最大的一种,左汉林提到一个很好玩的说法,他说,杜甫一生,只要安定下来就写律诗,所以成都和夔州都是他写了很多律诗的地方,在夔州当然更多更好,很多还是组诗,还有特别长的排律——相当于律诗的加长版。
杜甫在夔州除了有大量空闲时间,而且生计无忧,这一点主要得益于当地行政长官的照顾。这位和杜甫同年抵达夔州就任的都督柏茂琳,跟杜甫是在成都时的同事。当时杜甫是成都最高行政长官严武的参谋,而柏茂琳则是牙将,一文一武,想必也是有过交往的。所以,当柏茂琳被派到夔州担任行政长官时,他对这位年迈且穷困的老同事提供帮助,并不意外。杜甫带着家人开始游历后,经常依赖朋友的救济,但他这位老同事对他可以说是额外尊重,甚至“频分月俸”。有了这样的照拂,杜甫身心是有宽慰的。
至于回忆,一位创作者到了晚年,“回忆几乎是必然的”。当代诗人西川从杜诗里读到强烈的历史感,“一个人闲而又有历史感,而这种历史感又没人要,激发出来的东西就太多了”。当过皇帝的政治秘书,又亲历过战乱,被俘虏过,一度饥寒交迫,这些经历装满了杜甫的身心,抵达夔州前,诗人恐怕已经蓄满创作能量。
在所有回忆诗里,《秋兴八首》尤其值得关注,它可能是杜甫诗作当中被分析研究最多的一组诗,同时也是公认的杜甫最好的作品之一。这组诗中,杜甫经常在一个句子里同时提到夔州和长安。“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从“夔府”“瞿塘峡口”,瞬移到指代长安的“京华”“曲江”。这些对长安的反复吟望,像在对过去的理想告别。

到现在刘明华还能记得50年前的一个雨夜,知青下乡第一年。在大巴山,分给他的那间房子漏雨,他用一张塑料薄膜盖在蚊帐上方,水积多了就舀出去,平时凑合也能过。有一天晚上雨有点大,他正睡得沉,突然蚊帐架子就被积水压垮了。当时头脑里冒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读一点杜诗了。但是太疲倦,很快他就在床上找了一块未浇透的角落继续睡去。
刘明华从二十出头开始研究杜诗,通读1450余首杜诗,前后熟读记诵的有四五百首,今年69岁,他仍旧没有停歇的意思。过去研究《秋兴八首》时,他对这组诗里的时空转换印象极深,“这组诗是一个整体,仔细去读,前后都有呼应,并且能看到明确的‘回环往复’。历史和现实,首都和边地,过去的繁华和现实的衰敝,曾经的辉煌时刻和现在的穷途末路,诗人的悲凉悲愤都在这些反差对照当中了”。
对杜甫的晚年创作,刘明华还有一个总结:我们的诗人在有意识地追求诗歌的语言格式。对于精微的格律艺术,杜甫相当在意,诗人自己也多次总结过他的创作思想,“语不惊人死不休”,“晚节渐于诗律细”等就是其中的明证。
研究者还会提到“拗律”,这是后人发明的一个词,用来指代杜诗当中不符合格律的诗。复旦大学朱东润教授认为,杜甫看到,为了追求音节的醇美,七律有时会走向反面,诗人到了夔州,试图打通一条新路。刘明华大体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觉得杜甫作拗律或许可以证明一件事,我们的诗人在夔州意识到,他自己也无法超越自己的前诗,于是去做了一些实验性的艺术创新。这些创新为夔州诗带来一种“铿锵的音调”,读起来确实有种艰涩顿挫的音响效果。

瞿塘峡:不尽长江滚滚来
杜甫写到峡口的险丽景象,经常出现以下元素:赤甲山,在长江北岸;对面则有白盐山;两崖对峙,中贯一江,望之如门,就是夔门,此处潜流暗涌,异常湍急;两岸还有猿的哀啼。
萧驰在《诗与它的山河》一书中提到,杜甫在描绘瞿塘峡时,不断使用的代称有“绝塞”“绝域”“荒城”“乌蛮北”等词,夔峡的质感在我们的诗人心里恐怕首先就是“荒远闭塞”。杜甫一直都很明确他对三峡的感受是“形胜有余风土恶”。今天的奉节人兴许并不愿意承认,诗人对山川险峻,和夔州此地的交通阻塞、潮热气候都是不适应的。瞿塘峡的雄峻森耸固然能激发创作,但等到杜甫终于能离开夔州,除了百感交集,更多的还是畅快,“始知云雨峡,忽尽下牢边”,能感受到一种欢欣跃然纸上。
不过外来客在2025年来到奉节,恐怕很难感受到杜甫笔下的“荒戍之城”。奉节人还会带着一种复杂感情告诉你,2003年三峡大坝蓄水,水位最高可达175米,从此瞿塘峡的急流险滩也不复可见。
2022年通了高铁之后,从重庆下到奉节,只需不到两个小时,从奉节到巫山不过20分钟。不过长江上仍有班船通行。2000年以前,当地人口中的“小红船”就已经在奉节和巫山两地之间运行,这种班船早晚各一趟,同一时间对开,船客多半是种水果和蔬菜的农户。8月,巫山脆李上市;11月,奉节脐橙上市,这是船客最多的时节。现在,到了“五一”“十一”等公共假期,小红船还能迎接一批游客。
假如依然不死心,企图哪怕从物理位置上靠近杜甫诗中的夔门,坐这样的慢船是最好的选择。我登船是在9月初,正好是淡季,从奉节码头起程,上来的船客只有四人。不过,船穿过瞿塘峡之后,小红船开始走“之”字形,往返江两岸,承担渡轮功能,有船客挑一担青杮,只为去江的正对岸。最后抵达巫山码头时,船上就有了20余人。

小红船二层驾驶舱前方,是最好的景观位。起航约莫20分钟后,远远地,赤甲山进入视野。这座山很可能是外乡人抵达奉节之后,最先学会辨认的地理坐标。赤甲山海拔1388米,山顶尖尖处有一处很明显的折角,线条垂直往下,直插江底,使得它在山尖上的造型接近桃尖,本地人因此也叫它桃子山。凸出的尖顶,一面布满绿树,另一面则是秃的,裸露出它暗红色的山体。这些都是我学会辨认它的依据。至于白盐山,它就在赤甲山对面。夔门就更容易寻找,两山中间就是。

我在奉节几天,在不同方位见识过赤甲山的多种形态,山的形态是那些天流连在脑海最多的图样,配的画外音是杜甫写赤甲山最有名的诗句,“赤甲白盐俱刺天,闾阎缭绕接山巅”。甚至也登上了赤甲山——它现在以“山峡之巅”的名头存在,2020年对外开放,已经被列为奉节旅行必到之处。

我们去登赤甲山,原本是试图从山巅俯瞰夔门,听说从这里能看到“一条带子形状的长江”。但这天恰好有细雨,等我们登到山顶,雾气沼沼,拦在半山腰,盖住所有觊觎长江的视线。开发之前,赤甲山人迹罕至,当年的杜甫大概率也只是“仰望”,但他在白帝山登高,写下了流传千古的七言绝句《登高》,或许值得将全诗摘录在此——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刘明华生活在重庆,对三峡十分熟悉,从研究杜诗开始,就对《登高》很有感情。这也是杜甫非常打动人的一首诗,由于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很多人成年后即便不记得全诗,也能背诵前四句。刘明华说,“落木萧萧,长江滚滚,它表面上是在描述长江和瞿塘峡的景观,里面却有一种历史的律动,那种生生不息的厚重感,杜甫两句话就表现出来了”。
写这首诗的时候,杜甫已经搬到东屯。大约是在重阳节这天,原本跟他约了喝酒的吴郎爽约了。吴郎是杜甫的一个远房亲戚,带领家眷来到夔州,杜甫就把瀼西草堂借给他们住。本来可以跟亲人喝酒作诗,现在只能登台独酌,我们的诗人心里应该又感受到了强烈的孤独。多病,又流寓在闭塞之地,由此及彼,顺势联想在长安时的诸多活动,这些都是他在夔州最常表达的主题。他在重阳写的《九日五首》,读来也是同样的感受。但其中唯有《登高》,空间壮阔磅礴,时间漫长恒远,读来悲凉又悲壮。
“滟滪既没孤根深,西来水多愁太阴”,杜甫也写“滟滪堆”,而这是另一个山川敌不过人类改造的例证。滟滪堆原是夔门峡口一块巨石,夔门最窄处原本就只有百余米,又有巨石阻拦,夏季水流大,一江怒水直冲滟滪堆,导致的涡流极易造成航行事故。杜甫写它“孤石隐如马”,这个礁石究竟有多大?1959年12月被炸掉前,曾有人专门测得数据,堆长40米,高出水面26米。
“高江急峡雷霆斗”的景象当然无法再现,或许今天的瞿塘峡更接近杜甫刚刚离开夔州抵达江陵那个春天写下的《旅夜抒怀》: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小红船驶过夔门,我转身回头张望,江面宽阔,沉稳无言。

白帝城:卧龙跃马终黄土
奉节如今自称“诗城”,历史上夔州确实有众多诗人过境,或途经,或短居,留下过许多著名诗句,所以去游览白帝城、三峡之巅等景点,甚至行车穿隧道的隧道口上方,都能看到大号字体醒目张贴这些诗句,有李白的,也有杜甫的。
刘明华跟我谈到杜甫的悲剧性时,说杜甫艺术上的超前性,使他在唐代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盛唐人偏爱李白、王维等诗人,他们是浪漫的、空明的,但杜甫一方面更喜欢用典,另一方面,他书写了大量民间苦难,这些叙事性诗作,批判揭露社会现实,都不符合当时的审美风格。
一个挑战我们对杜甫刻板印象的事实是,杜甫也是个“狂人”。杜甫在夔州所写的回忆诗《壮游》里,就说自己“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出将入相的大志7岁就立下了,直到晚年仍然表达自己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刘明华认为,杜甫对自己的才华有相当准确的评估,“一个诗人有没有才华,几个人在一起写一写、比一比就知道了”。当然,很少有人像李白一样,生前就获得了与才华相匹敌的追捧和荣光,享受到伟大诗人的福利。比起这位超级明星,杜甫到了晚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唐代人说起白帝城,有时也指夔州府,后者是在长江北岸白帝山的基础上,往西北面山坡扩展出来的一片城池。但今天,当我们说起白帝城,通常是指瞿塘峡口北岸建在白帝山的那块景区,也是杜甫在夔州反复描绘的地理位置中最明确的一处。“白帝城位于白帝山上”,今天,这个叙述已经失效,三峡大坝蓄水后,水位最高可达175米,白帝山,如今是个岛。

过去从鱼复浦前往白帝山无需涉水,从山底出发,走完400余级台阶,就可以到达白帝庙。说是白帝庙,供奉的却是刘备和诸葛亮等人。白帝城的历史要追溯到西汉末年,陕西人公孙述自立为“蜀王”后,在长江北边建造了这座城池。不过关于白帝城,更著名的故事当然还是刘备托孤。夷陵之战,刘备伐吴大败之后,带领残余部队退到白帝城。第二年,刘备将诸葛亮从成都召唤过去,并将儿子刘禅托付给这位鞠躬尽瘁的丞相。后世因为公孙述没有合法性,转而为刘备、诸葛亮等人修筑了塑像。
杜甫一到夔州,就住在西阁,靠近白帝山山脚,山,每天抬头可见。几乎是第一时间,他就上山去凭吊过他的偶像。杜甫在成都时就游览过武侯祠等遗迹,而比起长安和成都等地,杜甫在夔州能游历的景致其实并不多,白帝庙是他反复前往的地方。为此他写下不少诗,其中公认最好的一首是《白帝城最高楼》。诗中描述完白帝城高耸的城头后,末两句说,“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有个拄着藜杖忧时叹世的人,正将血泪掷向空中,与此同时还要回头遥望北方——白帝城半山腰上,也能见到一个回首遥望的杜甫石雕像。
在奉节的倒数第二天,我们才得以登上白帝城。沿台阶走到山腰,看到雕像,停下来拍照时才发现,雕像身后恰好就是“赤甲白盐俱刺天”的景象。还有一块指示牌提醒我们,目之所及的这块水域,就是过去“滟滪堆”的所在地。

龙占明告诉我,雕像原本不在这里。过去白帝城山脚下有家氮肥厂,旁边就是杜甫西阁,它兴建于上世纪80年代。西阁被淹到水下之前,庭中就立着这具杜甫雕像。库区蓄水,能抢救的东西有限,但大家还是将雕像向东上移到白帝山山腰。奉节人用心良苦,为雕像找到了这样一个可以登临远眺的风水宝地。诗人在夔州,借助亘古山河与历史遗迹,倾泻他的无尽忧思,但政治理想落空,时代也未来得及为他加冕桂冠,然而山河跨越千年,在此与我们照面。
如果说刚得到检校工部员外郎的任命时,杜甫还能迅速重燃入仕的理想,到了夔州,他意识到他的两项旧疾(糖尿病和风湿病)加重,需要在此地静养。与此同时,国家局势并没有因为安史之乱的结束而走入平稳,唐帝国处在内忧外患、军阀混战当中。杜甫恐怕也很清楚,盛朝景象彻底成为过去,而和平时期他都没能“致君尧舜上”,面对战乱,他就更加没有可效力的机会了。
诸葛亮是许多古代文人的政治偶像,我们的诗人或许最初的情感投射,也是一种景仰,羡慕他与刘备之间拥有的理想君臣关系。但在夔州时期,他的诗透露出来的,更多的是哀叹和无可奈何。白帝城山顶,就是白帝庙,庙内有座明良殿,主位是刘备像,左侧有关羽和张飞,右侧是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刘备托孤前,或许算是留了一手,当着所有大臣的面,他跟诸葛亮说,刘禅如果能干,丞相就辅佐他,如果这小子不堪大用,丞相可以取而代之。杜甫徘徊在白帝庙,思考君臣关系,当他想到这一层,或许会产生一种“卧龙跃马终黄土”式的自我宽慰。
瀼西与东屯:亲爱的生活
台湾中山大学特聘教授简锦松跟学生讲授读杜诗的方法是“平实地去读”,顺着杜甫看到的景致,跟随他的行动,杜甫写诗擅长用典故,容易读不懂,碰到这类句子,那就跳过去不管。按照这个方法读杜甫的夔州诗,比较容易被其中那些生活面的真相所吸引。杜甫为此创作的诗歌展现出来的夔州生活里,有丰富有趣的一面,他有时甚至会针对极琐碎的小事创作,像在写日记。
春天,搬家。766年的晚春,是领着一家约十口人,从云安搬到夔州。767年的春天,更是一连搬了两次家,先是西阁搬到赤甲山,很快又搬到了瀼西,先是租了房子,后来又买了下来,包括旁边一个40亩的柑园。
春夏之交,农闲时分,杜甫会派仆人去山谷里砍树,为修补院墙的篱笆做些准备。
夏天,等人上门送菜。柏茂琳会遣人给他送夏令时蔬,可是这个送菜的小职员又怠慢老人,送来一些没人爱吃的野菜,杜甫发牢骚,作诗一首。柏茂琳后来又换了个人给他送,这回令人满意,杜甫又作诗一首,夸完领导,又夸下属。
秋天,盼雨,“畦丁告劳苦,无以供日夕”,蔬菜供应不足,杜甫催仆人去田野里摘些野菜回来凉拌。不久后终于下了一场雨,杜甫又催仆人趁雨去种些菜。秋初,家里还做过一种叫“槐叶冷淘”的消夏凉品。
冬天,看雪。两个冬天都下了雪,尤其是第二个冬天,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壮雪。有一次半夜还起大风,刮走了门外江边的大树。正是在这个时节,老杜发出由衷的感慨:“君不见夔子之国杜陵翁,牙齿半落左耳聋。”
西川说他读这些诗的感受是“杜甫非常诚实”,因为中国古人在写作当中,诚实的感受经常会被他们的审美替代,但杜甫的写作突破了这种限制,“他的诗与他的生存状态关系非常直接”。但过去文人的作诗习惯是,“修辞场景”才是符合律诗审美的内容,但杜甫却会将“骑马摔了”这一类偶然性场景写进诗里。
当然,杜甫对于这些琐碎生活,有时也充满自嘲,他写道“穷老真无事,江山已定居”。但正是这些“生活面的真相”,使得简锦松认为,一定程度上,杜甫在夔州过着“亲爱的生活”。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我们的诗人近不适应夔州的气候,远又想要回到北方家乡,所以在夔州的两年是“不得已”。但刘明华提醒我说,别忘了杜甫并不是一个普通百姓,他有官阶在身,更何况,他走到哪里都有人救济。
安史之乱后,杜甫一直在路上,漂泊生活没有真正停止过,夔州山水激荡,可杜甫的身心得到抚慰,或许一度也接受了仕途无望的这样一个结局。能安心在这里生活两年,后世读者无疑也为我们年迈的诗人松了一口气。
杜甫在夔州搬了三次家,每一次可以说都是改善型搬迁,东屯是他离开夔州前最后一个居所。按照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1979年和1980年踏访的记录,“东屯,在白帝城东北十余里,沿着白帝城北面旧基址走,城基下有河床蜿蜒如带,细流如绳,即旧之东瀼水,今之草堂河。走下山坡,又沿草堂河谷的公路向东北走了几里,就到了奉节县草堂区白帝公社的浣花大队。这里就是杜甫东屯草堂旧址”。
龙占明退休后,曾参与奉节县志修订,十年时间,他对夔州地理方位的变迁相当熟悉。他告诉我,清代就有“鱼复杜工部祠”和“草堂杜公祠”同时在这里存在。《夔州府志》也记载,自宋代以来,至少有15次修建或修葺杜公祠的记录。夔州历代官员应当都很重视杜甫留下的生活遗迹,所以才会将东瀼水改名叫草堂河,将东屯所在的村子命名为浣花村。
1981年,龙占明被分配到草堂中学任教,后来还当了校长,他与夫人苟文俊在东屯度过了15个秋冬。夫妻二人带我重游草堂中学旧址,它紧挨长江,站在岸边,能看到赤甲山的北面。龙占明指出旧址的大致方位——它早就深深地淹在水位之下。学校停办之后,部分校舍成为“三峡文化研学基地”的一部分,校园主干道一旁因此还有李白、杜甫、陆游等诗人的介绍,这些诗人都曾过境夔州,而显然,杜甫是其中对夔州文化贡献最大的一个。但与杜甫关系最贴近的文物,现在只有一块残碑,由安徽巡抚冯煦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所撰,题为《重建杜工部瀼西草堂记》。东屯杜公祠上世纪50年代改建为草堂供销合作社,祠宇和塑像都荡然无存。

龙占明现在依然在主编夔州杜甫研究会的会刊《秋兴》,聊起杜甫和诗人的夔州生活,总是滔滔不绝,有一次我打断他的讲述,问说:“读杜甫的诗、研究杜甫,给你带去什么变化?”这个问题有点难,他想了一会儿,说,“杜甫使我崇高”。
龙占明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但是上世纪80年代,一位教授的到来让他变得不普通。1987年,重庆三峡学院谭文兴教授到奉节考察杜诗地理,他是专门为《天池》这首诗来的,这是首20句的五言长诗,头两句即是“天池马不到,岚壁鸟才通”。龙占明接待了谭教授,加上他的另一位同事,一行三人,沿一条土公路,徒步前往“天池”。三人在山里过了两夜,最后确实也找到了古天池遗迹。谭教授一共考察天池两次,写成一篇《谈杜甫的〈天池〉诗》,发表在1988年第4期《杜甫研究学刊》上——龙占明是第二作者。
这次偶然事件唤起了龙占明对杜甫的兴趣,他也开始学习如何研究杜甫,并逐渐成为奉节本地杜甫研究会的重要成员,外地研究者(或者像我们这样的记者)去奉节考察前,倘若打听本地向导,得到的推荐名单里一定就有龙占明。前几年,杜甫出生地河南巩义县的杜甫研究会前往奉节考察,龙占明就在接待团队当中,那个时候,背诵《秋兴八首》全文已经是他的拿手绝活,而他发愿背下这么多诗,是因为有一天看到范曾背杜诗,心想自己比范曾还要年轻几岁,他能背,自己也能背。那天,他也当众背了几首,巩义的一位企业家很受感动,他请龙占明打开微信收款码,当场给他转了两万元。杜甫恐怕也想不到,他在夔州不到两年,竟然还能为1000多年后的本地人,带来这么多“崇高的”生活乐趣。
大历三年(768年),还是一个春天,杜甫启程前往江陵,可以投靠的是他的族弟杜位。然而江陵未能久留,实际上,离开夔州及至最后在湖南去世,杜甫再度陷入过于动荡的流离生活。公元768年至790年,两年时间里,杜甫的行程是这样的:夔州—江陵—江陵公安—岳州—潭州—衡州—耒阳—潭州。他在江陵写下的《旅夜书怀》的最后一句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参考书目:朱东润著《杜甫叙论》、陈贻焮著《杜甫评传》、左汉林著《杜甫画传》、[美]宇文所安著《诗的引诱》、洪业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莫砺锋著《杜甫十讲》、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著《访古学诗万里行》〕

排版:小雅 / 审核:同同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大家都在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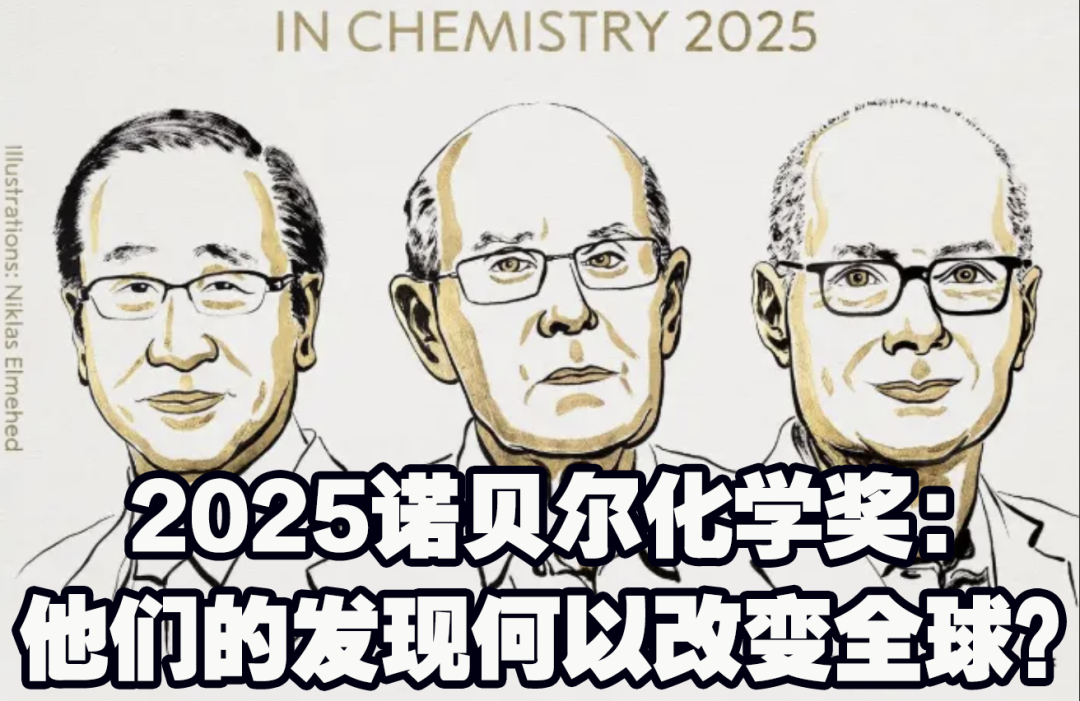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1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6159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