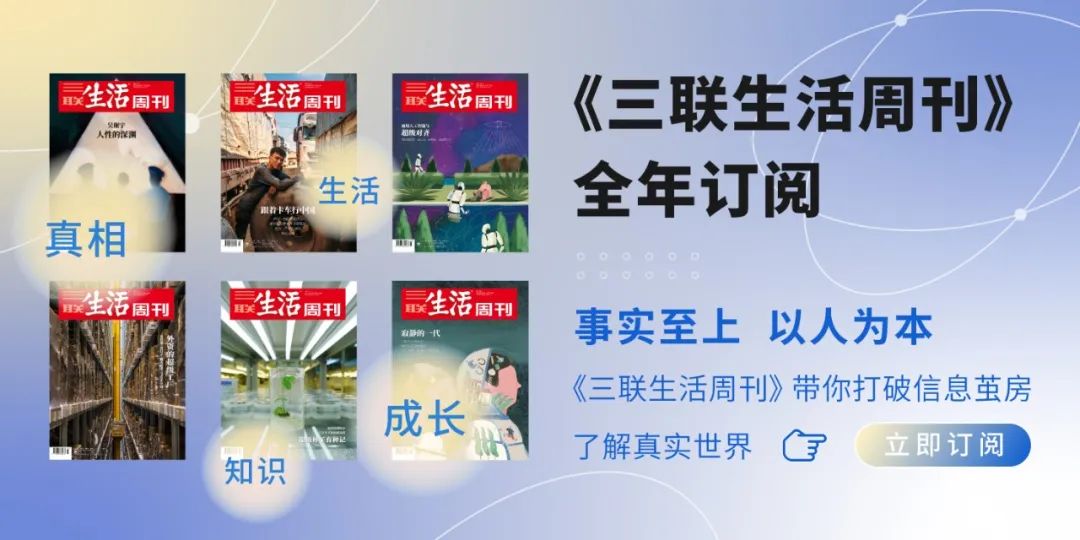活得拧巴的年轻人,其实在经历一种新型隐秘危机?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今天·阅读时长20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自我同一性的发展所经历的环境,最初是原生家庭,然后是学校,之后是工作环境和社会生活。个体在这些环境里的每一步成长,都可能被环境所促进,但也可能落入困境而停滞或紊乱。获得了充分的自我同一性的人,往往是经历过诸多挫折,但又未被挫折所打败的。唯其如此,他对世界的理解才比较贴合真相,他的自我才比较牢固,他的“做自己”才不是逃避的借口或空想的口号。
文|訾非(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
大学三年级的安娜(化名)整天忙得焦头烂额。自上大学以来,她的“必做清单”越拉越长,清单里的部分事项如下:(1)保持高绩点(为保研做准备);(2)参加老师的科研项目(为保研做准备);(3)参加培训以准备考公;(4)参加社团活动并担任社团干部;(5)谈恋爱;(6)申请并参加名校的暑期夏令营;(7)整牙;(8)减肥(虽然安娜的体重指数在标准范围内);(9)追星;(10)学《周易》算命⋯⋯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不是在忙,就是在去忙的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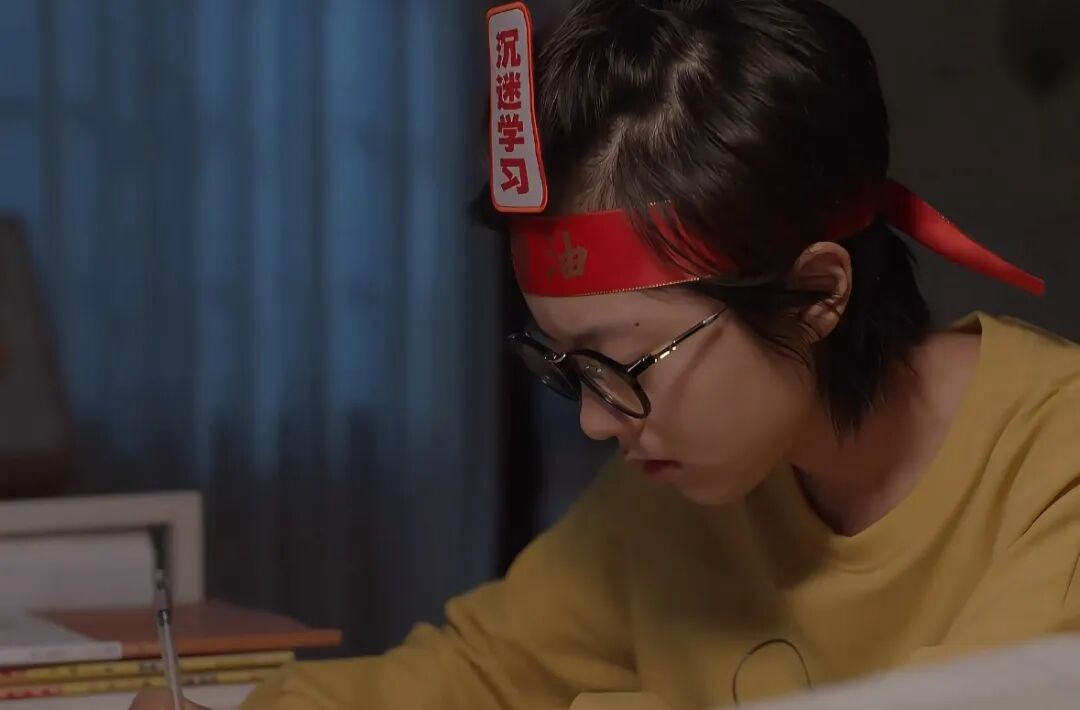
有同学调侃安娜,说她“比总理还忙”。安娜觉得这恐怕就是事实——她被“必做清单”弄得应接不暇,时不时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即使世界上真有比她还忙的人,那也应该不多。
安娜说,当大家都去做某件事的时候,她就感到那事儿一定很重要、有价值,如果她不去做,就觉得是一种损失。“如果别人做了,而我没做,我会恐慌。”“如果别人做了,我也做,我会觉得安全——如果我做得更好,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安娜的男朋友戴维(化名)认为,安娜之所以如此忙碌,是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做自己”“总是以别人为参照”。
戴维说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有一个目标,就是大学读完后“考公上岸”,找一个稳定、有保障的工作。这是父母对他的期待,他觉得这个目标挺好。
但是安娜说她宁愿忙死也不能像男朋友那样“躺平”,她认为戴维依托在父母的意愿上活着,看似知道自己要什么,其实连“做自己”的边都没有摸到。尽管安娜似乎总是在“跟风”,但她把这种做法看成“做自己”的一种途径——通过以他人为参照,通过“人有我有,甚至更优”,安娜相信这样可以打造一个更丰富、更优秀的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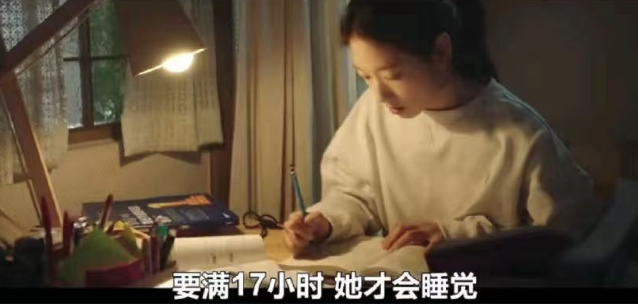
戴维认为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己不被周围的人的追求所影响,而安娜是在“做别人”。
这一对恋人在人生观及生活态度上的差异,让他们的关系变得岌岌可危。结果发生了一件“狗血”的事情:戴维结识了另一个女孩,突然就发展成恋爱关系和性关系,和安娜分了手。
戴维和新女朋友瑞秋(化名)是偶然认识的。瑞秋已经从大学里退学,以在酒吧里打零工为生。瑞秋认为上学、上班、稳定的关系,都是“生活的圈套”。
在戴维眼里,瑞秋简单、活泼,“永远活在当下”,不像安娜那样成天心事重重。
但是没过多久,瑞秋就展现出让戴维焦虑的“多面性”。的确,瑞秋更“重感情”,更愿意花时间和戴维在一起,情感表达也“直接通畅”,不像安娜那样“压抑”。但如果戴维没能及时接她的电话,没能在十分钟之内回复她的微信,她会勃然大怒,认为戴维不重视她,要抛弃她。起初戴维耐心安慰,瑞秋在情绪被安抚之后,又变得乐观、积极,对戴维充满爱意。戴维似乎也很享受和瑞秋这样“快意恩仇”的戏剧性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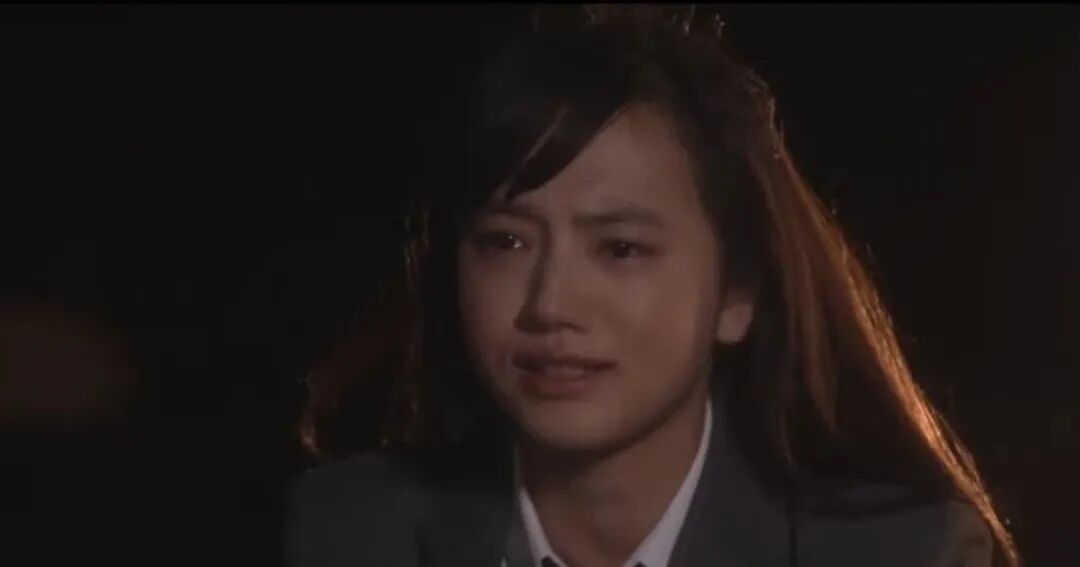
但当这类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很多次后,戴维对瑞秋的耐心也损耗了许多。于是瑞秋开始在她觉得戴维不重视自己的时候用刀片划自己的手臂——这是她在中学时期做过的事情,如今重又出现了。
在戴维这边,当然有许多朋友劝他和瑞秋分手,但是这段关系反而比他和安娜的更让他难以放弃。他觉得他和瑞秋之间有某种深刻的联结,离开瑞秋就是放弃她,会让他感到内疚。
虽然安娜、戴维、瑞秋这三个人的生活态度和方式迥异,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想要“做自己”。这种需求,用心理学术语描述,就是试图获得“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
自我同一性是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提出的概念,它是青春期青少年的核心发展议题。在青春期,比之于其他年龄,人类更容易思考“我是谁”“我想成为什么”之类的问题。一些人在青春期对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答案,能够把自己的动机、能力、信仰和社会角色整合起来。获得自我同一性的人,会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特的个体,感到自己的过去、现在、将来是统一的,感到自己的不同部分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而另一些人即便青春期结束,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不稳定或者不满意的。没有获得自我同一性的人即便成年,也依然会无休止地消耗在内心冲突、难以实现的欲望或者空虚感里,他的价值观可能并不自洽,他与他人的相处也比较困难。

未能获得自我同一性的个体有三种典型的心理状态,心理学家马西亚(James E. Marcia)概括为同一性早闭、同一性延缓、同一性扩散(又被译成“同一性紊乱”)。
安娜对戴维的评价是有洞察力的。戴维用他人的期望代替自己的探索,与其说是在“做自己”,倒不如说是“没有自己”。通过心甘情愿地躺在权威的意见里,生活仿佛是面对一道设计好的填空题,只要把参考资料上的答案一个个填上去就好了。这种方式关闭了自我同一性的进一步成长——在青春期及以后,个体本可以发展成一个独特、有创造性的人。
不过对于戴维,我们也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同一性早闭”也让戴维活得心安理得,内心少有冲突。我们似乎也没有权利批判他的“不成长”。毕竟,以这种方式度过一生的人其实是人群中的多数。虽然同一性早闭的个体可能会出现激烈的中年危机和老年期对自己的失望,届时也可以求助于宗教和玄学以度过心理上的难关。在可见的将来,这种生活方式恐怕依然会占据主流。
只是,戴维“不幸”碰到了安娜和瑞秋,两个虽然在自我同一性方面的发展碰到了困难但至少没有放弃探索的人。在碰到安娜时,他还可以因为安娜的疏离而抱持内心的稳定,等到他遇到瑞秋,他的自洽受到了挑战,他的社会面具下对自由与个性的渴求被搅动了出来。只是他无法应对瑞秋的“同一性扩散”,就像一个只学过算术的学生无法帮另一个学生解决在微积分课程上遇到的困难。
瑞秋努力“活在当下”,放弃对生活长远的安排,其实是在努力反抗来自他人的定义。他人可能很难理解瑞秋如此强烈地反感“正常的”生活。但是从她特殊的成长经历,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动因。

瑞秋在6岁以前由祖父母抚养,父母在南方打工。6岁以后父母回到家乡工作,瑞秋也开始上学。在7〜12岁之间,瑞秋便在父母的近距离“监控”下生活。在6岁之前几乎没有照顾过瑞秋的母亲此时却变成全职母亲,全方位地塑造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习惯,控制她的人际交往和一言一行。瑞秋一度成绩优秀,举止文雅,成了好学生的典范——当然瑞秋也会暗中和母亲较劲,对抗母亲近距离的控制。毕竟瑞秋的性格冲动且敏感,对于高控制的父母的感受经常是负面的。
亲子关系的高控制和性格的高敏感的冲突在瑞秋青春期格外激化——高强度的控制让瑞秋做出许多冲动性、攻击性甚至破坏性的言行以对抗控制,而这些冲动性、攻击性和破坏性的言行激起父母的不安,他们便采取更为严格的控制,由此进入了恶性循环——结果瑞秋无法真正进入自我探索,发现自己的独特性,而是在极端紧张的环境里努力对抗,保护自己的主体性。
15岁的时候,瑞秋的父母突然离婚,各自去外地工作,瑞秋回到了祖父母身边。其实此时祖父母已经老迈,无法起到教育者和养育者的作用。瑞秋在学校里和老师、同学的关系都非常紧张。瑞秋“放飞自我”的生活就此开始。
同一性扩散的发展背景,不只是瑞秋碰到的这种情况。长期的被忽视、霸凌、家暴、性侵等创伤都可能在未成年人的不同发展阶段削弱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信任感,让他们难以确定自己是不是“好的”,难以维持稳定的人际关系,为青春期的自我同一性扩散埋下伏笔。

缚于“必做清单”的安娜,不希望停留在过去的自己,希望能够发展潜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但她努力的方式相对幼稚,表现出同一性延缓的特点。青春期自我同一性发展比较顺利的人,到了大学阶段,基本上能够结合自己的能力、性格、兴趣以及其他条件,对自己的发展有一个大致的展望,不会紧跟周围人的行动而行动。
不过,考虑到以高考为指挥棒的应试教育环境,如果一个青少年在这种环境下还能及时地完成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反倒是难得的例外。即便如此,安娜寻求自我成长的具体做法,与其他“同一性延缓”的同龄人相比,还是显得更幼稚一些。
安娜的心态有点像3岁的孩子。此时的孩子已需要和同龄人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做着同样的事情。这是他们的“平行游戏”阶段,他们热衷于“一起来做游戏”,一起滑滑梯、玩沙子、荡秋千,互相模仿,互相激励,相互“攀比”。但这个阶段的孩子并不具有真正的相互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随着年龄的增加、阅历的积累,孩子们逐渐拥有自己的个性与习惯,不那么需要和别人“一模一样”了。“人有我有”固然好,“人有我无”“人无我有”也是可以的,因为有差别,才相互需要、相互支撑。他们会开始不喜欢太听话的人(这种心态在9岁时会突然变得激烈)。他们甚至会因为自己和他人的雷同而感到不安(这种心态在青春期表现得最明显)。

如果断然说安娜的“心理年龄”是3岁,我们对安娜的理解就过分简化了。毕竟安娜有持之以恒的成就动机,这并不是3岁的孩子所有的。她也有一个21岁成年人所具有的完整的智力和人际边界感。我们可以说,安娜的人格浸透着3岁孩子的心态,她有幼稚的一面。
安娜曾是原生家庭中“最不受父母待见”的孩子,很少被父母关注,但凡有被关注的时候,就是父母对她批评挑剔的时候。她似乎总要提醒自己必须参照“好孩子”的标准努力改善自己,以避免被指责。进入幼儿园和学校以后,她的这种谨小慎微的态度延续了下来,并且被强化了——学校、老师、同学当然比家庭里的他人更难以捉摸,关系也更加复杂。
自我同一性的发展所经历的环境,最初是原生家庭,然后是学校,之后是工作环境和社会生活。个体在这些环境里的每一步成长,都可能被环境所促进,但也可能落入困境而停滞或紊乱。这并不意味着自我同一性发展的最好条件是无挫折的顺境。“泼天的富贵”“少年得志”“赢在起跑线上”⋯⋯诸如此类令人羡慕的积极体验,经常同重大的创伤一样延缓了青少年的自我同一性的发展。过于积极的体验会让青少年依赖于外在的奖励、他人的目光、及时的满足和极端的刺激。

获得了充分的自我同一性的人,往往是经历过诸多挫折,但又未被挫折所打败的。唯其如此,他对世界的理解才比较贴合真相,他的自我才比较牢固,他的“做自己”才不是逃避的借口或空想的口号。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36期封面故事)

排版:球球 / 审核:小风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大家都在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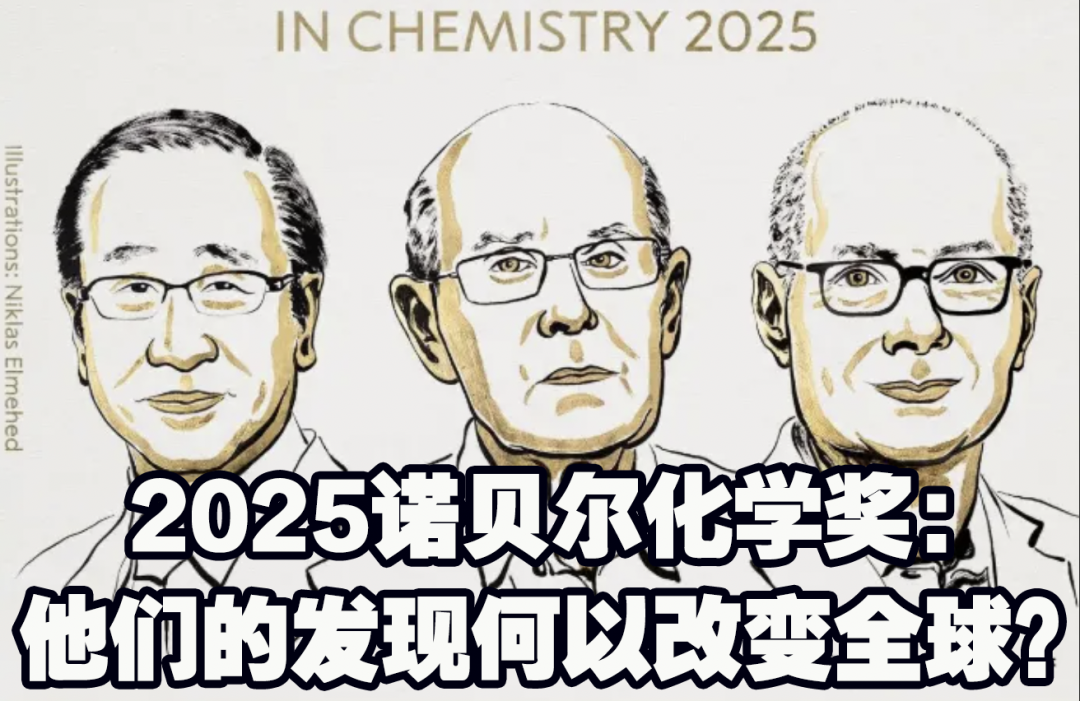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1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6158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