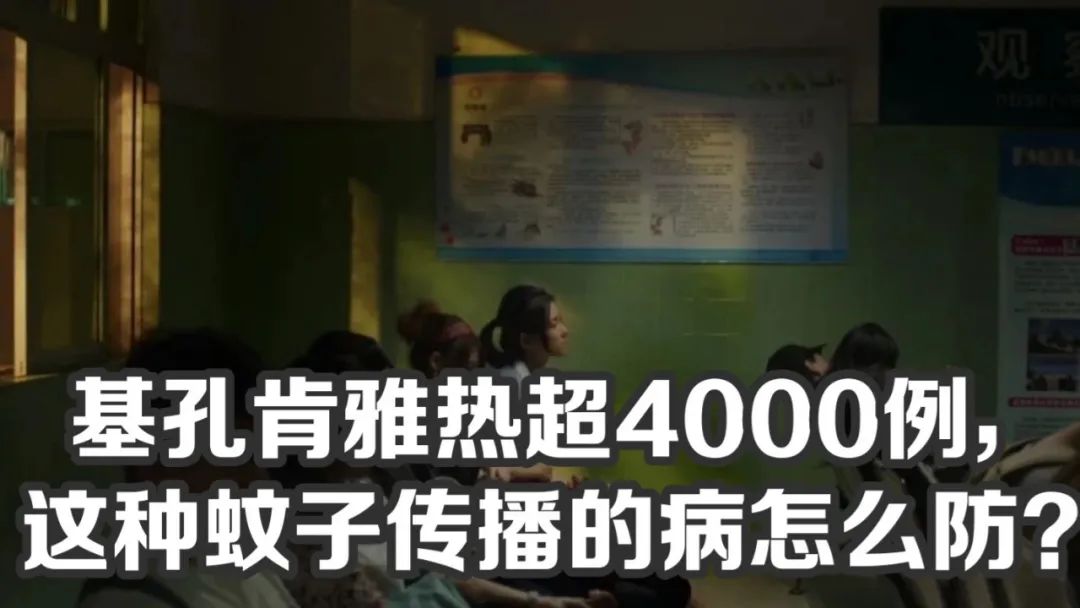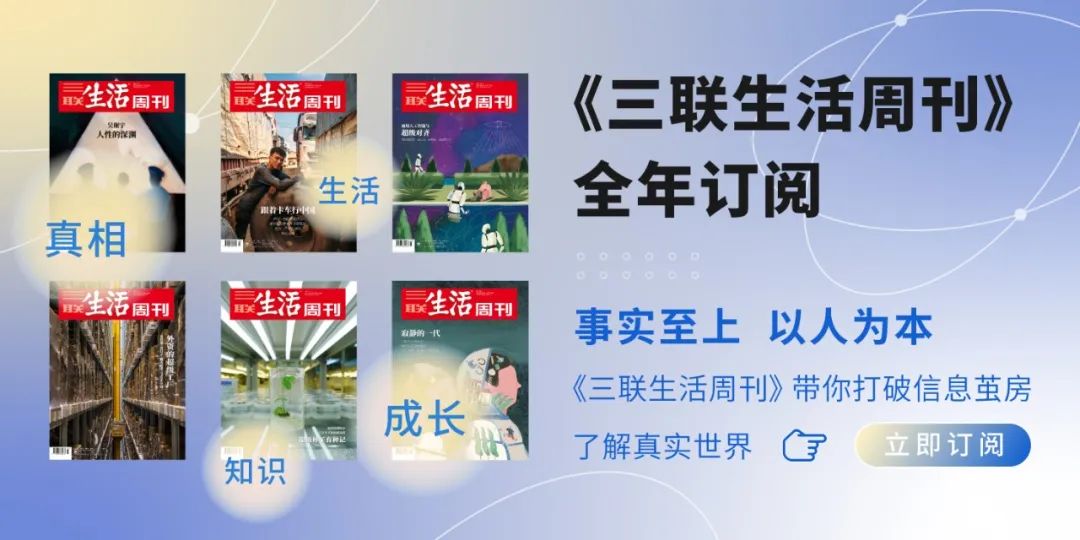“全员神演技”国产片,也没拍透“东亚小孩”的创伤?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7-28·阅读时长22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由张子枫、马伊琍主演的《花漾少女杀人事件》(下文简称《花漾少女》),是新人导演周璟豪的长片首作,曾入围第78届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电影直面优绩主义对于东亚亲子关系的扭曲,以及花漾少女充满疼痛的抗争。张子枫和马伊琍贡献了一流的表演。
电影拥有不错的完成度,但失之于烂尾——将母女关系收束于“你情我愿”的虚假和解。
文|从易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
由张子枫、马伊琍主演的《花漾少女杀人事件》(下文简称《花漾少女》),是新人导演周璟豪的长片首作,曾入围第78届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电影直面优绩主义对于东亚亲子关系的扭曲,以及花漾少女充满疼痛的抗争。张子枫和马伊琍贡献了一流的表演。
电影拥有不错的完成度,但失之于烂尾——将母女关系收束于“你情我愿”的虚假和解。
文|从易

扭曲的亲子关系
电影围绕花样滑冰选手江宁(张子枫饰)展开。她在单亲家庭长大,母亲王霜(马伊琍饰)也是她的教练。职业生涯的最后机会近在眼前,江宁正拼尽全力训练,渴望抓住这扇可能会关闭的门。
天才少女钟灵(丁湘源饰)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平衡。钟灵仿佛天生为冰场而生,轻盈灵动的姿态很快吸引了王霜的目光,她将更多关注投向钟灵。
三人的关系变得微妙。看着钟灵轻易就完成了自己苦练多年的动作,并夺走母亲的关注,江宁内心的焦虑与不甘日渐累积。最终,压抑爆发——深夜的冰场上,锋利的冰刀划过钟灵的脖颈,花漾少女“杀人”了……

江宁与钟灵的关系,让人联想到《黑天鹅》中妮娜与她想象中的竞争者,不同的是,《花漾少女》中母女关系的重要性先于江宁与钟灵之间的关系,张子枫与马伊琍强大的表演,更加凸显出了母女关系的存在感。
当然,如果将电影中王霜换成父亲,一切仍是成立的。在路演时,有观众提问电影中为何没有出现父亲的角色,导演周璟豪的回答是,他在调研中确实发现更多孩子,是由母亲在陪伴训练,“但电影中没有父亲的角色,跟表达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新人导演的第一部作品,人物关系我希望简单一点”。
电影并非单一地刻画东亚母女关系,而是聚焦于一种更广泛、更普遍的,被优绩主义扭曲的东亚亲子关系。

优绩主义虽然是在20世纪才广泛流行的概念,但这种概念将成功视为个人奋斗的结果、将失败归因于努力的不足,在东亚社会早就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长期依赖单一的评价标准,比如考试成绩、学历背景、薪资水平等等,来衡量人的价值,所有人被迫朝同一个方向拼命奔跑。在学生时代,我们大多经历过“唯分数论”,不论你是走传统的读书道路,还是选择练体育、学围棋、练花滑,成绩几乎是唯一的判断标准。
优绩主义也深刻影响了东亚的亲子关系。在很多家庭中,孩子是否“优绩”,是父母给予爱的前提,父母对孩子的爱和孩子的表现挂钩。孩子成绩好、考上好学校、找到体面的工作,父母就会更满意、更疼爱;如果孩子表现平平,父母就会失望,会发火,会打骂。“有条件的爱”让很多孩子从小就感受到压力,觉得必须优秀才能得到父母的认可。
王霜对江宁的态度,取决于江宁在冰场的表现。江宁的每一次跳跃和旋转,都在接受绩效评估。江宁在冰场摔倒或者表现不佳,王霜的态度就是“冷暴力”——冷漠、冷眼、无视,或者是冷言冷语的回应——你都这么差了,我还有什么训练你的必要?坦白讲,看到王霜对江宁的“低气压”我心有余悸。父母对孩子的“冷暴力”(冷漠、忽视、拒绝沟通),有时比单纯的批评和发火对孩子的打击更深,因为这是一种情感上的虐待和剥削。

钟灵出现后,天赋异禀的她轻松完成江宁苦练多年的动作,并迅速成为王霜的新希望。王霜表现对江宁的“抛弃”,暗示女儿不再是最优选择。这种“可替换”的逻辑,不仅否定了江宁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也否认了江宁作为母亲女儿的不可取代性。在优绩主义体系下,竞争取代了情感连接,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父母以“别人家的孩子”来刺激自家小孩,甚至社交平台上“大号废了,练小号”的说法也颇为流行……虽然家长多是以玩笑的口吻,但这些说辞本质是对孩子的情感虐待。
当父母以爱的分配与否来操控孩子的喜怒哀乐,孩子的主体性或被绞杀,像江宁一样陷入精神分裂状态并不意外。花漾女子“杀人”,只是少女精神崩溃后的幻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在优绩主义的渗透下,由东亚家庭扭曲的亲子关系所导致的悲剧不时发生。受害者可能是一个天才围棋少年,也可能是一个培养出名校高材生的家长。

东亚“疯”女孩
《花漾少女》并不只是一个东亚母亲把学花滑的女儿“逼疯”的故事,也是一个为了技艺“不疯魔不成活”的故事。
在《黑天鹅》和《爆裂鼓手》中,也存在把主人公“逼疯”的角色,但这个角色不是母亲。主人公对于“疯”的状态是“甘之如饴”的,为了抵达艺术的更高境界,他们甘愿忍受被逼迫、被打压的痛苦。用我们很熟悉的话说,就是“不疯魔不成活”,为了“成活”,他们甘愿“疯魔”。

《黑天鹅》剧照
“不疯魔不成活”出自京剧行当,但它也是艺术创作领域的经典准则,即,如果不达到痴迷疯癫的状态,就很难在行当里实现突破。它指向一种极端投入的创作状态——创作者必须将全部生命能量灌注到艺术中,甚至模糊现实与艺术的界限,才能产生打动人心的作品。
不论是《霸王别姬》里的京剧,《黑天鹅》里的芭蕾舞,《爆裂鼓手》里的鼓手,《追月》里的越剧,还是这一次《花漾少女》中的花滑,这些技艺的本质,是对“艺术规律”的掌握与重构。常规训练只能达到熟练,“疯魔”状态下,技艺占据了个体,个体不再是技艺规律的模仿者,而是技艺规律得以显现的载体。换句话说,一个“疯魔”的表演者会从“有意识控制”变成“无意识运用”,个体与技艺合而为一,痛苦与狂喜同时降临。
比如从三观的视角评判,《爆裂鼓手》中的魔鬼导师弗莱彻就是一个大变态,把男主角当“狗”一样训。可男主角为何不逃离?因为对技艺精进的渴求,已经变成他的一种内在强迫。常规状态下的快乐多依赖外部反馈(如认可、奖励),而“疯魔”中的快乐源于主体对自身创造力的直接确证,具有纯粹性与自足性,成为支撑他忍受痛苦的核心动力。只是,“不疯魔不成活”从来都具有两面性。当对技艺的追求压倒一切时,个体的其他维度,比如情感、社交、健康等,可能会被系统性忽视,从而变成对创作者生命整体性的某种剥夺,好像其他快乐都不快乐了。

《爆裂鼓手》剧照
这种“不疯魔不成活”的状态,也存在于江宁身上。
母亲一直在逼迫她、情感剥夺她,但江宁甘于忍受,也未曾真正反抗。电影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江宁屡次向母亲主动提及训练,有时候没有训练时,她怀疑母亲是在故意惩罚她。这既说明江宁成为“训练机器”,同时也说明,每天上冰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当江宁无法突破三周半跳,一次次重重摔倒在冰面上,她就一次次重来,她从未因为打压或失败,而对花滑产生厌倦,对冰面产生恐惧。她是爱花滑的,她渴望突破,当她顺利完成一次三周半时,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她表情闪过的那难得的笑容——不是普通的快乐,是一种突破关卡的、释然的、自由的、成为主宰者的快乐。
坏处是,江宁与《黑天鹅》里的妮娜一样,走向了精神分裂。为了实现技艺上的突破,她分裂出一个竞争对手钟灵,更催生出了个性中的黑暗人格。她嫉恨钟灵,举报她,在无法毁掉她后最终“杀”了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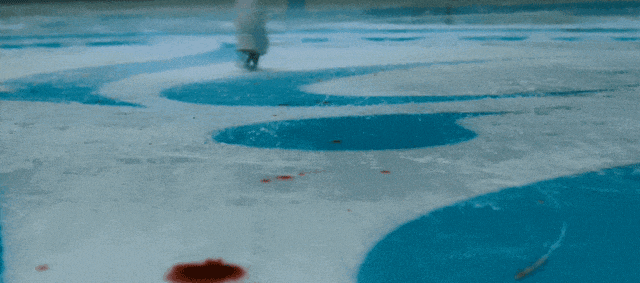
但江宁又不完全等同于妮娜,她终究是一个东亚小孩。对于一个东亚女性来说,对于某种技艺的追求,意义并不只局限于技艺本身。
这让我想起了帮助何赛飞拿到2023年金鸡影后的《追月》。何赛飞饰演的戚老师对越剧极致投入与痴迷,但她从来都不是一个完美的女性。早年她以肉体交换演出机会;后来她前往省城发展,除寄钱外,对三个孩子近乎“自生自灭”般疏于照料;女儿未婚先孕时,她仅让儿子带女儿去打胎,自己则赶去北京完成演出,间接导致儿子入狱、女儿精神失常……电影打破了东亚社会对女性贤妻良母的主流期待,塑造出一个为追求艺术理想,不惜牺牲家庭责任、充满野心与自私的女性形象,促使观众反思母职与个人实现的矛盾。

《追月》剧照
江宁不是一个所谓的“温良恭俭让”的女孩,她充满野心,从不掩饰对胜利的渴求,不回避竞争中的阴暗心理,不将欲望包装成“被迫为之”的无奈。但也恰恰是她这种有些“疯”的精神状态,让她没有被母亲的打压完全摧毁。试想一下,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东亚乖女孩,很难扛住一个王霜式母亲的冷暴力,但江宁的叛逆和野心让她始终保持着一种尖锐的自我意识——哪怕这种自我意识是扭曲的。母亲用冷暴力逼她训练时,她用更疯狂的练习怼回去,母亲把希望转移到钟灵身上时,她不是自怨自艾,而是用极端手段清除这个对手……
这样的“疯魔”非常痛苦,无异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不乖”,或者说“疯”一点,有时也是弱者仅有的抗争了。
虚假的和解
观看《花漾少女》时,我的心情一直很复杂。我确实在这部电影中看到很多经典电影的影子,但导演在学习借鉴其他影片的基础上,加入的那些我们能感同身受的“东亚式”观察和表达,也值得鼓励。
直到电影行进到收尾时刻,导演直白又冗长地揭示江宁与钟灵的关系时,“担忧”成了我最主要的感受——这部电影是不是要收不住了?

《花漾少女》终究不是又一部《黑天鹅》或《爆裂鼓手》,它的核心不是对于追求艺术过程中,极致痛苦与极致快乐并存的探讨。所以,这部电影不需要一个“团圆”或“圆满”的结局,电影必须以母女一方的相对胜利,来实现对某个主题的极致表达——要么是母亲“胜利”了,扭曲的亲子关系最终泯灭了一个东亚女孩,要么是女孩“胜利”了,她以“疯魔”完成对扭曲亲子关系的突围,让母亲在失败中痛苦并反思。一旦电影是某种“圆满”,电影就变成囫囵吞枣——什么都有一点,最后什么表达都不极致,落入了空洞。

很遗憾,《花漾少女》走向这个糟糕的结尾。
王霜向江宁坦白,自己从未具备夺冠实力,自己的职业生涯也并非因为江宁而结束,并出于保护女儿的目的,她主动希望女儿可以终止比赛。这个转变突兀且割裂。前90分钟里,王霜是那个会冷眼看着女儿摔倒在冰面头也不回的魔鬼教练,是用“你毁了我的职业生涯”绑架女儿的母亲,是一个屡次无视医生警告、利用女儿的精神分裂来刺激女儿出成绩的偏执狂,何以到了这时,她突然推翻了自己十几年的执念?这种坦白来得太过轻易,仿佛之前那些歇斯底里的控制、那些近乎虐待的严苛训练,都只是一场可以随时遗忘的噩梦。被父母伤害的“东亚小孩”,需要的不是这种轻飘飘的和解。
江宁也“原谅”了母亲,她坦言自己想赢,自己需要母亲的逼迫,“如果没有一个压迫的母亲,我又如何开脱呢”。这相当于母亲的打压合理化了。事实上,那个松弛的钟灵本就是她,热爱和野心足以成为江宁的驱动力,反而是因为母亲的打压,她不能真正放松地享受花滑。

所以,江宁知道真相的这一刻,应该是她挣脱母亲控制的时刻,是她夺回主体性的时刻,不是什么母女“你情我愿”的和解时刻。现实中,多少人在打压下崩溃?多少人的热爱,在打压下变成“憎恶”?多少人即使取得成就,仍要花费一生去治愈童年的创伤?
《花漾少女》以“东亚”的框架,重新诠释一些经典的类型故事,这可以帮助新人导演找到一条可以借鉴的叙事路径,并承载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以更本土的议题打动国内观众。可惜的是,电影虽然敏锐发现了很多问题,但它无力解答,“包饺子”的收尾消解了前90分钟建立的批判力度,系统性压迫烟消云散,就像握紧的拳头打在棉花上,那些让东亚观众感同身受的窒息感,一下子就坠入虚无。

排版:小雅 / 审核:雅婷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大家都在看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4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6137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