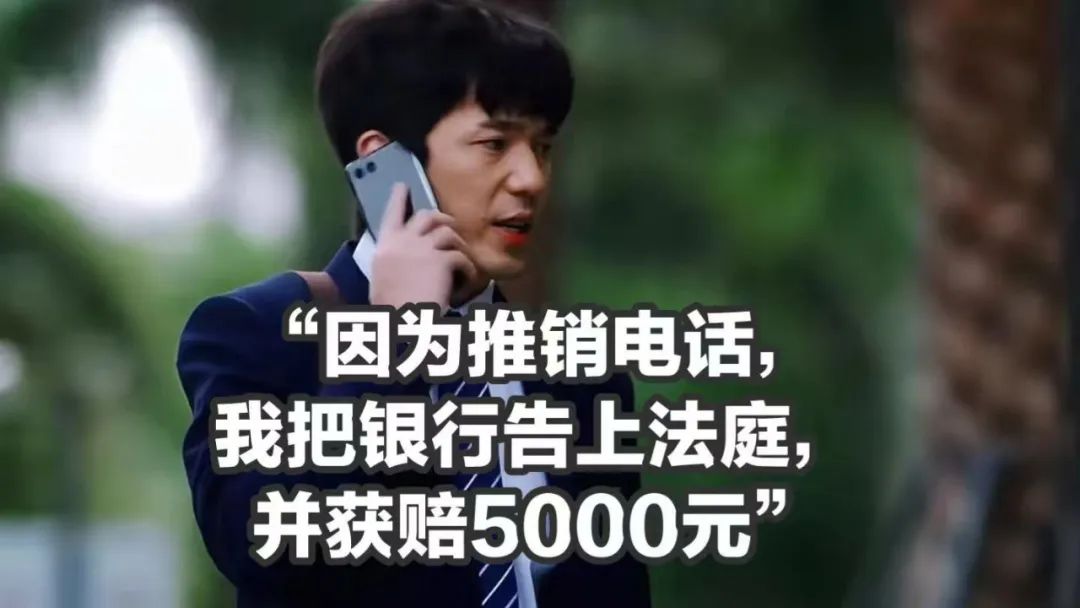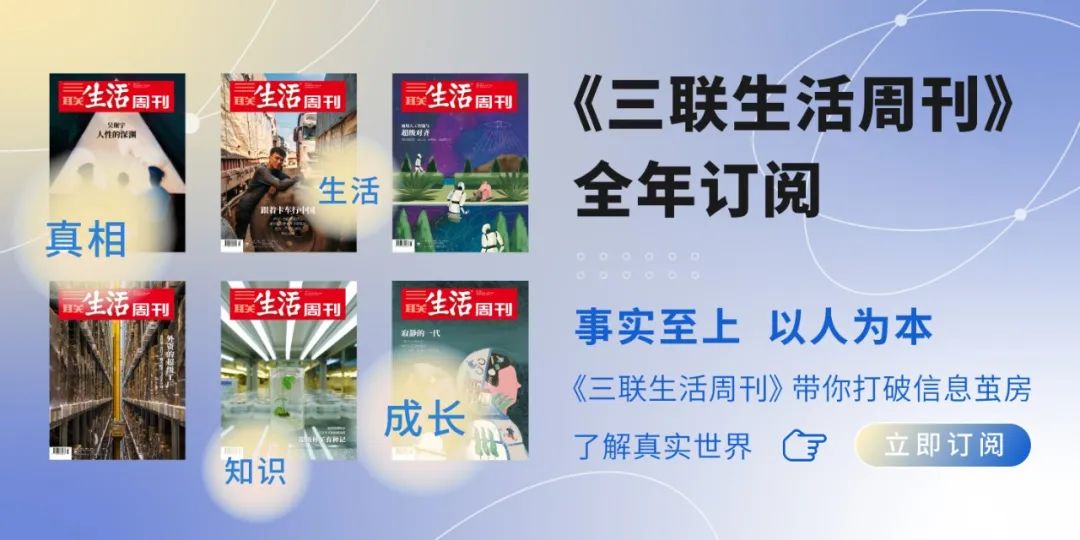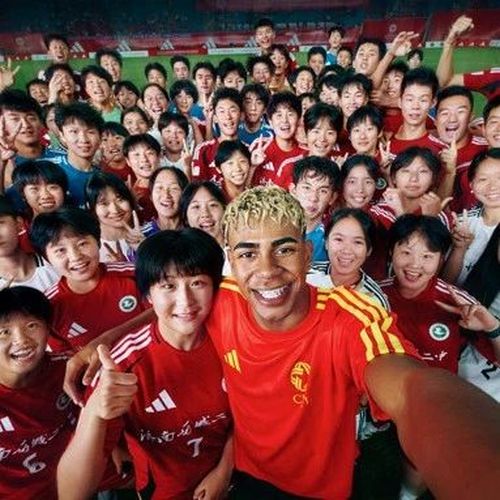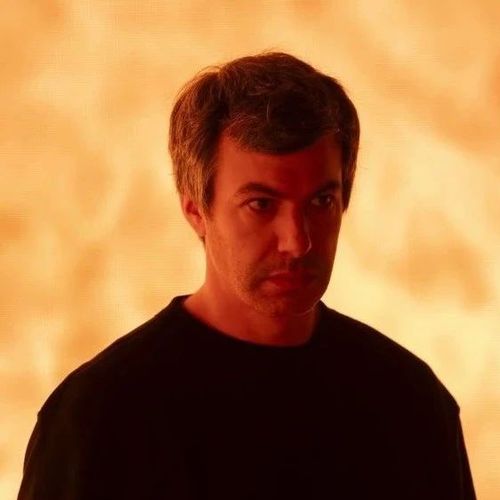被年轻人追更的老年回忆录,为什么好看?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7-11·阅读时长21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写回忆录这件事一度是名人的专属,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尤其是老年人,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人生。他们在纸上写,在公众号、小红书写,甚至找人代笔,将自己的故事整理成册。这些回忆的主体,并非是充满戏剧性的人生,他们是普通的教师、退休工人或家庭主妇……他们借由回忆录的讲述,与过往和解,与家人重新建立情感链接,也重新确认“我是谁”。
我们与三位“写”回忆录的老人聊了聊,他们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身份背景,写作方式、讲述对象和记录者也各不相同,却都不约而同地在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一个人?”我们总在关注宏大的议题,但身边无数奋力生活的普通人,他们的故事也值得被记录,真实的生活,往往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写回忆录这件事一度是名人的专属,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尤其是老年人,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人生。他们在纸上写,在公众号、小红书写,甚至找人代笔,将自己的故事整理成册。这些回忆的主体,并非是充满戏剧性的人生,他们是普通的教师、退休工人或家庭主妇……他们借由回忆录的讲述,与过往和解,与家人重新建立情感链接,也重新确认“我是谁”。
文|旷晓伊
文|旷晓伊
71岁 楼小莉:直播是留给自己的档案
一年前,71岁的楼小莉开始在直播间讲自己的故事。
她本以为自己没什么话可以说,没想到这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她讲和蔼的姥姥,要强的母亲,出嫁后的婆婆,再到后来成为母亲的自己,顺着记忆一层层讲下来,像剥洋葱似的,轻而易举地将那些有着浓烈味道的场景和细节一一具象在观众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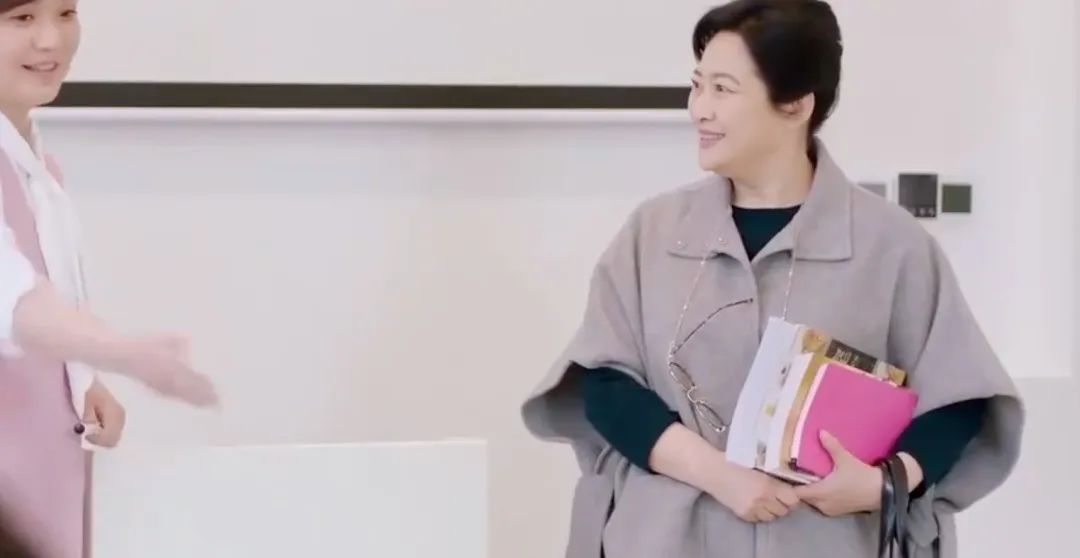
《爱的厘米》剧照
镜头里,楼小莉的情绪一直很饱满,总是笑得开心,毫无阴霾之色。讲述时,她习惯用“那时候”这样的句式开头,语气平淡,内容密密实实,几乎没有停顿。她的声音不高,但很稳,或许是早年做电台主播留下的底子,让人很想继续听下去。
楼小莉还把自己的故事写在公众号上。她给自己定下目标,每周更新两次推文。写作的主题并不固定,有时是幼时犯错被母亲责罚的片段回忆,有时追忆多年失联的老友,又或者是某张泛黄老照片承载的往昔故事——想到什么便写什么。
她写自己童年瘫痪后“借腿”的趣事。那会,楼小莉才五岁,坐在青岛黄台路的窗边,望着波螺油子(地名,位于青岛市市北区与市南区交界线上的胶东路)的方向发呆,想念姥姥,想着想着便灵机一动用几颗糖果“贿赂”街头玩弹珠的男孩,请他们轮流背自己去见姥姥。一路上,糖盒哗啦作响,像旧人力车的铜铃声。七八里路,几个少年满头大汗,终于把她送到门前。姥姥一把将她搂住,泪水瞬间涌出脸上的褶皱。
“我也不急,就慢慢写,”她说,“最后把这些文字像珠子一样串起来,编成一条项链,就是一本回忆录。”
讲述自己的人生,并不是楼小莉突然的冲动,而是一个在她心中潜伏多年的想法。
20世纪90年代,她还在青岛电视台工作时,曾与某作家有过一面之缘,“他说我是个有故事的人,让我写自传。”楼小莉回忆,“他还说,如果我不愿意写,可以找人代笔,再拍成电视剧。”但那时她才四十来岁,觉得自己“根本还不够格”。

《春潮》剧照
嘴上说着不写,心里却悄悄种下了种子。后来,楼小莉离开电视台,去了上市公司,又创业,做公益,在监狱做劳动改造教导员,一路忙个不停,直到退休。那些年,她的故事越攒越多,种子也慢慢发了芽。也许,是时候给自己写点什么了。
楼小莉是个要强的人。多年来,她的心里始终憋着一股气:她想证明,“我是有价值的。”自从5岁那年因病瘫痪起,她就感觉自己始终被社会轻视。不能和别的孩子一起外出玩耍,成年后找工作也屡屡碰壁。“一听我是残疾人,很多人就摇头。”她记得自己下岗那会儿的艰难,心里满是无力。
但现在,不一样了,她靠自己的努力,一路从普通的女工,做到上市公司的总经理,还创立过自己的公司,实现了可观的财富。她想写下来,关于这一切。
楼小莉准备得很充分。她先是花了七八千块购买了网上的回忆录写作课程,边听课,边把回忆录的框架拉起来。后来,有志于做回忆录事业的宋教授在网上看到了她分享的经历,主动联系了她。一个有故事,一个有平台,两人一拍即合。宋教授邀请她每周一起直播,慢慢把自己的故事说给大家听。
写作的过程并不轻松。由于长时间用手机直播、改稿,楼小莉的视力大不如前,另外,腰椎老毛病也让她无法久坐。为此,她特意买了台可以躺着用的笔记本电脑。“现在年纪大了,每天用手机改稿,眼睛有些吃不消。”她如是说道。
困难那么多,但她从未放弃过书写这件事。她不太喜欢“写书”这个词,觉得太大了。但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写的东西,是留给自己,也可能是留给后人看的。她说:“写回忆录,是我自己的档案。不是单位那种格式化的档案,是有感情的,有思想的。那些话,有时候不在话里,只能在回忆里写出来。”

《我能说》剧照
写着写着,很多时候,她会想起从前那些大悲大喜的瞬间,想起曾经在生活中想不通的事情,想起自己因为瘫痪被别人瞧不起的那些时刻,写着写着,那些曾经的痛苦纠结也仿佛穿梭时光一一被文字抚平。
“我想给自己有个交代。年轻时,我是为了摆脱被轻视的处境,如今,我更在乎的是:自己是否真正成为了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我的这些经历写出来,如果能给社会上其他人有一些正向的作用,那就更好了。”聊起自己坚持写作的动机,楼小莉如此回答。
80岁 徐家树:我想追问我的人生
相比“证明自己”,80岁的徐家树在写回忆录时更关注“我之所以成为我”的内在过程。
他是一位知名摄影师,尤擅拍摄西藏的人与风景。过去几十年间,曾多次深入藏地,出版了多本摄影集,并曾荣获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第130届国际摄影展银奖、美国《Communication Arts》杰出摄影奖(1992年)等多个国际奖项。
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后又在澳大利亚定居多年,在写回忆录的过程中,徐家树想弄明白,为何自己对遥远的西藏如此着迷,“为什么几十年来我会一次次地踏上那片土地?我想搞清楚这个过程。”
契机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偶然机会,他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样一段经历——他初到藏地时,看到“街道两旁的藏民,跪倒在路边,双手合十,伏身在地。我们的吉普车缓缓驶过,周围变得异样地宁静——只有车轮碾压碎石的咔咔声,以及藏民口中的诵佛声。我惊得目瞪口呆,心怦怦直跳,唯一能做的,是本能地双手合十,默默祈愿。”这样的景象震撼了我,我想去探索这片神奇高原上的风土人情,读懂他们的文化与敬畏。

《飞跃老人院》剧照
写回忆录,也就最近三个月的事情。徐家树在小红书上,每日更新一千字,至今已更新100多篇笔记。“我今年80岁了,觉得也该写点什么留下来。”另一个原因是,他意外发现,母亲在30年前写下的《山居杂忆》这本书几次再版后,许多读者好奇书本之外的故事。徐家树很惊讶,没想到二十年后还有读者朋友对自己家族的故事报以如此浓烈的好奇,但母亲早已过世,“我就想,干脆自己写。”
要从哪里回溯自己的人生呢?
徐家树想到了一张老照片,那也是他目前主页的头像:1945年,母亲高诵芬怀抱一岁的他,站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家的花园里。那一刻被永久定格下来,也成为他记忆书写的起点——一个孩子的人生,被包裹在母亲的怀里,站在时代的门槛上。
也许是工科出身的缘故,徐家树不喜煽情,也不追求结论。他阅读大量自传体回忆录,从蔡澜到诺奖得主,并反思写作形式。“我不喜欢母亲那种按事件写的方式,更希望梳理出人生的整体脉络。”
他的写作像“流水账”,从五六岁写起,想到什么写什么,尽量克制,不掺杂情绪与评判。“我只是记录我所见、所做,尽量真实。”徐家树觉得,既然是口述历史,就应该让读者自己去理解。
写回忆录,也让他重新连接起许多旧友。有些细节记不清了,他就去问大学同学,对方补充的片段常常让他豁然开朗。“有时候,你以为遗忘了的事,会在别人的一句话里回来。”
徐家树觉得,回忆录不是小说也不是论文,而是生活的证据。“经历得越多,人生越有厚度。”在耄耋之年回望过往,是一次与命运的和解,也是一种感恩。
羊子记录母亲:她也曾是一个小女孩
不是所有老人都像楼小莉、徐家树这样拥有强烈的表达欲,更多的老人们,鲜少有受到高等教育和工作的机会,他们大多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为家庭贡献一生,他们对生活里的变化早就习以为常。羊子的母亲黄培兰也是如此。但羊子想为母亲写本回忆录。

《姥姥的外孙》剧照
相伴五十多年,羊子总以为自己很了解母亲,直到202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那一年,患阿尔兹海默的父亲,在一次发作中将母亲摁在地上打伤。那个曾在下课后急不可耐回家探望妻女、几十年如一日宠妻的丈夫,一夜之间变得陌生而可怕。但母亲经过短暂的身心调整后,就又开始继续照顾他,继续张罗这个家。
为了方便照护,羊子和姐姐轮流回家和父母同住。几十年未曾共同生活的一家人,被迫重新适应彼此的作息、习惯、情绪。生活的摩擦层出不穷:洗澡时间、饮食搭配、谁几点睡觉、谁几点起床。母亲仍旧习惯操持一切,饭桌总是丰盛热闹,却也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这令早已习惯独立生活的羊子颇感不适。也就是在这时,她开始重新审视起自己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同一时间,羊子的女儿留学归来,决定创业,与羊子之间也产生了不少摩擦,“以前我总觉得她太能干了,什么都要安排好。但后来,尤其是自己成为母亲后,才明白,她只是用她能想到的方式,在尽力关心我们。”
既是女儿,也是母亲,这种双重的身份时常让羊子觉得割裂,尤其是在父亲的病情与日俱重的情况下,羊子突然发现,自己或许并不了解真正的母亲,还有自己。面对各种难缠的父亲,母亲没有崩溃也没有气馁,仍然保持耐心,那种沉稳,让羊子动容,也让羊子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她今天怎么变成了她?她年轻时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成了羊子决定写回忆录的起点——“我不仅想记录她的故事,更想通过写作重新认识她,也认识自己。”
她在网上找了一位回忆录写作者,和对方合作,希望母亲的故事被完整地记录下来。羊子说,照片和视频会消散,但文字可以留下来。“这些是写给下一代看的,让他们知道,外婆是个怎样的女人。”

《妈妈!》剧照
更重要的是,羊子觉得自己没有能量去与母亲摊开来进行更深度的交流。也许因为,她已经习惯在母亲的羽翼下不动声色地被照顾着,而母亲也习惯了强势地撑起整个家庭,尽管如今角色有所倒转,但两者间的位置并未转换。
她鼓励母亲讲一讲自己的故事。母亲一开始推辞:“我又没上过大学,也没当过干部,有什么好写的?”但话匣子一开,她便像换了一个人。
讲起年轻时的事,母亲会滔滔不绝。她说自己在学校是排球队的主力,冬泳时没有泳衣,就穿着短裤跳进水里;她说自己爱数理,曾和男生比着做题;她说她踩着缝纫机,帮全村人缝衣服补棉被……那些旧日的细节,被一一拾起,像电影画面般浮现。
“她不是一开始就是我的妈妈。她也曾是一个小女孩,一个有故事的人。”羊子说。
在为母亲“立传”的过程中,羊子也重新理解了三代女性之间的情感结构。她意识到,自己对女儿的期待,和母亲对自己的方式惊人地相似——“带着爱的小控制”。她停顿了一下,又说:“最重要的是,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在这种三代母女关系的夹缝中,重新认识了我自己。”
记录父母的故事,有时不仅是一次追溯,更是一次自我回望。
如今,羊子已经陪伴母亲进行了四次采访,每次都更加深入了解母亲,她计划在今年九月份之前完成这本回忆录,作为母亲八十岁生日的礼物。

排版:球球 / 审核:雅婷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大家都在看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4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6128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