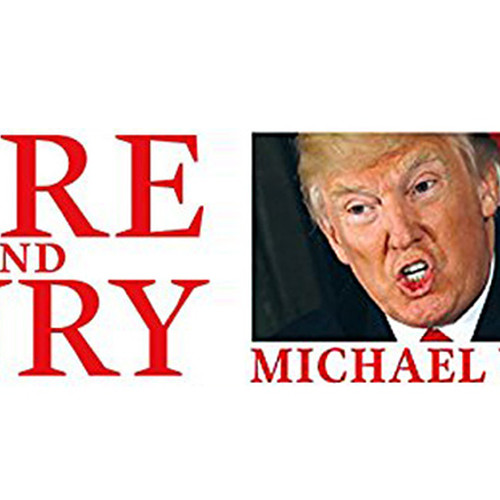金老师讲述:载沣的归隐
作者:钱业
2018-02-05·阅读时长8分钟
载沣:1883-1951,溥仪之父,晚清摄政王,大清最后的掌舵人
口述:金毓岚,载沣之孙,溥任之子
在普遍的认知里,溥仪登基那天的情形,像是一则高度戏剧化的预言。溥仪的父亲载沣在故事里,是预言家。
3岁的溥仪被载沣抱上龙椅,不停地哭闹,载沣安慰他:“快完了,快完了。”——大清快完了!
《我的前半生》里,溥仪采信了这种说法,像是主人公亲自承认了自身的古希腊悲剧式宿命。金老师说,他的父亲溥任也深信不疑。
可是历史或许是存在其他版本的。1908年12月3日的《纽约时报》在第四版记载了溥仪登基的过程。报道的副标题是“3岁的宣统独自爬上了龙椅”。“小皇帝独自走向龙椅,尽管脚步蹒跚,他并没有要别人帮助。”没有提及溥仪的哭闹。他向列祖列宗磕头、向太后磕头、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井然有序。报道的后面附了大清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国书,以及西奥多·罗斯福的回信。这是一场隆重、正式的皇权更迭。

历史是故事的先导,你阻挡不了它身后的千万种动人化身。但在即时即日刊载的新闻里,历史似乎还未来得及被演化为故事。
钱钟书说,“中国热得比常年厉害,事后大家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你看,所谓“兵戈之象”往往存在于后来的叙事里。
载沣曾被认为是历史的被动者,被动地发出了“命运的预言”。然而被低估的是他的政治洞见。他大隐隐于市,行到水穷,坐看云起。像历史的旁观者,宁静透彻。
1912年宣统退位,28岁的载沣主动辞去摄政王职务,承诺:再也不过问政治。“回家抱孩子了。”从此便真的和官场一别两宽,再无牵绊。
“祖父不是顽固的人。1915年张勋复辟,辫子军进京之后,载涛报告了我祖父,祖父表现得很冷淡。张勋见到他之后,一顿鼓吹,祖父愈加冷淡,张勋非常诧异。当时很多王公大臣跃跃欲试,觉得清朝又能复辟了。祖父没有这种幻想。谁也不能和他谈复辟的事儿,他最不爱听这两个字了。”
这种洒脱难得。谁都知道权力是最让人留恋的滋味。金老师笑说:“有些处长退休后,可难受了。”作别权力后以隐士自况,只存在于中国旧式文人的理想里。载沣将自己从权力纷争中解脱出来,倒是实现了陶潜以来中国文人最正统的归隐之梦。
诗人吟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金老师说,载沣确实没有做官的野心。当摄政王时自然勤勤恳恳,殚精竭虑,然而得放手时须放手,退隐是他的本心。
载沣是宗室当中嫡亲的皇族,传统文化的修养极好。他的绘画师从廖嘉玉,昆明人,好学问,是慈禧的绘画老师廖嘉蕙的弟弟。老醇亲王奕譞每天给老师置办一桌菜,等老师下课。虽然老师从来没敢吃。载沣给儿子溥任也请了如意馆的画师,学“清朝四王”的画。载沣给老师赏钱,少则二十块大洋,多则四五十块——当时二十个大洋就能买个院子了。载沣辞官后也没什么钱,仗着家里有些东西可以卖,也要给老师一个体面的赏。在展览中见过溥任的山水,他所承的是“南宗嫡支”的文人画。画中有禅意。魏晋以来的中国文人的“田园情结”是它的深厚底色。
辞退职务之后,载沣就安心在家里。由于当时北京局势不安稳,冯玉祥也咄咄逼人,1928年,载沣携子女搬到了天津,住了十一年。“没有住在日本租界,住在英租界里。葛登路13号,一听便是英国名字。”金老师2000年后陪父亲溥任去寻访旧址,发现已经被拆了。
退到天津之后,载沣就过一种很休闲淡定的日子。谢绝一切带政治色彩的造访,永远都是称病。就在那儿看书。“我祖父特别喜欢书,退位之后,不管多困难,都没有卖过一本书。但是解放后,他把7000多册书,一下子都捐给北大了。”载沣有两个印章,寄托心境,似乎颇为自足。一块刻“书癖”,一块曰“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
不是逃避、寂灭,是真的平静、豁达,物我两忘。

溥仪是载沣唯一的心病。因为溥仪在东北做皇帝梦,载沣叫也叫不醒的梦。
“九一八”前,载沣劝溥仪不要轻举妄动,溥仪没有听,到了“伪满洲国”,当了“皇帝”。
1935年,载沣带着溥任去了一趟满洲国。回来之后,记挂着两个儿子都在东北,几个女儿、女婿也都在,载沣心情郁闷寡欢,同时又很庆幸自己没有留在东北。“满洲国总理郑孝绪他们当时都极力想把我祖父留在东北,给他许了一个虚职:满洲国文化大臣,一个月能有一万块钱。对我祖父来说,当时确实没钱,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能有这笔进项,生活能有很大的改观。但他坚决回来了。”
载沣从东北回来之后身体就不好,腿走不动了。他又刻了一块印章:幸如塞翁。意思是自己动不了了,别人也就不好麻烦我了,不叫我出去干什么了。他没有悲于身世,愤于时事——他居然还在说“幸”!
只有金老师读懂了他:“这是很心酸的,谁不想健健康康的。”
载沣和溥仪的关系,是真正的父子关系。他们有着正常的情感纽带,也有父亲对于儿子的深切担忧。
他们之间,“父子”一直是超越“君臣”的,在后人对权力的异化的想象里,才拼凑出了父亲向儿子磕头称臣,自称奴才的场景。
“溥仪即位之后,仍然是按照父子之间的礼节向祖父行跪安,有人说,祖父见到溥仪之后要磕头,绝没有这样的事。清朝也没有这样的规矩。我曾祖见光绪,也绝不会向他磕头称臣。百官向溥仪朝贺的时候,我祖父是回避的,不出面。”
载沣在天津的公馆对外佯称“王公馆”,大家都不是很理解。金老师后来给琢磨出来了,这不是周吴郑王的王,是醇亲王、摄政王的王。载沣后来在任何的场合,不是用醇亲王,就是摄政王。“祖父生日,溥仪给他的寿礼,我见过几件,都是写‘摄政王殿下’,或者‘醇亲王殿下’,落款宣统。”
他们之间有祖制、人伦,礼数有序,断不会落下给旁人的笑柄。
1938年天津发大水,载沣住的公馆损失惨重,两代醇亲王收藏的珍贵的书画和书籍毁了很多。摄政王的金印也在那场洪水里找不到了。“这是我祖父最着急的事情,命我父亲带人无论如何得把这印给找回来,万幸的是,水一冲又把印给冲出来了,最后在烂泥里发现了这块印。这块印后来一直保留在祖父身边,直到1951年捐献给政府。”
从宣统退位到解放近半个世纪,北京城头变换大王旗,载沣的醇亲王府仍然像是各路人马进城要拜的“码头”。清朝的遗老遗少、日本军官、国民党、甚至还有司徒雷登。一波又一波,像历史的浪潮。而历史的浑水,载沣一次都没有趟。
“民国的时候,蒋介石想买醇亲王府。他找了孙连仲,国民党上将、第十一战区的司令官。孙连仲不知道怎么和醇亲王府攀了亲戚——他的太太和爱新觉罗家族沾点边,他就来认亲了。认亲是假,孙连仲在蒋介石面前夸下海口,说我给您办这事儿。一开始他找我父亲谈这件事,我父亲说,这得找老王爷。孙连仲有一天看我祖父挺高兴,就提出这事儿来了。我祖父一声没言语,没有作答。后来孙连仲又问了两次,我祖父说,这是不可能的。这就算回绝了蒋介石。蒋介石当时是一国之主,买你这个房,也不是抢。要说,卖给他就算了。但是我祖父觉得这是他一生需要保护的东西。孙连仲后来也不来了。
满洲国时期,溥仪身边有个日本人叫做吉冈,是关东军派在溥仪身边最大的间谍。吉冈多次到醇亲王府,一年起码来两三回,劝我祖父去东北。我祖父拍了桌子,大发雷霆,把他给吓跑了。他再来,我祖父再不见他。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投靠了日本人,也不是多想当汉奸,大多数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儿老小。但这是我祖父的底线。宁肯我得罪了你。
北平日据时期,有个侵华的司令官叫多田俊,曾经到醇亲王府去拜见过我祖父。我祖父也就敷衍了几句,没坐几分钟,多田骏就走了。中国的规矩是来而不往非礼也,重要的人物要回访。我父亲派手下人拿着自己的帖子——就是名片——回访多田俊。自己没有去。多田骏也是心里很恼怒,也不好发作,从此再无任何来往。”
1912年9月10日,孙中山在当时国民党步兵统领、俗称的“九门提督”的江朝宗的陪同下拜访载沣。“本来是十分敌对的两个人,一个是革命党人,一个是清朝实际的掌舵人,见面之后却谈得很好。孙中山对于我祖父辞去职务也表示很钦佩。9月13号,我祖父亲自回访,到孙中山在铁狮子胡同的行馆。祖父还叫家里给孙中山做了一桌饭菜,给抬了过去。相约第二年见面,但是由于孙中山身体不好,没有能再见。
有人说他是趋利避害,但是得罪蒋介石,得罪关东军,得罪多田骏,都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他不顾这种后果。”
日本投降之后,北平政府拿了一个蒋介石的函来醇亲王府,传达蒋委员长对载沣的褒奖,意思大概是:阁下在沦陷期间,不畏强暴,坚守民族气节,实属难能可贵。送给他十万法币,以资褒奖。
“蒋介石向祖父买这个王府,他没卖。解放后,他把这个王府给捐了。他靠的是政治智慧。周总理说,在日据时期能够保持政治的清白,可以说他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心静如水,分寸丝毫不乱的载沣,也有鲜衣怒马的时光。他曾经把枪顶在袁世凯的脑门上。
金老师给我看了几张载沣的旧照片,一张是载沣18岁时奉命出使德国,取道香港时拍的,载沣坐在正中间,在一群穿长靴马褂的清朝官员和西装三件套的外国人间,像一道光,年轻得晃眼。他把左侧脸给镜头,微微向上扬首。他曾有这样掩饰不住的意气风发。

在出使德国之前,载沣还没有担任过任何事情,但他很好地完成了这次出访。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超规格接待,亲自来到他的住处。载沣在德国参观了很多工厂和军工厂,威廉二世向他面授机宜,希望他回国掌权之后,一定要把军事抓在手里。
这是开眼观世界的机会,他看到了,学到了,并且接受了这些新鲜的东西。他是京城王公大臣里第一个剪辫子的、第一个买汽车的——一辆美国产的道奇。醇亲王府里有一个玻璃房,里面铺了地板,放的是西洋式的沙发,用来接待外国客人。
“一解放,他就跟子女说,不用天天给我请安了,把这给免了。这套礼节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东西。我七姑是自由恋爱结婚的,他也不干涉。他没有抱着封建的东西不放。”他又有很守旧的一面,从来不肯吃西药,“我父亲给他药,他说搁那儿吧,转身就给扔暖气后边儿了。如果他肯吃药,也能再长寿些。他崇拜西方,对于西药又不信任。”
他的少年豪情,没有挡住大时代的际遇。载沣当摄政王之后让载涛、载洵,一个管海军,一个管陆军。“这两个人成天逼着我祖父要官做,一点忙没帮上,添了很多乱。尤其我这六爷爷载洵,纳妾,抽大烟,是最不好的一个人。七爷爷载涛就是北京老炮儿,吃喝玩乐什么都会。唱戏,李万春都跟他学了好几年的戏。猴戏京城无人能跟他比,李万春跟他学的。斗蟋蟀,他的贝勒府就是京城最大的斗蟋蟀场。蟋蟀死了之后都弄一个小金棺材给埋了。”
载沣家里有不少地球仪、航海仪,他热爱天文、航海、地理,在载涛热爱蟋蟀的同时。

“雍和宫初一、十五的舍粥,以前那是救人的。宣统年间,雍和宫也没有余粮了,有人就报告我的祖父,祖父从府里拿了米,支撑了小半年,以前看了篇小文章,有个人就说他是喝了这个粥,才活了下来。祖父的日记里说:大清王朝不是哪一个人的,也不是哪一个家的,倘若能让天下老百姓安居乐业,吾辈应当尽力而为。这种思想,好像并不是封建君主的那一套。”
于载沣,摄政时,没有主宰苍生的意愿,只有分担疾苦的担当。归隐时,是心之所向。
文章作者


钱业
发表文章8篇 获得33个推荐 粉丝124人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