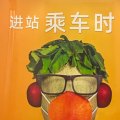有个北方作家朋友数落《繁花》:“你写的什么呀,男男女女,黏黏糊糊的,看都看不清楚什么关系,黄梅天那样——上海气候虽然如此,北方可明亮得多了,行还是不行,行就行,不行拉倒,一目了然,干脆麻利不好吗?”说了半天,结束时他却说:“我也要来上海生活。”对这部小说,我从没有过怀疑或犹豫,把曾经的事——当然是个人主观意义的——尽量形成一种貌似的观察记录下来。比如说,普鲁斯特经常(是这样),他写得最好的就是聚会,听到周围两个女人在说别人的八卦,飘过来,然后声音又没了。经常是所谓众生喧哗环境里一个真实的人。《繁花》写那么多饭局,是故意的,为什么故意?还有所谓上海话“不响”两个字,实际《繁花》最特别要说明的,是某种国民性,可以沉默,可以大声喧哗,大量沉默、不语,日复一日的聚会、饭局,也许是国民特点。
01-26 15:03
0人推荐
0人转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