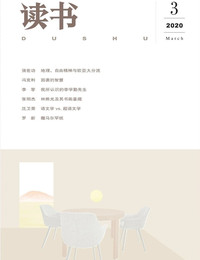细“嗅”文明
作者:读书
2020-04-02·阅读时长9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4732个字,产生16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周凝
近年,生物学对嗅觉研究的重视和香水贸易的全球化掀起了一股气味文化的现代复兴。嗅觉在过去几百年里都遭遇文化圈的贬低和无视,被狄德罗称作最为纵情声色(voluptueux)的感官。康德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强有力地证明了嗅觉的劣势:触觉、听觉、视觉都是客观的,而味觉和嗅觉却是主观感受。嗅觉使人对物体的感知短暂而模糊不清,无法被语言描述,并且其绝对的动物性使它不具备任何文化反思的可能性。直到二十多年前科学研究发现,嗅觉是唯一一个不通过丘脑的传递而直接进入大脑边缘中枢的感觉(而视觉、触觉、味觉、听觉均有此中转过程);并且,它具有极强的个体差异性与标识性,也是婴儿神经元建立的中心角色。换言之,唯有嗅觉是后天习得的,受到社会经验的影响的感觉,是一种文化压抑的产物。神经科学家从此开始注意其价值,认为嗅觉是最原始的感情基础。二十世纪,帕·聚斯金德小说《香水》中的邪恶谋杀与气味陷阱引起文坛轰动,并在二○○六年改编为同名电影搬上银幕,为此后嗅觉文化的研究埋下了伏笔。相关研究纷至沓来,一九九八年毕尼克(Aurélie Biniek)的硕士论文《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气味和香料》,二○○一年科尔班(Alain Corbain)的专著《瘴气与水仙》等学术成果使香与臭的二元化嗅觉感受成为时下的流行论题。
二○一八年,法国历史学家罗伯特 ·穆尚布莱德(Robert Muchembled)的新作《气味的文明》(La Civilisation des Odeurs)被摆放在法国各大城市书店最为醒目的位置。不同于其他单一色调的装帧和封面坚毅的名人头像,它饱和率较低的色彩弥漫着古朴之韵,封面展示的是文艺复兴风格的贵妇半身画像。作者似乎已经厌倦了对历史听闻絮絮叨叨的重复,转而将注意力投向了人类嗅觉在历史进程中所遗留下的痕迹。嗅觉总让人联想起动物原始的生存本能,听上去与文明毫无干系。在医学层面,臭味在鼠疫泛滥期间被视作疫疾的传染源;在风俗层面,人们对臭的厌恶根植于古希腊文化,但在文艺复兴时得以缓和;在宗教层面,教父神学教义所发展出来的魔鬼学将无处不在的 “臭味 ”等同于 “魔鬼 ”;而在生活层面,香与臭在情人之间传递着模糊的暗语,开启了诱惑游戏。对作者而言,香与臭、善与恶的二元观在潜移默化之中贯穿了西方思想的变迁,嗅觉主题正是一个思想学界的弃儿,在无意识之中彰显出无处不在的表现力。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3个推荐 粉丝20761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