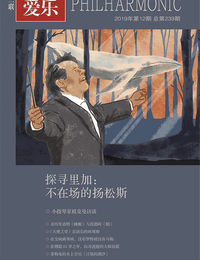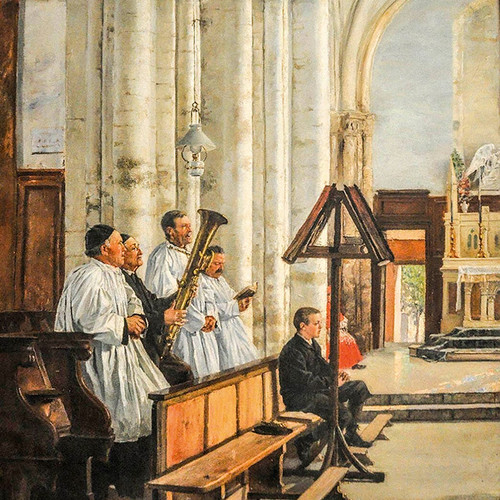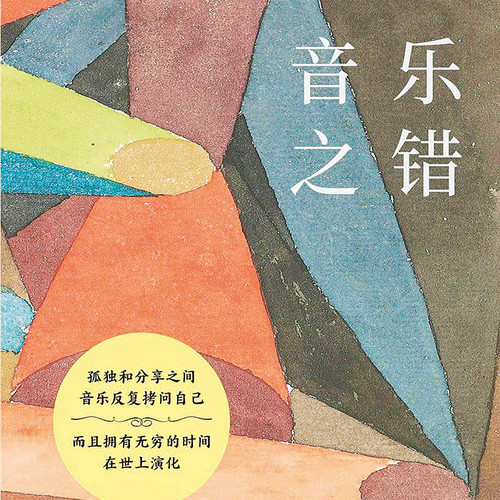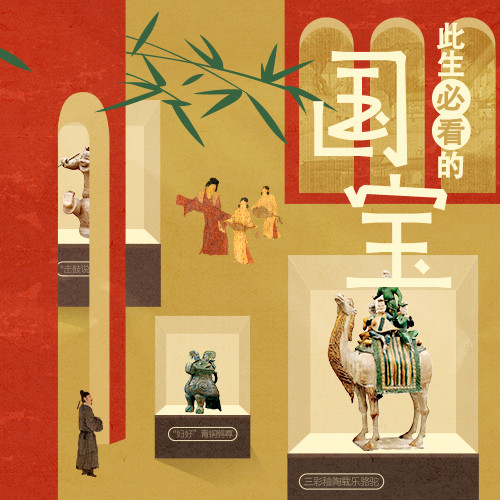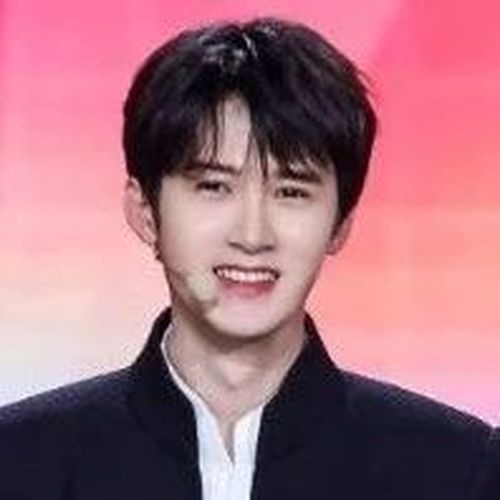梦境与虚拟的真实感:亲历里希特《睡眠》与范德阿《捌》
作者:爱乐
2020-01-07·阅读时长7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3535个字,产生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文/李峥
文/李峥
人在睡着之后,可以听到音乐吗?我所获得的体验是,音乐确实可以在睡眠中延续,只不过变换了一种被感知的方式,从听觉转成了整个身体的沉浸……随着音乐的徐徐流动,梦境缓缓降临,耳中的声音越来越朦胧,直至渐渐隐没,在无知无觉与有知有觉之间,沉睡着的整个身体似乎被声音轻轻托起,然后过了许久许久,周遭的声音再度飘入耳中,由弱渐强,直至可以完全辨出旋律,于是整个身体复苏,音乐得以衔接。这是我亲历水关长城的马克斯·里希特《睡眠》音乐会的真实感受。
“追梦·长城夜”是第22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首场演出,也是八小时的《睡眠》在国内的首演,安排在长城脚下则令人意趣盎然。原本计划的露天演出,由于天气原因临时改在室内,不过却一点儿没有降低它的魅力。三百个床位,三百套枕被,三百人共眠,一同沉浸在音乐之中,想来也是很壮观了。10月4日,刚好是天气骤变的最低谷,每一个人都把自己裹在被子里,灯光暗了下来,四周一片幽暗的蓝色——那是夜晚的颜色。
随着里希特指下敲击的琴声,31首乐曲中的开篇响起,《梦1(在风吹走一切之前)》中的那一串轻柔的敲击,就像时钟在宣告睡眠时刻的到来。接着的《积雨云》,弦乐加入并奏出不变的持续音,强烈的催眠效果显现了出来;《梦2(熵值)》是对《梦1》的回顾,然后在《路径3(7676)》中,女高音的吟唱宛如一支催眠曲,《谁的名字写在水上》则像是《路径3》的回声……在演出前的发布会上,里希特提到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它们都是为了睡眠而作的,不过对于我来说,二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当我听巴赫的那首时,会越听越无困意,而里希特的这首,却能真正为我招来睡意,或许巴赫的“哥德堡”只对作曲家所在时代的人才会起作用吧。
持续的音乐在里希特的独奏、美国现代重奏团的弦乐合奏、女高音格蕾丝·戴维森的歌声之间转换与融合,午夜过后,困意涌来,音乐在耳中逐渐变得若有若无,向着远方飘移,就像我在文首所记录的那样,音乐不再通过耳膜来接受,而是变成了梦境中的一员。睡了有三个或三个半小时,大概音乐的震荡可以起到按摩的作用,所以这是一次非常深的睡眠,当音乐从远方飘回,又若隐若现地在耳畔响起时,半梦半醒之间的我,发现了色彩的变化。
入梦之前的蓝色灯光,渐变成了粉红色。或许由于色彩的刺激,这时的我已经完全清醒,一觉过后,似乎音乐本身也泛起了闪光,虽然不知道进行到了哪一曲。不久,灯光又变成了明亮的浅绿色,而这彩色的音乐,令我不由想到斯克里亚宾的“火之诗”《普罗米修斯》,作曲家曾幻想有彩色灯光的音乐,此刻却让我在里希特的《睡眠》中见到了。在他的这部作品的演出中,色彩的变化,可寓意为时间的流动,或一个美好的过程,从夜晚到黎明,从睡梦到醒来。
文章作者


爱乐
发表文章834篇 获得1个推荐 粉丝18380人
三联书店《爱乐》杂志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