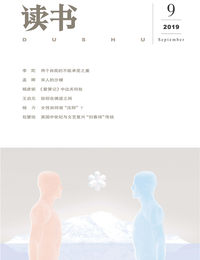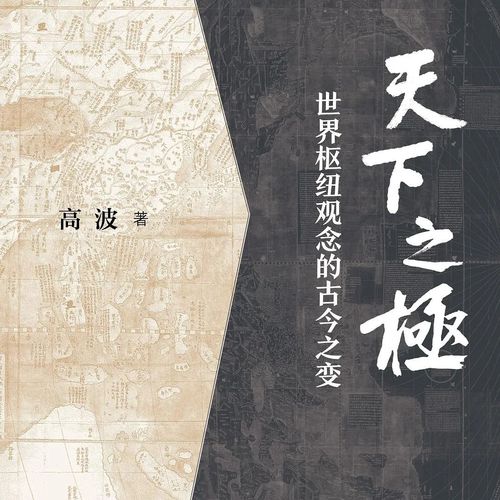西南腹地的构建
作者:读书
2019-10-15·阅读时长11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989个字,产生17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张翔
历史叙述及其命名有其特别的重要性,最好的案例莫过于两个路网的传播及其良好的接受效果,一是丝绸之路,一是茶马古道。丝绸之路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但这个概念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一百多年前才提出的,今天在全球政治经济发展中的功能有目共睹。茶马古道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木霁弘、陈保亚等学者在田野考察过程中提出来的概念,不到三十年时间,迅速得到国际上的广泛认可。
这两个概念还有另一共同特点,它们作为一种对历史实存的带有概括性的、凸显局部特点的描述,其所指的范围有着不确定性,因而不可避免会带来争议,或者会出现不同的界定。《读书》二○一八年第三期唐晓峰《李希霍芬的 “丝绸之路 ”》和第五期杨俊杰《“弄丢”了的丝绸之路与李希霍芬的推演》的讨论,便是与丝绸之路有关的讨论的例子。茶马古道是更年轻的概念,其所指更不稳定。
茶马古道概念的提出和讨论,是对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讨论的一个重要呼应。陈保亚、木霁弘等人在《滇、藏、川“大三角 ”文化探秘》(云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序言中即指出,茶马古道 “同海上之道,西域之道,南方丝绸之路,唐蕃 ‘麝香丝绸之路’有着同样的历史价值和地位 ”。当时他们认为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一是从云南的普洱出发经拉萨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的滇藏古道,一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康定、昌都到尼泊尔、印度的川藏古道。其他研究者对这一概念有所扩充。例如,王丽萍在《滇藏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廊道视野下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一二年版)中,将唐蕃古道纳入茶马古道,认为其线路主要分为滇藏道、川藏道和青藏道(唐蕃古道)。
陈保亚等人对茶马古道的梳理和命名,颇具特色的部分是他们从语言学家的角度所做的观察。他们指出,整个藏区和三角地带各民族交流的共同语言是汉语中的西南官话,而不是普通话或西北话。茶马古道上民族分布众多,这些民族的第二语言能够借茶马古道统一在西南官话下,这是世界文明传播史上罕见的实例。
基于这些现象,他们指出,相对于出入青海的唐蕃古道,联系西藏与西南地区的茶马古道对于汉藏文化交流更为重要。藏区在最初的茶马古道叙述中处于中心位置。在后来的众多讨论中,这一特点逐渐淡化,越来越多地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相并称和勾连。另一方面,最初的旨趣对后来的讨论仍然有很深的影响,虽然茶马古道越来越被叙述成连接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道路网络,其边界远远超出滇、藏、川“大三角 ”地区,但川藏线、滇藏线仍然是茶马古道叙述的主要内容。例如,王丽萍叙述了茶马古道的广阔 “外围 ”,向北可深入新疆、青海、甘肃,向东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南等省区。问题是,如果唐蕃古道能够被纳入茶马古道,是否也可以将这些外围或者部分外围道路网络纳入茶马古道的叙述呢?
在命名者那里,茶马古道的特殊之处在于,唐代茶叶传入西藏之后,藏区民众将茶视为必需品而非一般的贸易物,这是茶马古道相对于丝绸之路等古道更为持久的原因所在。不过,丝绸之路衰落的主要原因,恐怕并不在于丝绸是否必需品,而在于明代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从明朝中后期开始,东部沿海地区面临倭寇侵扰的压力,不再是宁静的后方,这是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形势,加上明朝的供需对丝绸之路依赖较少,嘉靖初期选择在河西走廊西北端实施封境政策。茶马古道相对持久的主要原因,则是因为历史上西藏扩张多沿唐蕃古道等方向展开,茶马古道沿线的横断山区相对平静。茶马古道的持久性并不依赖于藏民视茶为必需品的嗜好。
因为有喜马拉雅山脉的屏障,中国西南地区一直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历史上较少发生大规模战争。在广阔的西南山区,存在着极为庞大的山路古道网络,这些网络最初都是通过运输盐等生活必需品而兴起的。此前以川藏、滇藏古道为核心叙述的茶马古道,只是西南山区庞大的古道网络的一部分。在这些古道网络覆盖的地区,有一个极为重要,但至今缺少系统研究的语言文化现象,即是覆盖了众多少数民族的西南官话,其主要特点是 “古入声今读阳平 ”。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编,商务印书馆二○一二年版),西南官话区基本覆盖了除西藏自治区大部之外的西南山区,并在成都平原及江汉平原部分地区扩展。茶马古道的命名者们强调了西南官话在川滇藏 “大三角”多民族杂居地区通行这一全球少见的语言文化现象,但没有进一步系统讨论西南官话与整个西南山区古道网络之间的历史关联。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3个推荐 粉丝20774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