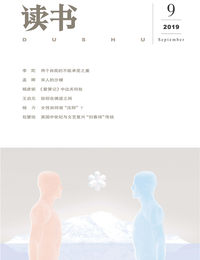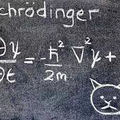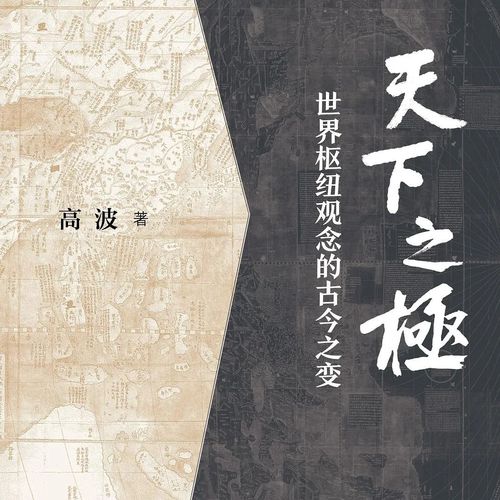我在这里看到了我想看到的一切
作者:读书
2019-10-15·阅读时长13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6765个字,产生2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张帆 陈雨田
一
匈牙利左翼作家阿图尔 ·霍利切尔(Arthur Holitscher,1869-1941)生逢诡谲动荡的乱世欧洲,过着波西米亚式的浪游生活,从“新世界 ”美国到“新希望 ”苏维埃,再到犹太复国主义的巴勒斯坦和革命中的中国,霍利切尔据此创作了风靡欧陆的多卷本旅外游记,以鲜活的 “异托邦风景 ”震撼陈腐没落的欧洲社会,成为欧洲新写实主义漫游叙事的典范。正如本雅明、茨威格、萧伯纳、罗曼 ·罗兰等东游 “朝圣者 ”一样,苏联和亚洲(特别是中国)之行,使霍利切尔走出文化无根感与生存孤独感的阴霾,他热情讴歌共产主义是 “一个伟大的思想,或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 ”,并能引领疾风骤雨式的 “世界革命 ”,“诞生新的人类共同体 ”;其游记在印象、评论与抒情的文字内里流溢着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求索和政治批判,不幸沦为一九三三年纳粹首次 “焚书事件 ”的牺牲品。霍利切尔被迫踏上流亡之路,一九四一年孤苦无依地客死于日内瓦救助站。
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六年三月,霍利切尔在为期半年的远东之旅中游历了印度、中国与日本等国家,并创作了游记《动荡的亚洲》(一九二六),实录了各国(除日本外)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反殖、反帝、反压迫的民族运动;在霍利切尔看来,这正是 “世界革命 ”的肇始,也是旧秩序瓦解与新秩序建立的征兆。霍利切尔尤为关注北伐革命战争前夜的中国 —这只沉睡已久但已苏醒的雄狮。古老的中华文明与崭新的 “苏联思想 ”结合,迸发出 “从所未有的希望 ”,这是 “世界历史新进程的焦点 ”“东方世界的命运之乡 ”“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诞生地 ”。此行于霍利切尔而言,不仅仅是漫游之趣,更是充满希望的救赎式远征。在此意义上,他解构了 “欧洲中心论 ”“东方主义 ”以及西学概念下的 “另类文化 ”,以细腻的笔触、炽烈的情感,筛选、剪裁、分割、排列与整合其直观印象与经验,在一种 “政治异国情调 ”的构建下,将看似零碎的印象、经历与反思统一在其革命乌托邦的想象之中。
二
霍利切尔的中国游记主要包括广州、上海、北京三部分,不同的城市景观给予他看待中国革命的迥异视角。广州作为 “中国南方革命的首都 ”与“伟大的中国解放战争的大本营 ”,在北伐革命动员阶段呈现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
霍利切尔的广州叙事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后举行隆重的阅兵仪式开篇,极力渲染阅兵式的隆重盛大 ——厚描东校场舞台上的孙中山巨像,细数出席检阅的政要,慨叹气势恢宏的士兵方队,讴歌革命群众的高昂热情:“当一个军团走过,或一个工会挥动着旗帜在远处现身时,就传来千万人齐声的呐喊,校场上的民众也跟着欢呼呐喊:‘第九军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北伐军的阅兵仪式令霍利切尔联想到莫斯科红场和列宁格勒冬宫前的军队游行。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理念的先行者和传播者,“苏联人 ……是征服者与先锋,却不是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 ……他们是一种即将征服世界的思想先锋。东方世界已然受到其影响,西方世界或自愿或被迫,终有一天也要追随这种思想 ”。
与阅兵场上生机昂扬的氛围截然不同,霍利切尔笔下的广州沙面租界却是一片死寂,西方列强的银行、别墅、领事馆 “早已是海市蜃楼,脆弱不堪,毫无根基 ”。杂草丛生的废弃足球场、门可罗雀的维多利亚宾馆(广州唯一一家欧洲宾馆)、落尘斑驳的威士忌广告、空无一人的俱乐部等;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那面刻着 “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自由 ”的法国 “一战 ”纪念碑已然坍塌,整个沙面岛上全面戒严,风声鹤唳。霍利切尔以沙面萧条荒凉的景象与惶惶不安的气氛反衬阅兵场上群情激荡、团结振奋的革命场景。在霍利切尔看来,帝国主义与殖民体系在中国已时日无多,中国人民重获自由解放已为时不远。
怀着对中国革命的无限热情,霍利切尔与苏联顾问 —时任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的鲍罗廷促膝长谈,了解 “在中国贯彻苏联思想的进展及其未来 ”,剖析消除中国土地私有制、组织农民阶级的困难性以及军阀混战、盗匪肆虐的破坏性,指出 “判定中国有某种确定的结局还为时尚早 ”。与鲍罗廷对中国革命问题理性审慎的态度相比,霍利切尔则饱含热切期待:“苏联已经实现了自我解放,这一伟大的榜样在这里,也在世界各地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产生着影响,尤其是在 ‘有色 ’的东方世界里。”在霍利切尔看来,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 ”的重要一环。“苏联思想 ”或共产主义,对他而言,更多的不是一种政治学说,而是人类社会彻底变革的乌托邦理想。
需要指出的是,霍利切尔的广州记述尽管充满憧憬,但其 “并非以可能性为尺度来衡量现实,而是在现状之中发现未来 ”;换言之,他将革命的理想与高蹈奠基于日常生活的凡俗人生,写实与想象熔为一炉。他遍览 “广州外滩 ”上船民、乞丐、手工艺人的生活,以及猖獗的偷盗、绑架等犯罪活动,以一种民族志式的文化刻写呈现出广州既有生机与活力,又有动荡与堕落的复杂图式。另一方面,他对 “这座动荡城市里的政治游行者、学生、工人与市民 ”则更多是富有想象性的描述:他们挥动着 “白色旗帜 ”,发出 “狂热的喊声 ”,投掷着爆竹,充满 “天真的活力 ”。仪式化的细节真实性与画面感恰恰表征着叙事的虚构性,因为异国旅行者显然无法确知游行者的身份,却又不惮于假设不同身份的人们在黑夜的掩护之下整齐划一地参与到政治宣传与革命活动中,无疑是一种审美想象与政治期待。然而,这座 “人口众多、活力非凡、日夜灯火辉煌的城市真正的乐章 ”是“受压迫者 ”劳作时发出的 “呻吟的、单调的、有时狂野的歌唱声”。霍利切尔以虚实交融的叙述喻示 “这座熙熙攘攘、迅猛动荡、永久年轻的城市 ”喷薄欲出的革命曙光。广州无论多么混乱,却孕育着革命与新生,而外国人的沙面,则将 “独自继续沉睡,自我麻痹,以珠江水面上冒着蒸汽、软弱无力的战舰做困兽之斗 ”。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1个推荐 粉丝20774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