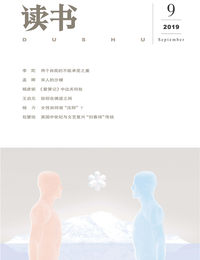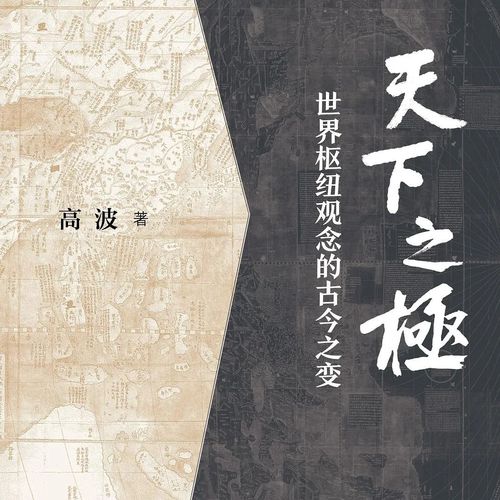信仰在佛道之间
作者:读书
2019-10-15·阅读时长13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6952个字,产生1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王启元
信仰在佛道之间
本土儒、释、道组成的 “三教 ”,是近世中国社会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信仰形式。其中的佛教与道教 ,今天的读者自然不会陌生,但明清以来 “儒教 ”的传统,则已不太为人所知。今日的民间社会中,还活跃着一系列传统信仰方式,因其下层、迷信、怪诞的特质,尚不能位列 “三教 ”叙述之中。它们最早被称为 “迷信 ”,抑或 “异教 ”“偶像崇拜 ”,也被称作比较中性的 “祭祀 ”,后来逐渐约定俗成为 “民间宗教 ”,它与本土 “三教 ”间的相关话题,自明清之际的传教士们关注到之后,便一直都是学界的热门领域。李天纲《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以下简称《金泽》)一书,继续探究 “民间宗教 ”与传统 “三教 ”间的渊源与联系,多有开创性的新见;学界也已围绕儒家宗教性、民间信仰、中国宗教学开拓的诸多话题,有过多次评议反馈。不过书中仍有不少跨领域研究可资借鉴的维度,尚待标出,其观点的共鸣不仅限于宗教学、思想史的范畴,在文学史、经学史、明清史甚至是区域地方史等学科同样产生了精彩的碰撞,这是《金泽》一书独特的魅力所在。
何以儒教?
《论语》中有句名言:“子不语怪力乱神 ”,以证明孔圣人理性的一面。但孔子不提倡,并不代表孔子及其之前的儒家传统,对“怪力乱神 ”持彻底无视或否定态度。《金泽》梳理中国经学史及本土宗教史(全书上编第三章及下编第八章部分段落)后提出,民间宗教信仰内核,来自早期的儒家周孔之教中的祭祀传统,是为全书桎辖。殷周秦汉以来,儒家的宗教性成分,与汉代经学家树立的 “周孔之教 ”,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信仰体系,这一信仰体系,虽在历史上屡经挫折,但顽强地保存在中国人的精神脉络之中。不过明清平民士人并不见得对文庙中的衍圣公像有多少遵奉的习惯,甚至清代读书人科考前拜得更多的,其实是武圣人关老爷。
同时,明初以来的官方政府,对天地鬼神祭祀活动的重视,深刻影响着地方甚至民间的祭祀行为。大明南北两京中的都城祠祀坛庙系统,负责整套国家祀典的进行,这其中除祭天的天坛外,地方府州县之中,会分别设下一级坛庙如地坛、日月坛、文武庙,由各级政府安排春秋两次致祭。这些便成为地方 “儒教 ”活动的主干。再往下一级到区域,没有了官方指派的祠祀系统,民间便自己形成了一套祭祀对象,一一对应 “官方祭祀体系 ”。《金泽》的书名,来自一个没有官方指派的祠祀的镇级行政区域、位于上海西陲的金泽古镇,那里至今保留春秋两季的香讯庙会。通过长达十余年对金泽镇进行的文献及田野考察,李天纲尝试追溯此地香讯文化的源头,“民间祭祀探源 ”成了全书最醒目的线索。他发现古镇祭祀活动中,至今保留了非常完整的《一朝阴官表》,记录金泽本地一系列神祇及庙宇的秩序,从金泽东岳庙里的东岳大帝,到杨爷庙里的杨震,形成地方上特有的从 “皇帝 ”到“州县官 ”的体系,并由此产生按照这个顺序一级一级烧香才灵验的“规矩 ”。今天犹存的 “阴官表 ”“杨老爷 ”等信仰传统,实际就是官方儒教制度在地方信仰生活中的真实投射。由此可以看到今天定义的“民间信仰 ”,实际出自中国明清以来恢复的儒教系统。尽管它们曾经在信仰传统中拥有相当的正统性,但今天只能保存在 “民间 ”“下层”之中,倒是真应了孔老夫子讲的那句:“礼失求诸野。”同时,近世以来重要神祇信仰体系的建立,与明初礼制改革及汉地信仰重建有莫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定义 “儒教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明清以来的儒教信仰,在神祇、仪式、教义等方面拥有三教信仰的不少共性,但不可忽视的是儒教不少独特的方式,尤其在其祭祀方面,其中 “魂魄 ”“鬼祟 ”“焚香 ”“设像 ”等具体措施,便是中国本土宗教的诸多基本形式组成。
正因为长期缺乏对 “儒教 ”宗教体制的认识,一些重要文本中的“儒教 ”描写,被长期忽略,而一旦明白了本土信仰中的这一线索,许多曾经忽略的细节又重新有了讨论的空间,比如《水浒传》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是大家所熟悉的。以往解说这则故事的精彩之处,都着眼于人物性格与情节设置的方面,但其中还存在一幕精彩的 “儒教 ”隐喻。这回书写到林冲被沧州牢城营差拨、管营算计,从营房天王堂调到偏远的草料场。风雪天去集市打酒回来,两间草厅已经被大雪压塌。去时林冲途经一座古庙,并进庙顶礼道:“神明庇佑,改日来烧纸钱。”草厅塌后,林冲至古庙暂宿,后仇人出现,一阵厮杀,都是读者熟悉的情节。作书人在林冲发现草厅压塌后,有一笔评论:“原来天理昭然,佑护善人义士,因这场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这里的 “天理昭然 ”,既有道德伦理层面的含义,同时还有 “天道 ”层面的宗教意味;而小说中具体替 “天”承担佑护的角色,无疑就是风雪中的那座山神庙与庙中的神祇。小说里描写山神庙时有言:“入的里面看时,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两边一个判官,一个小鬼,侧边堆着一堆纸。团团看来,又没邻舍,又无庙主。”山神庙中立有塑像,中间是一尊 “金甲山神 ”,两侧分别是判官和小鬼,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佛道神明;山神也从来没有被正统的佛教与道教收编,即便明清以后存在山神庙为道士接管的现象,但这一因山川河流崇拜衍生出来的山神祭祀行为,与佛道教系统有明显的差别。按照宗教学研究的成果,“山神 ”这一神祇,既可能出自山川之灵,留在地上木石头之魍魉;也可能是被派来镇守此处的物故名人。这两种身份,分属于汉儒总结的 “帝神鬼妖 ”中的 “神”和“鬼”。小说里的这位山神,不仅做到了灵验,同时还兼顾了正统价值观中的“天理昭然 ”,保持 “鬼神 ”公正的一面。而林冲躲过杀身之祸,并报仇完成后,出现一幕血腥的剧情:(林冲)“将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提入庙里来,都摆在山神面前供桌上。”同时放在供桌上的,还有陆谦的心肝。林冲这一行为无疑是向神祇献祭。
这段血腥暴力的情节,完全不能简单视作对仇人的泄愤,而是主人公得到佑护后的还愿举动,以回馈神明,这一 “还愿 ”描写其实就是传统血祭。中国本土儒释道信仰中的祭祀活动,唯一不避讳,甚至提倡血祭的信仰,便是儒教的祭祀,这也是儒教区别于佛道二家最为醒目的信仰行为之一。虽然文明的汉唐经师们,在儒家经典 “三礼 ”的注释中避免提到 “人祭 ”这一残忍的祭祀方法,但从出土的夏商时代祭祀遗址中,可以找到太多实例。据古文字及《说文解字》所释,“祭”便是 “用生肉敬供神佛祖宗 ”的意思,而“血”的本意,则为祭神杀牲时滴注在器皿里的体液。依据上古造字及背后蕴含的意义来看,中国古人早就对血祭神祇与先人,有一套完整的概念与程序。林冲在此血祭山神的做法,是其对自己先前说过的若得 “神明庇佑 ”“来烧纸钱 ”某种变相的许诺。林冲自知无法烧纸还愿,但还是采取合乎 “儒教 ”礼制的行为,完成对神明护佑的谢意。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4个推荐 粉丝20774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