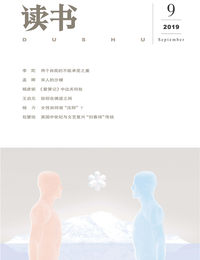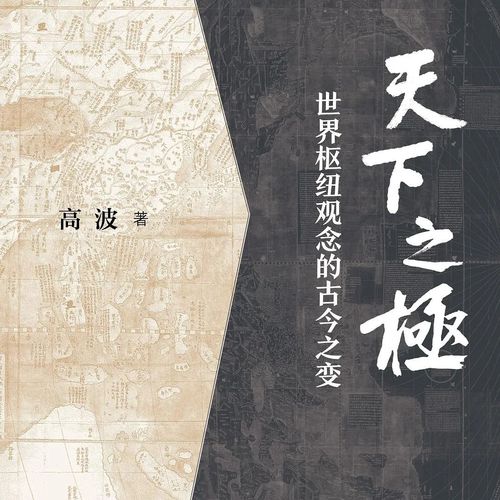《赵氏孤儿》的革命接力
作者:读书
2019-10-15·阅读时长6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3289个字,产生3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张晴滟
说起 “文革 ”样板戏,好像总会有一些负面的评价。但如果摘掉有色眼镜与政治外衣,考察其艺术表达与剧本改编,会发现它们其实都不简单。比如,《红灯记》就是与传统戏剧密不可分的典型代表。
《红灯记》的前身是创作于一九六二年的电影《自有后来人》。据编剧沈默君自述,片中 “革命的三代人 ”的设计是受到了戏曲《赵氏孤儿》的启发。新的史料继续披露说,李玉和的原型是东北抗联国际交通站的联络员傅文忱。老傅同志参加革命前有两个女儿,七年后他的老婆改嫁,又生了两个孩子。而老傅本人也再生两个女孩。这样复杂的家庭关系,现而今十有八九会为了遗产 “打”上电视栏目。但在反击侵略者的情境中,这一对革命夫妇组成了三个革命的家庭,齐心协力传递情报。沈默君将原本的 “三窝人 ”改编为毫无血缘关系的 “三代人 ”,这一笔不简单,把今天耳熟能详的 “宫斗剧 ”升华为革命剧。剧作家当时不曾想到,十年后,“革命的三代人 ”开花结果,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红色经典《红灯记》,被再次搬上荧幕。
中国人对《赵氏孤儿》的喜爱,可以追溯《史记》。元人纪君祥又做了重要改编,拔高主人公形象,写出英雄 “接力 ”牺牲的戏剧冲突。十八世纪的欧洲人看到如此这般高台教化,激动不已。《赵氏孤儿》成了伏尔泰一见倾心的古典主义高悲剧。王国维曾赞扬《赵氏孤儿》“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主人翁之意志 ”。平心而论,元剧中 “接力 ”复仇的思想根源,未必是出于什么独立意志,而是儒家理想中的忠君义死。“义死 ”的东洋形式是日本武士道中的 “切腹 ”,这一象征形式最终被法西斯主义吸纳。值得一提的是,与《自有后来人》同期上映的日本电影《切腹》对上述情结做出了深刻的批判。追根溯源,赵孤复仇的必然性揭示出:“天道不变 ”的假定下,血统之缘与春秋大义密不可分 —这也恰恰是同期反教权不反君主的欧洲启蒙主义推崇的国家理性。
在中国民间,赵孤的故事继续流转于南北声腔之中。明代曾有南戏和北曲两个版本的改编,其中只有北曲《八义记》的文本流传至今。北曲版中,情节被改编为程婴、麂、周坚、张维、提弥明、灵辄、韩厥、公孙杵臼这八位义士舍生救孤儿的故事,并且,全剧长度被扩充为四十二出。再往后,清代的梆子戏延续了北曲 “八人接力 ”的结构,改《八义记》为《八义图》。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沈默君脑海里 “三代人 ”的构思应该是受到过由马连良、裘盛戎、张君秋主演的京剧版《赵氏孤儿》(一九六 ○年)的影响。翻找影像资料,我们发现,这一版《赵氏孤儿》吸收了婢女复仇的情节,也发展出程婴含冤十六载,盼到新君登基,却又被忠臣魏绛拷打的场面。纪君祥用脸谱化的类型人物讲述司马迁笔下 “君子 ”舍生取义的 “接力 ”。京剧吸收了梆子戏里的女复仇者,也继承了纪君祥的路子,继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程婴。京剧中程婴的扮演者马连良同时也是当代最有名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海瑞的扮演者。从扮相和唱念上看,两个形象相差无几。时至今日,中国戏台上的《赵氏孤儿》还是老生当家,古史的春秋大义与当代史形成了东欧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所说的互文关系(Intertext)。而现代戏作为革命的文艺,必须要塑造抗战时期 “新君子 ”的“接力 ”。于是,戏台上的奸臣化作了日本宪兵队长,八义士变成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三代。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3个推荐 粉丝20774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