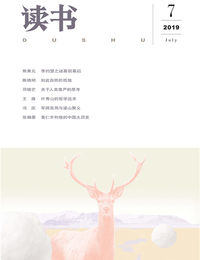“两声布谷”
作者:读书
2019-08-16·阅读时长12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6074个字,产生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孙红卫
暮春时节,莺啼燕语,中西诗人都不免为此兴发感动,赋诗吟咏。周作人应是最早留意到英国禽鸟诗歌的中国学人。在一九二五年的一篇题为《鸟声》的文字中,他便引介了托马斯 ·纳什(Thomas Nashe)、珀西 ·比希 ·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等英国诗人的禽鸟诗,指出纳什名诗《春》中四声鸟鸣或各出自杜鹃、夜莺、田凫、猫头鹰—“cuckoo, jug-jug, pu-we, to-witta-woo”(周作人:《雨天的书》),并且将之与中国文学传统的禽言诗并举。周曾另文考据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禽言鸟语,论述诗人如何摹声赋意,给予鸟类啼鸣以意义,并考察了清代士人对于历代禽言诗的爬梳与评述,强调研究禽言这一看似无谓的文字游戏对于研究民俗乃至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周作人:《过去的工作》)。不过,对于何谓禽言,钱锺书则有更为严苛的界定,他区分了禽言与 “鸟言 ”,认为 “鸟言 ”乃指 “想象鸟儿叫声就是在说它们鸟类的方言土话 ”,禽言乃指 “想象鸟儿叫声是在说我们的方言土语 ”(钱锺书:《宋诗选注》)。因此,“同样的鸟叫,各地方的人因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不同而听成各种不同的说话 ”(同前)。换言之, “鸟言 ”在于摹声,认为鸟类自有其语言系统,禽言则在于摹声赋意,即以人的语言赋予鸟声意义。
按照这个定义,英国诗歌中虽不乏对于鸟类声音的摹写,却鲜少禽言诗的写作。鸟类鸣啼要么被虚化为 “歌声 ”,如约翰 ·济慈(JohnKeats)《夜莺颂》之中的所谓 “灵魂之声 ”—这实则无异于一种浪漫化、隐喻化的指称,从而遮蔽了鸟类鸣啼本身声响层面的特征;要么是以拟人赋予鸟类人言的修辞手段,如杰弗雷 ·乔叟(Geoffrey Chaucer)《众鸟之会》(Parlement of Foules)之中的鸟类言语。即便有对于鸟声具体声音特征的关涉,也多是以象声效仿鸟鸣的拟声书写 —如周作人所引纳什一诗对于鸟声的描写:这四种鸟鸣在原诗中只是拟声,并无类似于中国禽言诗的意义指涉。郭沫若曾译纳什此诗:
春,甘美之春,一年之中的尧舜,
处处都有花树,都有女儿环舞,
微寒但觉清和,佳禽争着唱歌,
啁啁,啾啾,哥哥,割麦,插一禾!
…………
有意思的是,他将这句鸟鸣 “cuckoo, jug-jug, pu-we, to-witta-woo”的后半部分译成了禽言:“啁啁,啾啾,哥哥,割麦,插一禾。”前半部分 “啁啁,啾啾 ”乃是纯粹的拟声,后半部分 “哥哥,割麦,插一禾 ”则是既拟声又赋意了。此处翻译策略显然是受了中国禽言诗传统的影响,恰巧再现了中英诗中不同的鸟声写法。同样是杜鹃鸟声,在梅尧臣诗中,其鸣啼是 “不如归去 ”,在另一诗人那里为 “布谷”或“脱却破袴”(参见《宋诗选注》),纳什诗中则只是纯粹拟声的 “cuckoo”之音,而莎士比亚《爱的徒劳》剧尾诗节亦有此声:“cuckoo, cuckoo: Oh word of fear, / Unpleasing to a married ear!”(“布谷,布谷:恐怖之言 ,/令多少已婚的人胆战心寒!”)似可视为禽言,但在严格意义上也属 “鸟言 ”,只是借助 “cuckold”(戴绿帽子的人)的词源学意义(“cuckold”一词源于杜鹃鸟声,源自杜鹃鸟将卵混入其他鸟类巢穴的孵化习性)试图以 “cuckoo”之声勾起对于这个词的联想 —《尤利西斯》中,乔伊斯便引用了莎士比亚的这一典故,让机械钟里报时的小鸟以“cuckoo”之音鸣响九次,回答了小说人物对于婚姻的问询。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20772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