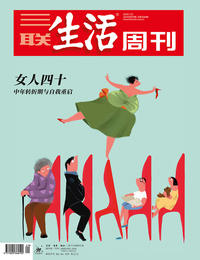“全职妈妈”:辛酸、渴望与再出发
作者:徐菁菁
2019-07-17·阅读时长20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10359个字,产生131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中国的全职妈妈群体正在迅速扩大,社会如何认识她们的价值,她们如何自处,是一个新的课题(视觉中国供图)
“三年之痒”
5月11日中午,母亲节的前一天,我到北京顺义福尼亚剧院参加“国际女主人节”。这场面对国际社区妈妈们的活动主题为“全职妈妈再出发”,重头戏是两场“轻戏剧”表演,都是由全职妈妈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来到这里,我有两个好奇。一是基于一个事实: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近些年,尽管中国女性受教育比例不断上升,但中国女性的就业率却从2000年的68.2%下滑至2017年的58.9%,这意味着有更多女性最终回到了家庭。在全面二胎的政策背景下,这一数字还可能继续下滑。智联招聘发布的《2017职场妈妈生存状况报告》显示,21.7%的职场女性有做全职妈妈的未来规划。第二个好奇基于我眼前的这个全职妈妈群体的特殊性。顺义后沙峪一带是北京著名的别墅区,这里聚集的是中国最富裕的全职妈妈群体,套用剧本里的一句台词:“我还以为你们是中国最幸福的女人呢。”她们也会有普通全职母亲的辛酸和焦虑吗?
戏剧开演前,准备了一中午的全职妈妈们决定快速解决一顿午饭。Inès拒绝了伙伴们让她吃一块三明治的建议。“我出门前只敢啃两只我妈煮的鸡爪,这三明治下肚,还怎么在台上演小蛮腰?”
Inès在戏里演一个叫赵小梅的角色。赵小梅曾经梦想当畅销书作家,她数十年如一日保持着小蛮腰。和身在职场的闺蜜一起逛街买衣服,人家买五套,上班一天换一套,她想着自己做全职妈妈全年无休,跟着买了七套。可是回到家,鞋还没脱就后悔了:“我啥场合穿?难不成穿着香奈儿去买菜?”她去银行办卡,在“职业”一栏谦虚地填了“家庭主妇”。柜台小姐笑了,用笔重重地划了去,改成“无业”,让她在旁边签字确认,承认她犯了错。“我们是中国最精神分裂的女人,”赵小梅有这么一句经典台词,“一面佯装幸福,一面绝望。”Inès和剧本里的赵小梅一样快人快语,台词一从她嘴里爽脆地抛出来,台下就笑作一团。
几个月前,“国际女主人节”的主办人Vida找到陶太,希望她执笔写一个剧本。陶太已经做了9年的全职妈妈,正在筹划重新回到职场。初稿写得很快。“那些台词百分之七八十是我跟我的朋友们生活中的原话。”剧本里,全职妈妈们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迷茫:“觉得前途一片漆黑,不知道自己是谁,要去干吗,要到哪儿去。”那正是陶太几年前“特别刻骨铭心”的状态。

Vida感到,全职妈妈们有再出发的渴望 (王旭华 摄)
陶太是在大女儿4岁那年回家的。父母年岁渐大,已经无法承担看护孩子的工作。陶太那时在一家媒体做编辑,为了两全工作和孩子,常常只能牺牲自己的睡眠,深夜里“点灯熬油式地熬”。有一次,她觉得自己再也熬不下去了。“女儿犯了哮喘。凌晨4点半,我开车去医院挂号,随身带着笔记本电脑和小马扎。我就坐在排号队伍里,敲着字编着稿子,别人往前挪一点,我也往前挪一点。”终于排到窗口,当天的号正好挂完。陶太当场嚎啕大哭。抹完眼泪,第一件事是把稿子编完,赶紧发走。
陶太原本以为辞职回家只是一段过渡期,没想到这一口气就“歇了9年”。说是“歇”,其实不然。全职妈妈是一个厨娘加保姆、司机加陪练、教师加秘书的混合岗位,而且是7天24小时工作,没有周末,没有假期,看不到头。两年前《爱乐之城》上映的时候,陶太想去看场电影,死活抽不出两个小时。那时,大女儿已经进入青春期,特别敏感。小女儿2岁,刚进入幼儿反叛期,已会大声说“不要不要”,一言不合,马上躺倒在地上。这个淘气的孩子一个月里创下了看医生的纪录:一次是她悄悄翻出了姐姐的手工材料袋,鼻子里塞进去一颗小珠子,陶太惊魂未定,两天后又发现她磕伤了门牙;接着小人儿大哭大闹,肚子痛、发烧、上吐下泻,不得不去看儿科急诊。陶太通常早上5点多醒来,有时夜里12点还没有坐下来喘口气,孩子生病的时候,更是只能整宿抱着孩子坐着。“累还在其次,最难受的是,我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鲜有坐下来一个人发会儿呆的工夫。”
某个周一,面对周末热闹过后乱糟糟的家,陶太又疲乏又沮丧,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我需要一个人的假期,哪怕是以小时计。”她鼓起勇气要求先生早点回来,让她去看那场《爱乐之城》。大银幕上,男主角问道:“Do you have a dream(你有梦想吗)?”黑暗中捧着爆米花,吃着哈根达斯犒劳自己的陶太觉得每一个词都敲进了自己心里。
陶太生于上世纪70年代,自言是在“妇女能顶半边天”这种观念下长大的一代女性,一路读书求学,勤恳工作,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成为全职妈妈。辞职回家的事,陶太心虚地瞒了母亲多年。4年前,二胎政策还没放开,夫妻俩觉得时间不等人,决定去美国生孩子。陶太给母亲打电话,说她会在美国待半年。母亲问:那么长时间,你领导同意了吗?陶太鼓起勇气,说自己辞职了,但还是隐瞒了已经辞职5年的事实。母亲言语上没说什么,但老人家不满意的气场还是从电话那头紧逼了过来。
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个把头衔,不是高级职称就是业界的资深人士。“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除了是个妈妈,你几乎什么也不是。有一段时间我特别不愿意参加同学聚会,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就好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谈论的那些东西我不是不感兴趣,可是我插不上话。”还有一段时间,陶太发现自己这个曾经的媒体人,成天和孩子们打交道,似乎连说话能力都退化了。“一张嘴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肤浅。”
在家里,陶太也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眼前这个人,不仅是你的伴侣,他也是你的饭碗,当你知道他是你的衣食父母的时候,你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刚结婚的时候,她向先生坦白自己没有积蓄,为了践行自力更生的独立女性价值观,她主动提出家用AA制。可做了全职妈妈,半边天变成了伸手族,她心里纠结得不得了,买件稍微贵点的衣服,心里就有满满的“负罪感”。后来她发现,周围的全职妈妈都“报虚账”“做假预算”。譬如买菜的预算是按照超市标准制定的,但坚持去早市买菜,只买时令菜。再譬如同学聚会AA制时,一定热情付账,刷卡买单,而后收取现金,称为“套现”。还有人会悄悄地在每月的家庭开销里扣下一笔,当然,前提是数量不至于大到引起先生注意。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维系自己的自尊心,攒下一笔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钱。有朋友告诉陶太,她的目标是攒出一笔自己的养老金,将来老了,不至于给孙子买颗糖都得问先生和孩子伸手。实在无法节流,就想办法开源,陶太常常前脚把先生孩子送出门,后脚就扑到电脑前挣点兼职码字的钱,估摸着先生快回家了,便开始小跑着扫地叠被,预备一家人的餐食,“角色转变之迅速,比电视遥控器还灵敏”。
陶太说,她观察,在中国从一个甜蜜的全职主妇,变成一个崩溃的绝望主妇,大约需要三年。这恰好是一个孩子度过婴幼儿时期,可以交托到幼儿园的起始阶段,也是一个全职妈妈内耗到弹尽粮绝的极限。“三年之痒”的原因五花八门,有些是因为家庭经济的压力,有些是厌倦了看不见尽头完全没有奖赏的家务琐碎,有些则纯粹因为伴侣不能够认同这份付出,回家变成了失败的代名词。
陶太的家庭没有顺义妈妈们那么富足,但那种个人价值感缺失的不安全感是共有的。
香港妈妈Estella是“国际女主人节”另一场“轻戏剧”的编剧兼导演。在陶太眼里,Estella是个异类,她永远热情澎湃,活力四射,陶太剧本里写的那些悲观自怜,好像在她身上都看不见。可是Estella告诉我,接受全职妈妈这个身份,她花了很长时间。十多年前,35岁的Estella做了个决定:结婚,和丈夫移居到北京。38岁时,她速战速决生下两个孩子。休完产假,她把孩子们交给保姆,回到职场。可是圣诞节的时候,她发现孩子把小区大厅圣诞树上的圣诞球拿回了家。“这是公共用品,怎么能这样做?”还有一次,保姆让孩子在小区公共场合随地大小便。“生下小孩子就可以不管了吗?我怎么能够允许我的孩子不按照我所认为的基本规范去成长?”现在看起来,回家照顾孩子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只有Estella知道自己接受这个选择有多难。来北京以前,她在香港一家大公司的客户服务部做部门经理。离职的时候,她一层楼一层楼地去和同事们告别。“我好爱工作啊,舍不得,坐在别人办公室里哭,走都走不动。”回想起十多年前,她还是忍不住在我面前抹起了眼泪。

Inès曾在加拿大做税务审计工作,回国后,她的公司税专业完全派不上用场,职场经验重新归零。那时候,年纪逼人,要孩子是当务之急。“吃药,看医生,每天早晨睁眼第一件事是量体温,画温度曲线,整个人的精力都耗在了上面。等孩子终于生下来,更没有时间筹划就业了。”孩子小的时候,黏在母亲身上,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几年之后,孩子渐渐长大,Inès觉得自己不太对劲了。“说起来特别矫情,我每天吃得饱穿得暖,想买什么也买得起,可我看什么都不顺眼,觉得全世界欠了我。幸不幸福是个精神状态,和外界条件其实没多大关系。以前小时候看哲学家要追问‘我是谁’,我只觉得好假,可是到一定的年龄,我也开始问自己:我是谁?我什么也不是!别人一到年底公司有奖金,开年会,我连个组织都没有,那种失落感你知道吗?”
Inès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法西斯”妈妈:孩子是别人眼里的学霸,但她甚至可以为一些小事对孩子说出“你真像猪一样”这么难听的话。先生屡次批评她,说她把自己的坏情绪倾倒在孩子身上,Inès并不觉得。直到有一次,她被学校老师找去约谈。老师说,孩子在学校里当小组长,需要督促同学完成作业。老师模仿孩子催促同伴时的一言一行,Inès一下子羞愧难当:“我就像是在照镜子。”
文章作者


徐菁菁
发表文章143篇 获得25个推荐 粉丝1762人
《三联生活周刊》资深记者。写字是为了满足好奇心。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