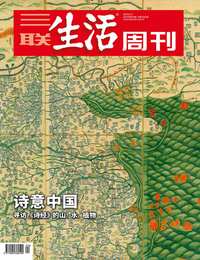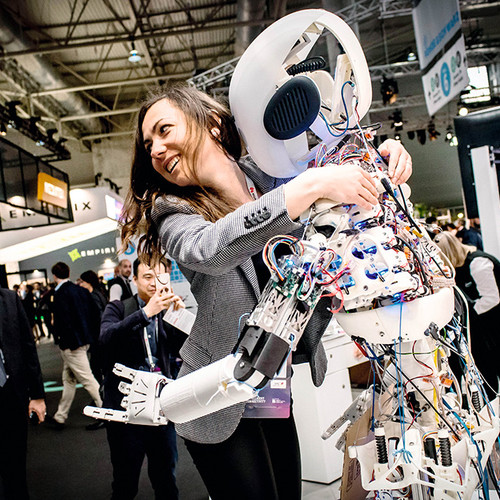汾河:晋地之母
作者:刘畅
2019-06-12·阅读时长10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188个字,产生1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汾河风光
摄影/蔡小川
王制之始
如今你只能站上堤岸,跃入汾河。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诗经·魏风》里伸入河滩的湿地不再,采野菜的翩翩少年亦不再,一如“魏风”的确切范围已扑朔迷离,与“唐风”难辨彼此。“十五国风”里,“魏”“唐”皆属春秋时的晋国,在晋南地。“汾”即“大”,汾河乃晋地最大的河流,自晋中的管涔山北缘而下,蜿蜒713公里,西入黄河,润泽方圆3万余公里。经至临汾盆地已是下游,河水平缓,东岸卧有崇山,居盆地中心,周围的汾河谷地自古乃唐地,正是《诗经》成书时晋地的核心。
公元前1035年,此地发生叛乱,周公平乱后,周成王把自己的弟弟分封于此,史称“唐叔虞”。我从临汾市里向此进发,东南驱车不到一小时,但见路旁不时出现茹毛饮血的原始人宣传画,指向崇山西麓陶寺村的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唐叔虞定都崇山之前千年,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间,那里已形成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都邑,与五帝之一的“唐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汾河谷地缓缓抬升,放眼望去,遗址只是斜坡上高高低低的麦田。东西约2公里、南北约1.5公里的遗址被5个村庄包围,数千年来却几乎从未被后世的房屋覆盖。遗址的土不够黏,村民建不了窑洞,盖房也莫名觉得此地阴气太重,反而绕开这片宽敞、向阳的高地。

陶寺宫城遗址
“陶寺的城址东边有从山上流下的南沟,中轴线上有中梁沟,两条河都汇入汾河,当时的人们除了打井,用水的主要来源便是它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高江涛常年驻扎现场,他带我探访先人选址筑城的门道。距离陶寺遗址西北界不到5公里便是汾河。山中南沟的河道仍在,建都时为修筑围墙,特意让河道拐了个弯。“‘(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管子在《乘马》篇中总结的都城选址原则,在这时已得到贯彻。古人不像今人会生活在离水很近的地方,尤其不会在滔滔的黄河边。为了既用上水又不被淹,古代都邑往往建在黄河、长江的大支流旁,并且多是在河边宽阔的二级阶梯上。” 高江涛说。
自上世纪50年代被发现,陶寺遗址已发掘出早、中、晚三期的遗迹,夯土砌墙围出城郭,大城中套宫城,又有下层贵族生活区和平民生活区,乃至祭祀区、手工业生产区、墓葬区、仓储区。“根据季风和河水流向,‘下风下水’的地方是平民区乃至有污染的手工业区所在的地方,与北京城‘北贵南贱’格局的理念一样。”整个城址目前是遗址公园,观景点在城址东南部祭祀区的观象台,高江涛引我东望,崇山中间隆起,两边缓缓伸入地平线,恰把遗址“抱入怀中”,正是千年来国君建都时都要寻找的“太师椅”。“更为难得的是,山上有密密麻麻的支流,即使现在也能看到条条河沟。一旦山间有暴雨,这些从高处看像‘凤凰之羽’一样的结构会立刻把山洪分化,保证城邑的安全。”
把视线从崇山山尖拉回,眼前是13根4米余高的灰色柱子。柱子围成一个半圆,依夯土遗迹和远处的城墙高度还原,宽窄不一,柱间有缝。夏至日,日出时,阳光拉着柱间的影子,恰好从第二个缝隙里透过来,照到圆心处的夯土圆台遗迹上,像太阳在大地上刻下的指针。“冬至日能从第十二个狭缝看到日出的阳光,第七个狭缝透光时为春、秋分,依照这些缝隙泻到圆台上的光,可以确定20个节气,由此规划农时。”
“《尚书·尧典》中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正是这个意思。”高江涛在他15年的发掘时光里,对此地与尧的种种巧合着迷。“当地村民称太阳的音近似‘尧窝’,与对‘尧王’的称呼一模一样。而在甲骨文里,‘昜’就是一个人站在地平线上看太阳,恰是在观象台观测时的样子。而在出土的朱书扁壶上,有两个红色图案,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目前最早的文字,写的是‘文尧’,是对尧的敬称。”
陶寺遗址是否“尧都平阳”,成为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但中国文明的早期国家形态在此成形,已是共识。除却都邑的形式绵延不绝,此地铭刻着“华夏”的基因。“相比其他地区同时期遗址中出土的祭坛和通神的纹饰、面具,这里有等级分明的墓葬和炫耀武力的兵器,而且有记录农时的观象台和圭表,表明此地崇信的不是神,而是世俗的君主。”高江涛告诉我,汾河谷地上相互协作的农业生产,铸就了王权。“墓葬里虽然有很多武器,却会把武器封在盒子里。尤其在一座陶寺中期王墓的墓壁上,嵌有一个公猪的下颌骨,这是《周易》中描述的‘豮豕之牙’,左右两边各摆三柄带彩漆木把的玉石钺,含义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虽然陶寺遗址内也有战国时的人类活动遗迹,但公元前1900年以后,陶寺遗址上的人群便不知所踪了,直到近千年后,晋国的都邑才出现在崇山的另一面。
文章作者


刘畅
发表文章102篇 获得6个推荐 粉丝498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