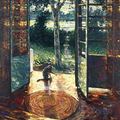饭桌上的中医与思想史上的中医
作者:读书
2019-04-11·阅读时长13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6806个字,产生3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王一方
中医乃学、乃术,由学术文献、理论与临床实务两部分构成,要展开有品质的学术批评,一是要花气力研读文献,研习理论,二是亲自临症,体验辨证。不过,近代中国,批评中医完全可以绕过这几个环节,只顾放逐意气,观点越极端,越能吸引眼球。于是批评沦为讥讽、谩骂,论辩(争)沦为声讨、罢黜,这一切似乎都与“饭桌”有关(此时胃肠充血,大脑处于缺氧状态)。民国时期,许多重大议题都在饭桌上商讨,夜读《张元济日记》,招饮宴宾是一等“正事”。一部民国文化史、出版史似乎就是一场场餐桌上的头脑风暴。部分留学生也有“饭后口舌运动”的癖好,他们于酒足饭饱之余都喜欢骂几句中医,以示新潮。朋友眼里的丁文江就喜欢“吃肉、喝酒、骂中医”,得闲时,还会将这份痛快书写出来,投书同人报刊,换来共鸣,也顺便换来下顿饭的酒钱。似乎并没有人撂下正业去系统研究中医。现如今,中医又成为“饭桌绝交话题”,拥护派与废止派之间常常恶言相加,拂袖而去,割袍断义。基本没有学理辨析的批评,只是一份情绪化的发泄与围观。然而,随着历史语境的淡去,饭后运动的激愤之辞成为“名流示范效应”,成为一些人中医认知站队的标杆,继而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裹挟利用,演化成为废止中医的闹剧。在两军对垒的擂台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科学与迷信,进化与退化,激进与保守,真理的唯一性与相对论,似乎高下立判,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背后隐含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开放与自主,文明互鉴与文化自信,民族主义与科学主义,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化,思想偏激与学术兼容,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玄观与玄妙,哲学上的实在论与现象学、实证主义与存在主义,医学中的科学性与人文性、技术与人性张力,都有坚深的学理基石和广泛的思想史论辩空间。对于坊间流行的批评泛滥,也不应该以“意气纷争”解读,而应该努力发掘其中的价值失焦现象及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动因,重新开启聚焦于理性、开放、建设性的论辩之旅。
一
屈指算来,“五四”即将跨入百年的时间坐标,重读当年“全盘西化”的檄文,分明是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滋生出国民发奋图强,抛弃传统包袱的决绝心态。盘点“五四”,有几大勋业,一是从思想上打倒孔家店,摧毁儒家文化的精神价值,二是日常生活上反中医,开启废止中医的序曲。陈独秀曾经抛出一个锋利的命题:传统生活的存在必定会阻碍现代化的进程。一九二九年余云岫提“废止旧医案”,特别昭示“扫除阻碍卫生事业(科学)进步”的宏旨。全盘西化肇始于此两端,文学上推广白话文成绩斐然,但后来遁入魔道,逐渐发展到诋毁汉字,欲废除汉字,实行拉丁化的疯狂之中,瞿秋白声言:“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钱玄同建议:“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鲁迅也认为:“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现今看来,恰恰是极端的科学主义、西方文化中心(优越)论导致历史认知的迷失与文化价值的断裂。这样一来,究竟是矫枉过正,还是玉石俱焚?激进时期,矫枉过正似乎在所难免。李泽厚曾感叹: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史书美在《现代的诱惑》一书中指出,“诱惑”一词暗含了服从和否定的双重过程,而且相互纠缠。一种方向是中国的现代主义者将现代性视为充满诱惑的、迷人的、值得向往的东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臣服于这一外来的范畴。这一过程也催生了中国的世界主义者,逐渐失去文化主体性。另一种方向则是在黑格尔的否定过程中将现代性转化为内在的固有范畴,在地区范围内修订、重新思考、定义、创造现代性,获得一份文化坚守,主体性被催生出来。如果历史是一架巨大的钟摆,五四运动之后的前三十年基本上朝着丢失文化主体性的方向摆动,后七十年开始有了后一种意识的萌生。站在百年的历史节点上,理应获得一份正—反—合的清醒,在这里,“反”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步骤,但不仅是反叛(打倒孔家店)或翻盘(全盘西化),还应该包含反思,如何面对传统?事实上,“五四”前后对儒家文化、中医以及阴阳五行的单向度挞伐是值得反刍的,譬如,以实在论的眼光看待阴阳五行是错误的,它并不是一种实体,而是生命内稳态的平衡与关系模型。
文章作者


读书
发表文章1317篇 获得1个推荐 粉丝20773人
人文精神 思想智慧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