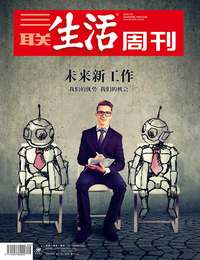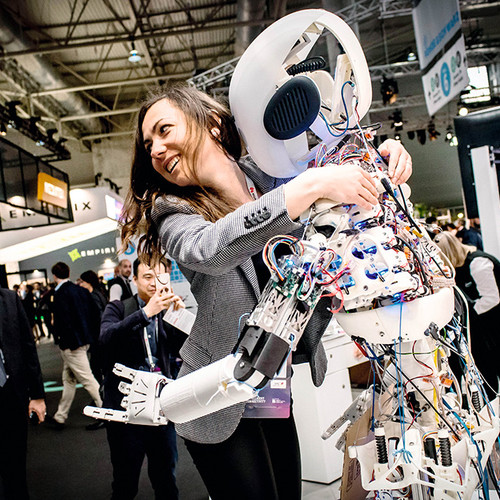江南弃儿:跨越60年的寻亲
作者:刘畅
2019-02-21·阅读时长14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7264个字,产生1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我想知道自己姓什么”
大年初五,山东日照莒县人鲁禾把24位朋友聚拢到饭馆里,免不了又聊起赵淑亮夏天寻亲的事。
“他当时只当是去嘉兴旅游啊!”饭馆家家爆满,鲁禾的两桌上,碰杯声不停,一群中年人最大的60岁,最小的44岁,都操着山东方言,时而哄笑,时而叹息,像一团忽明忽暗的影。51岁的赵淑亮不在场,却是最令人羡慕的人。那个皱纹爬上脸的细瘦农民敛不住的笑,在他们脑海中挥之不去。2018年8月的嘉兴寻亲会上了电视,赵淑亮的哥哥看到他的脸和自己的父亲简直一模一样,立刻联系了他。他被收养的地址和生辰跟他们送孩子的信息几乎都对得上。两边的人各自做了DNA检测,回去等结果。
“那天我正在地里干活呢,晚上9点多一回家,看手机上全是电话和信息,告诉我基因匹配度在99.5%以上。”赵淑亮因为等亲哥哥来看他,缺席了这场聚会,但他之后对记者讲述了第一次见到亲人的每个细节:看到基因匹配上的信息,他一夜未眠。加上二女儿刚考上大学,可谓是双喜临门。他没想到,自己在鲁南的小村庄里当了50年农民后,与600余公里外的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杨家浜村联系到一起。本想着提前偷偷看看生母,但为配合一同找到生母的其他人,他又憋了两天,请村里人和寻亲的朋友轮番吃饭,8月12日一清早坐着朋友的车,拿上给母亲买的新衣服,直奔故乡。赵淑亮的生父已去世多年,他下午到杨家浜村时,母亲带着他的哥哥被村民簇拥着,已等在村路口多时。都是瘦脸尖鼻子,母子二人却一人说嘉兴话,一人讲山东话。他把年逾八旬的母亲揽进怀里,母亲拉他回家,攥着他的手不松开。

“他当时流眼泪了,但也没太激动。”鲁禾是嘉兴寻亲会的组织者之一,比赵淑亮小两岁,已生华发,看起来更沉稳,却难以想见若看到自己的生身父母,该怎样抑制情绪。在座的山东人都是从江南抱来的。1959年到1961年是“三年困难时期”,单纯依赖水稻为生的江南地区遭遇饥荒,约有5万的婴幼儿被父母遗弃;从那时开始到70年代中期,“江南弃儿”加起来近10万,弃儿大部分经由南下干部,被送往他们的老家——山东、河南、安徽等粮食作物更加丰富的北方地区。
“无锡宜兴的吕顺芳最早从2000年开始在无锡、南京、常州、江阴等弃儿多的城市办寻亲会,收到全国各地上千份资料,目前找到300多对家庭。但她曾经举办的寻亲会都在江苏,而浙江的嘉兴、海宁作为当时粮食和经济作物受灾的重地,当时也送出了很多孩子。”鲁禾找了亲生父母十余年,却寻到越来越多的同路人。“从2016年开始,嘉兴那边的人也加到我的微信群里,有些寻找自己的父母、有些寻找自己的亲生兄弟,大家既是寻亲人,又当志愿者。去年8月,我们与嘉兴媒体一起在当地举办寻亲会,来了上百号人。寻亲会后,我们的寻亲群从20多个人,一天内激增到400多人,目前还在不断增加。”
加入寻亲群的人都亲如一家,鲁禾同到场的寻亲者讲好,以后每年这个日子不用通知,大家一定来团聚,图个相互安慰:
“别人不理解,过了五六十年,有些孙子都有了,为什么还要找亲生父母呢?”
“五六岁时,村里的小孩就骂我是‘拾’来的。我问养父母,他们说:‘对啊,小孩不都是大人从沟里捡来的吗?’又过了两年,我去看别人家抱养的孩子,旁人却指着我说:‘你和他一样。’”
鲁禾的养父母比他大40岁,他上面一个姐姐,也比他大近20岁。虽是抱养,养父母也是老来得子,对他宠得不得了。他哭着回家问养父母,他们嘴上不承认,却找嚼舌头的家长理论,动起手来。“父亲被打得头破血流,我在旁边看着,又心疼,又恨极了亲生父母。我当时就想,非要找到他们,质问为什么不要我,然后就不再理他们。”
在农村,弃儿们几乎都有类似的经历,幼时不知自己来自何方,只把养子的“真相”藏在心里。他们几乎都像鲁禾一样,儿时养父母便已近中年,上面有数个姐姐,相继出嫁,一个人度过了孤僻的童年。独处让他们总是和自己对话。鲁禾记得,小时候什么农活都干,但别人家兄弟几个一上午就做完的活,他得一个人在地里干到晚,“那时我做梦老幻想,自己也有很多亲兄弟”。
不过鲁禾终究是幸运儿。他不像许多弃儿,孤寂的童年也意味着随着年龄渐长,家道日益贫寒,鲁禾上小学后便被姐姐接到县城,从此摆脱掉邻里的闲话,没人再知晓他的出身。城市生活也让他从取笑对象变成没进过城的儿时玩伴眼中的“上等人”。

但他对亲生父母的怨恨却并未减弱,这也成为他最初寻亲的动力。20多岁时,鲁禾得知自己是姐姐抱来的,姐姐当时在外地上大学,他就想着自己是不是从学校边上抱的。直到他娶妻生子,看着妻子十月怀胎的苦,体会养孩子之难,他的怨恨才转为理解。“那时候怀孩子不像现在这么多补品,炖只老母鸡都没有,我们只能买个鸡架子,炖起来补补,可想而知生我时得多困难。我不能想象谁能轻易把自己的孩子遗弃。”
弃儿心中的和解总会以各种形式到来。“抱养的孩子没母乳,只能喝羊奶,但营养不够得加糖,糖却得凭票,那时都得托关系。”赵淑亮与众不同,他在养父母家有个与他同岁的姐姐,他吃过母乳,也知道加糖的羊奶来之不易。虽然同样儿时便从伙伴嘴里知道了身世的真相,但生活的困苦使他早早就把对亲生父母的怨恨消解,玩伴的嘲笑更像是田里卷起沙子的风,虽然迷眼,但对小孩来说,来得快,忘得也快。一旦男孩长成了壮劳力,无人再有闲话,身世不过是脑后一个不甚漂亮的胎记。
寻亲的“执念”加深,源于为养父母养老送终之后,他们又成了无根的人。“我想知道自己姓什么,想告诉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从哪里来。”养父母去世后,鲁禾每每看到电视里认亲的节目便默默流泪,他的妻子嫌寻亲麻烦,岳母却不忍他难受,让他向姐姐询问真相。鲁禾找到年逾七旬的姐姐,提起话头便引来姐姐的一通恸哭,知道他不会背弃养父母这边的亲戚后,姐姐告诉了他真相,他是从嘉兴毛纺厂里抱来的。
“十几年前,我到乡下废弃的老宅找线索,那里连姐姐上中学的课本都完整无缺地留着。”鲁禾认定亲生父母遗弃时总要留些东西,课本里果然掉出一张红纸条,却让他痛苦万分。纸条正面有他的生辰八字,他知道自己身份证上的生日原是农历的。而背面有收款人和交款人的名字,以及30元的字样。“收款人是化名,交款人不是我的生母,却必定与她有关。但我去嘉兴查,也查无此人,也是用化名,不愿让人找到。”
文章作者


刘畅
发表文章102篇 获得15个推荐 粉丝498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