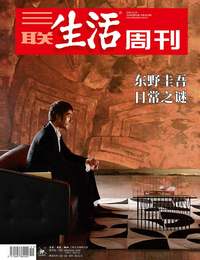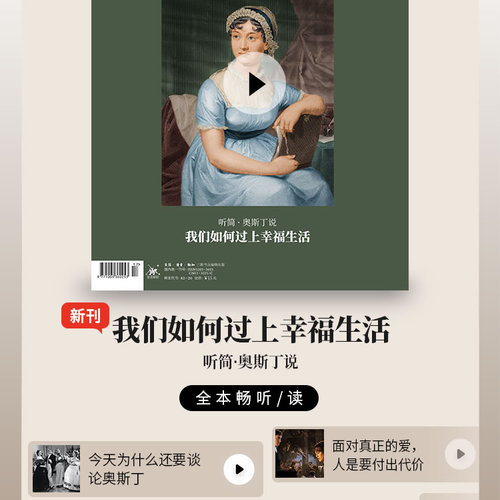匿名写作,反对与偏见
作者:孙若茜
2018-12-21·阅读时长11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895个字,产生6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简单来说,“匿名作家计划”就是一场文学界的“蒙面歌王”。据说,这项计划最初被张悦然在一次网络会议上提出时,用的就是这个概念。它既是一个写作计划,也是一场比赛,规则很简单,写作5000~2万字的中文短篇小说,主题、内容不限,投稿者的身份、年龄、国籍也不限。严格要求的只有“匿名”,对于读者和评委,作者要始终保持神秘,不能通过任何渠道透露出自己的身份信息。历时半年,最终,有一名优胜者。
几乎所有匿名写作者的最终目的都是希望读者的关注回到作品本身,不管最初隐匿姓名是为了回避社会中的性别歧视,还是写作了敏感的主题;是单纯希望作品和自己的生活不被搅为一谈,还是不过想做一个游戏。他们追求写作的自由感,对抗把文学作品放在作者的身份之下或其以往写作的坐标系中去阅读而带来的偏见。
在过去,匿名写作的成功例子是有很多的。但成功的前提首先是被发现。如今,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失败的例子大概更能说明问题。2011年,当J.K.罗琳以罗伯特·加尔布雷思的名字写作了侦探小说《布谷鸟的呼唤》并投给两家出版社时,收到的不只是退稿信,还有让她不如先去读个写作班的建议。这本书还是出版了,但只卖了500本,在英国亚马逊网站排名5000开外。而事情的扭转就发生在J.K.罗琳的“揭面”时刻,《布谷鸟的呼唤》销量增加了507000%。
当我们留给文学的耐心越来越少,“倾向于相信作者并过于相信作者”,就总是会选择熟悉的作家去阅读。实际上,一个尚未出名或名气不足的写作者和一个匿名作家之间,被读者发现的概率其实是没什么差别的。换句话说,在这样的环境下,“留给年轻写作者的机会变得特别少”。
与其说,“匿名作家计划”是在反对阅读的偏见,不如说是在对抗一种忽视。当年轻作家与知名作家的名字成为编号被并列在一起一决高下时,我们不会,甚至说不敢错过这些编号下的任何一篇作品。“匿名作家计划”的首奖就是在这个前提下产生的。
12月15日,当作品《仙症》被宣布折桂时,作者郑执的身份还没有公开。他蒙面上台,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台下的议论窸窸窣窣。面具拿开,名字也出现在大屏幕上,那一刻,现场反而安静了。认识他的人真的不多,以至于没有像其他几位作家揭面时的那种集体的恍然大悟:阎连科、路内、双雪涛、马伯庸……当这些名字出现时,台下是泛起了惊讶声的。
就这样,郑执站在聚光灯下,被当天在线观看那场决选直播的26万人认识或重新认识了,他的《仙症》开始在朋友圈里被转发,接着,很多人买了他的小说《生吞》。郑执此前已经出版过几本小说,而且《生吞》很有反响。但是他的小说似乎没怎么在传统期刊上发表,没有进入严肃文学的视野。
这是“匿名作家计划”最终的结果,但这显然不是最重要的——“匿名作家计划”并不会成为主流和趋势,也许甚至都不会对当下的文学环境做出真正的改变,同样,郑执的被发现也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拥抱。花掉几个小时的时间去观看一场三个作家评委对六篇作品的品读的人,肯定不只为了等待一篇作品的脱颖而出,重要的是,经历了一场集体回到文学本身的体验。
作者真的有可能依靠匿名,实现真正的退场,还原读者对作品本身的关注吗?以下是本刊对《鲤·匿名作家》主编、作家张悦然进行的专访。
文章作者


孙若茜
发表文章103篇 获得7个推荐 粉丝708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