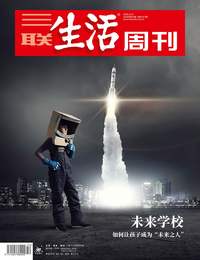董其昌的世纪
作者:张星云
2018-12-12·阅读时长10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5487个字,产生2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书画船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在北京任职翰林院编修兼皇子讲官的董其昌因鼓励失宠的皇太子继承皇位,受到皇妃郑贵妃的嫉恨,被调离京城任湖广副使,明升暗降。他想躲避当时宫廷的激烈内斗,却又不愿放弃官位,于是他想了一出权衡之计,以身体不佳为由不去赴任,奉旨以编修身份回家乡养病。这是董其昌为官四十八载起起落落中第一次引退还乡。
回到老家松江,处在仕途低谷的董其昌与旧友们纵情山水,鉴赏书画。他曾认真地记录过一次与家乡老友陈继儒泛舟黄浦江的远游,“随风东西,与云朝暮,集不请之友,乘不系之舟。惟吾仲醇,壶觞对引,手著翰墨”。他们两人就这样没有目的地乘风漂荡,董其昌还在船上乘兴绘画《山水图》送给陈继儒。
这种泛舟远游在董其昌所处的明末文人群体中最为盛行。唐宋以后文人聚集地从北方转移到江南。江南河道拱桥遍布,舟船不仅是世代当地居民的代步工具,也渐成为文人远眺赏景、举办雅集的方式。按董其昌的话说,“舟行多暇”。行舟闲暇之余,他会在船上作画赏画。
艺术史学者傅申将这种舟船命名为“书画船”,认为董其昌的长卷山水,与他在书画船上看到的实际景色有关。古时船慢慢行,景致跟着慢慢移,人无需脚力劳顿,就在这份从容中把全景山河欣赏完了。
万历二十七年(1599),董其昌奉旨为持节使臣赴长沙,可谓平生最重要的乘船旅行之一。他从北京出发,取道嘉兴,一路访画游历。他此行更大的收获,是乘船在洞庭湖和潇湘道中的沿途所见景致,“蒹葭渔网,汀洲丛木,茅庵樵径,晴峦远堤”。第二年完成旅程返回北京后,董其昌购得一卷董源绘画,展开此卷时,“令人不动步而重作湘江之游”。此画签题当时已经模糊,但董其昌凭借着自己曾经所观的实际景致,认定此画便是《宣和画谱》所记载的董源《潇湘图》。
后来董其昌对此卷爱不释手,一再题跋。万历三十三年(1605),董其昌赴任湖广提学副使,再登书画船,重走湘江之旅。这回他一路带着董源《潇湘图》和米友仁《潇湘奇观图》,与实景相印证,随即在船上再题跋:“秋日乘风,积雨初霁,因出此图,印以真境,因知古人名不虗传,余为三游湘江矣!”字写得龙飞凤舞,非常奔放。
正是这些最直观而又最难得的经历,让董其昌对董源、米芾一派山水画有了豁然顿悟,是同时代一般鉴赏家所没有的视野。

后来他尤其推崇王维、董源、米芾、高克恭和“元四家”的绘画,认为他们的作品富有诗意,有文人的浪漫色彩,而不拘泥于形似,并著书立说写下《画旨》,提出“南北宗论”,将古代众画家归纳为两个门派,对后世影响巨大。但要说他的这套理论真正开始被视为中国艺术史论的开端,就要等400年之后了。
独开中国画史
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凌利中告诉我说,1992年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举办展览“董其昌的世纪”,展览期间进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西方学者第一次提出将董其昌视为中国首位绘画史学者。
在“南北宗论”这套理论中,画史的山水画家们一一被放进两个看似对立的阵营,一派由唐画家李思训为鼻祖,另一派的最初领袖则是王维。董其昌没有按照画家们所生活的地理位置划分,而是借鉴了禅宗北渐南顿的方式,将两派分别命名为“北宗”和“南宗”,北宗艺术家们全是专业画家,他们努力追求绘画的写实效果,而南宗画家们则大多为文人雅士,推崇自然天赋。
“实际上在中国艺术史被纳入西方近现代艺术史研究体系前,中国传统画学也将董其昌视为极其重要的人物,只是表述方式不同。”凌利中说,在传统画学理论中,明末董其昌与明初的赵孟頫一同被视为文人画一脉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尤其后来清初四僧、四王,金陵、新安画派,乃至晚清,这300多年的画坛风格无不受到董其昌的影响。而作为书画藏家的董其昌,也将自己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民国书画鉴藏家吴湖帆,后者又培养出了张珩、沈剑知、徐邦达、王季迁等现代书画鉴藏大家。
但与其影响存在巨大反差的是,半个世纪以来,除了30年前在上海举办过一次学术讨论会外,几次董其昌书画展和国际研讨会均在大陆以外进行,包括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澳门艺术博物馆、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和东京国立博物馆。因此本次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便成为大陆首个董其昌大展,展览以上海博物物馆藏为主,同时向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海内外15家重要收藏机构借来藏品,总计154件,其中来自上博馆藏的展品有80%为首展,既包括目前传世所见董其昌最早的画作《山居图》,也有其绝笔之作《细琐宋法山水图》,涵盖他48年的创作过程。
除了83件董其昌的书画作品外,展览还在第一部分展出数件董其昌曾鉴定收藏过的晋唐宋元名迹,其中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王羲之《行穰帖》、浙江博物馆藏黄公望《剩山图》(《富春山居图》前段),还有王羲之《寒切帖》、颜真卿《楷书自书告身》、郭熙《树色平远图》、赵佶《竹禽图》等。凌利中说,这部分展品同样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清楚地体现了董其昌最初整理总结艺术史的动机。“题跋、品评只是外在形式,他进行大规模收藏,正是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中国绘画发展遇到了困境,已经持续一两百年停滞不前,因此他才决定梳理中国古代绘画史,总结前人经验,以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破旧立新,为他自己的绘画创作所用。”
凌利中为此专门对经董其昌鉴赏题跋的传世作品进行了一次梳理,总共近300件,其中不仅有西晋陆机《平复帖》、东晋王珣《伯远帖》,还有顾恺之《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展子虔《游春图》,怀素、颜真卿书法六件,董源和巨然山水画五幅,苏轼和米芾的书法有十几件,赵孟頫书画达20幅,而“元四家”“明四家”书画更是不计其数。
董其昌鉴赏收藏经典书画之丰富,甚至可以与宋、清两朝皇帝内府收藏的《宣和画谱》和《石渠宝笈》相提并论。作为一名士人,他的收藏能够达到如此高度,不仅因为他对书画的热爱,也与他的仕途经营分不开,足够的财力及社会身份让他广识文人名流,博览历代名画。
文章作者


张星云
发表文章193篇 获得9个推荐 粉丝1031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