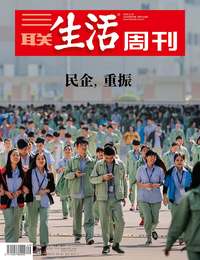瑞士的蕾丝之都
作者:杨聃
2018-12-05·阅读时长9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4800个字,产生23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探访圣加仑
从维也纳到圣加仑的火车车程约7个半小时,看着窗外景色连续不断地变换摇移,城市气息与山谷风光的平缓切换,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火车充斥了19世纪的文学,而飞机在20世纪没做到。记得王尔德曾调侃道,他从不会忘带自己的日记旅行,因为一个人在火车上总需要读点写得好的东西,不知他是出于自恋,还是没有体验过旅途中的风景线——时而平坦如织,时而蜿蜒起伏,恬淡安谧,很难让人“审美疲劳”。
不知过了多久,两辆火车“擦肩”倏忽而过的那股迷离感,让我从美景中抽了神。试想蒸汽时代,夜间火车的鸣笛声,透过车窗留下的灯光点点,抑或是驾驶员和站长之间交换的类似情书暗语般的话术,都能激起人们的浪漫情愫。对此,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曾非常不浪漫地总结到,当代文化催生出一种视觉文化,这一变革的根源与其说是作为大众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不如说是人们在19世纪中叶开始经历的地理和社会的流动。铁路让乡村和住宅的封闭空间让位于旅行,让位于速度和刺激。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康斯坦丁·贝魁尔给予过火车极高的赞美。他认为,借助铁路和轮船的旅行比法国大革命更有效地传播了平等和自由。不同财富、地位、性格、习俗、着装风格的人因为旅行聚集在同一生活场景,戏剧性地展示了民主的状态。不过和他所描述的不尽相同,某些“不平等”在早期的旅行中客观存在,比如从1890年到1940年间,头等车厢的乘客能得到一整套享受——在风格优雅的餐车享用现场烹制的美食,安静地平躺在宽敞的床上休息。而普通车厢的乘客远没有那么惬意了。如今,欧铁车厢也分一等和二等,除了空间排布的略微不同,几乎同样享受着列车的舒适与便利。我不禁好奇铁路还产生了哪些文化产品?网络上搜出的答案五花八门,其中两个比较靠谱:车票(相继派生出身份证、戏票、旅馆房间钥匙和信用卡)与标准时间。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是,火车让上层绅士接受了威士忌,其缘由还没看完,圣加仑就到了。
圣加仑在博登湖和森蒂斯峰之间,地处瑞士、德国、奥地利和列支敦士登四国交界。我们到时本应是初雪的季节,却还延续着秋日的明媚。司机跟天气一样热情,一路上操着口音浓重的德式英语介绍着,这座城市由一位流浪的爱尔兰僧侣所创建,故事细节跟宗教和熊有点关系。他指着远远能看到塔尖的教堂说,大部分游客都是冲着它来的。
对那座巴洛克大教堂和比邻的洛可可图书馆我早有耳闻。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组合,它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3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图书馆馆藏图书17万册,其中有2100多部珍藏手抄本,最早的可追溯到8世纪。大部分书籍封面的材质是亚麻而非皮革,饰有精美的刺绣。这个细节“泄露”了圣加仑和高级时装的历史羁绊。从中世纪开始,纺织作为支柱产业在瑞士东部蓬勃发展。圣加仑先以亚麻织物闻名,后继的刺绣和蕾丝为它赢得了更多国际赞誉,据说老城区九成的房子都是用纺织工业赚来的钱所建。
通往教堂的蜿蜒小巷上,成群的国际留学生沿着铺满鹅卵石的街道漫步,还有一些穿着考究的人在等公交车。司机告诉我们,可不要小瞧了他们,那些人当中不乏讨论巴黎、米兰和纽约潮流的时装设计师。街角的面包店外,西装笔挺的金融人士接过硬皮面包,准备就着圣加仑特色油煎香肠大快朵颐,旁边一排人正在耐心地等待“杏仁馅蜂蜜饼”新鲜出炉。说起杏仁馅蜂蜜饼司机又滔滔不绝起来,简直把它夸成了圣加仑面包店的骄傲。原材料无非都是面粉、蜂蜜、糖佐以茴香、芫荽和丁香,但每家店都有其世代相传的配方,他心目中最棒的要属位于“纺织小径”的Café Pelikan。


纺织小径是圣加仑最繁华的街道之一,饰有洛可可风格凸肚窗的精品酒店和餐厅鳞次栉比,它们大多是刺绣工坊的遗址。作为一种古老的“炫富”方式,凸肚窗建得越大、装饰越多说明主人越富有。19世纪末,圣加仑的刺绣品产量占全球的50%,盆满钵满的工坊主开始大肆扩建凸肚窗。与此同时,美国人也专程跑到瑞士东部来购买绣品,当时新落成的办公大楼都以华盛顿、大西洋、大洋洲来命名。虽然Café Pelikan的杏仁馅蜂蜜饼味道如何不得而知,它的凸肚窗倒是华丽异常。四块代表旅行与探索的石雕壁画上分别刻有四大洲的名字,唯独少了澳大利亚,想来库克船长在1770年才发现它,比窗子建造的年代晚了好几十年。除了宗教故事中的天使和神兽,凸肚窗上的装饰还包括大量象征丰饶的水果和农作物。事实上,圣加仑的高海拔并不利于农耕,浮雕中的呈现只有亚麻是这儿“土生土长”的。
几个世纪以前圣加仑人为了织出高品质的布料,将亚麻纤维铺在地上用晒日光的方式自然褪色,一铺就是延绵几英里,远远望去犹如常年覆盖着皑皑白雪。晒亚麻的地方被人们称为Bleicheli,源于德语“bleichen”,漂白的意思。老话儿将亚麻布称为“白色的黄金”,喻示了它对当地经济做出的贡献。1753年这份“殊荣”让位给了由土耳其工艺演变而来的刺绣。如今位于城市西部的Bleicheli区给人的印象不再是“白茫茫”而是“红彤彤”。在艺术家皮皮罗蒂·瑞斯特和建筑师卡洛斯·马丁内斯的合作下,铺着人造地毯的红色广场作为城市休息室,“呼吸吐纳”着当地人与慕名而来的游客。
文章作者


杨聃
发表文章131篇 获得10个推荐 粉丝470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