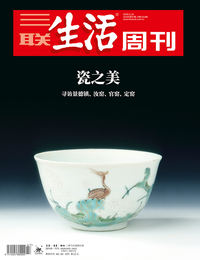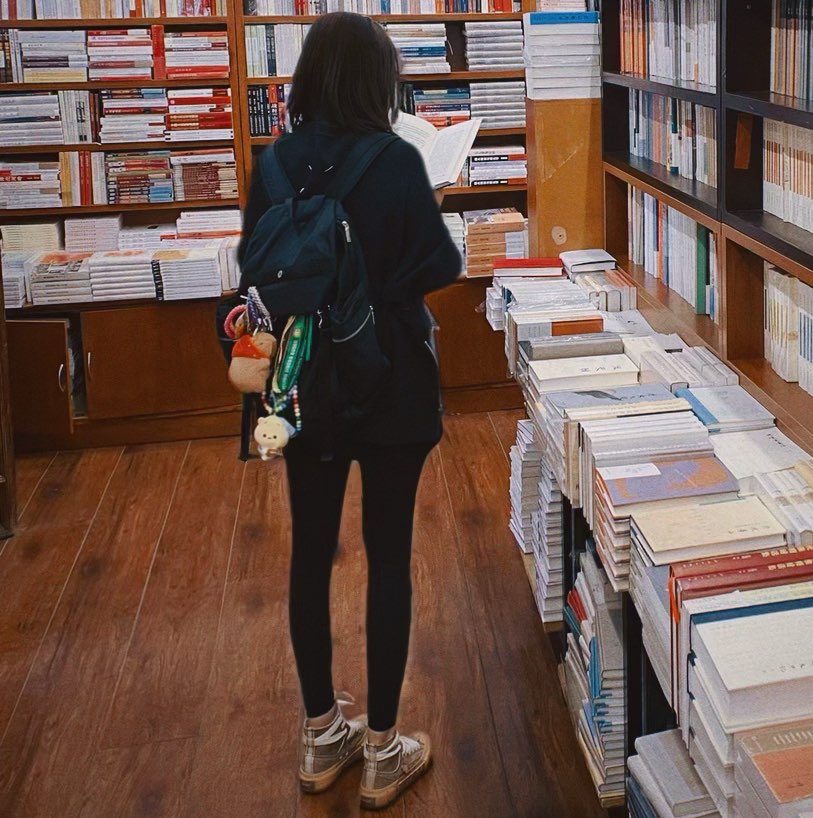景德镇寻瓷:手工体系里的瓷器史
作者:贾冬婷
2018-11-21·阅读时长22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11235个字,产生182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碎瓷片上的城市
周一早上7点刚过,我们赶到了古玩市场。这里从凌晨4点多就开市了,是景德镇有名的“鬼市”。看着已经大亮的天色,摆得密不透风的摊位,心下也明白,这时候已经碰不到“鬼”,也捡不到什么“漏”了。带我们来的罗国新倒是不以为然:“这两年流出来的官窑瓷器越来越少了。即便有,也不会摆在明面上。”
摊位之间以垫布来划分,大部分是一块红布,或织锦或丝绒,试图给上面摆放的器物衬托出仪式感,但在满坑满谷的瓷器堆里又有些力不从心。这些器物乍看起来都大有来历,青花大罐,粉彩小碗,还有火热一时的“文革瓷”,让人挪不动步子。让罗国新来看,他甩出一句“新做的”,就径直去里面的碎瓷片区了。在这片区域,罗国新像是国王出巡自己的领地,所到之处,小贩们纷纷迎上来招呼。罗国新戴一副厚厚的眼镜,人称“瞎哥”,但他的眼力非但不瞎,而且因为在瓷片堆里历练日深,难得有赝品逃过。不时有人拉住他,郑重地拿出件宝贝请他鉴定。据说凡是经他鉴定为真品的,一旦日后被确认不对,都由他来买单,几乎像是个人“特技秀”。也有摊主专等他来,打开后面的蛇皮袋“献宝”……他今天收了一块乾隆仿秦汉时期的瓦当残片,并不贵,700块钱,但正好和他现有的几块对得上,差不多可以拼成一个完整的了。
碎瓷片里有什么奥妙?这些瓷片按照大小、年代、颜色分门别类摆放着,青瓷、黑釉、红釉、青花等,很多还带着泥,或者破损得辨认不出原属器物。在我们外行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一个仿制精美的完整器诱人。这里面最“完整”的,是一个个打磨光滑的圆片,上面画着各种青花纹饰:鱼、龙、牡丹、草叶在疾风中飘荡、两个童子在玩闹……这些都是瓷碗的圈足,听报价也平易,“2毛”,就是20块钱,大一些有龙纹的也不过50块钱。但在罗国新看来,碎瓷片的价值不在完整和好看,而是每一个残片中携带的历史信息。或许足底的几个汉字会告诉你这件器物的时间,而那些纹饰的画法或许又会揭开什么历史谜团。罗国新赞美这些捡瓷片的摊贩:“他们是默默无闻的考古工作者。”
“以前我都是提个篮子来,碎瓷片论篮买。”罗国新告诉我们,现在古瓷片少了,他也淘得比较精了,来“鬼市”只为查缺补漏。他在落马桥出生长大,那里曾经是元青花官窑窑址所在地。小时候走路不老实,常常一踢就能踢出一块瓷片来。80年代时,他做瓷器生意,卖“超万件”,一种直径有2米的大缸,编一个窑工呕心沥血造缸的故事,一个缸能卖100万,他卖出去了12个,大赚了一笔。后来转做出口,去广州、深圳、北京,渐渐地生意没那么好做了,他又想起了家乡景德镇。自从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起,多少景德镇的好东西在中国消失了、湮灭了。他在10年前回到景德镇,一头扎进碎瓷片的世界。
跟着罗国新来到他家,像是掉进了兔子洞,几乎被碎瓷片给淹没了。一楼是拼接好的碎瓷片龙缸为招牌的瓷器店,二楼则完全是碎瓷片仓库,他工作的书桌、睡觉的床都在这里,拉开床头的柜子和抽屉,里面也都是瓷片。最夸张的是阳台,堆放着若干塑料大筐,里面是分门别类的瓷片。他常在这里挑拣,挑出那些隐藏历史信息的,或者有可能和别的瓷片拼接在一起的,拿到书桌研究,就像是玩拼图游戏。这绝对是一个需要巨大耐心的游戏,常常为了凑出一个完整器,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他拼出过两个明代“最大器”龙缸,那种画了青花龙纹的大缸,直径达70厘米,在当年烧造极为困难,甚至引发了窑工童宾不堪忍受跳进窑缸,后被奉为“窑神”的故事。只是找齐碎片就花了四五年时间,把它们拼在一起又花了三个月,如今较好的那一个给了景德镇陶瓷博物馆展示。他给我们看刚拼好的一个青花杯,成化年间的,大概碎成了七八块,他前后花了几万块钱凑齐这些碎片,再用金箔镶上,拼好后能卖十几万元,而这样一件完整器的市场价是500万元。

某种意义上,如今的景德镇,就是一个建立在碎瓷片上的城市。“瞎哥”说,景德镇最好的东西是官窑,这些东西大多直接运去了北京、进了皇宫,留在景德镇的,都是不合格的次品,而且大多按制度就地砸碎掩埋,碎片留在了窑厂遗址中。以前,浮梁古县衙周围一带的田地里,昌江河边,到处都散落着各朝各代的古瓷片。前些年的城市改造中,也经常能发现一些碎瓷的填埋坑,还有很多盗挖,经过一道又一道地转手,很多官窑碎片流到民间。这两年,对窑址的保护愈加严格,市面上的碎瓷片才渐渐少了。
在景德镇御窑厂的修复与研究中心,对碎瓷片的拼接就是日常工作。这里也是故宫与景德镇合作的“故宫学院”所在地。现场所见,几个年轻人正在拼接手中的残片,周围的游人来来往往,他们却如入无人之境。从完成的器物来看,碎片共有两类,一类是青花瓷枕,一类是青釉刻花高足碗。景德镇考古所的李军强告诉我们,这些是2014年在龙珠阁北麓抢救性发掘出来的,大部分是“空白期”——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器。碎瓷片修复前,要先分釉色,再分器型。目前修复的这两类,青花瓷枕相对容易拼,毕竟纹饰可以对接,器型也特殊。青釉刻花高足碗就难了,碎片与碎片之间太相似,难以分辨。李军强说,像这样的一个遗址发掘出的1000多件器物,要想全部修复完成,快则两三年,慢则七八年。而从上世纪70年代御窑厂考古开始算起,存留下来的碎瓷片已经几十吨,今后修复工作会比发掘更艰巨。
碎瓷片的价值,还在于对历史信息的补足和确认上。这段时间,故宫博物院正在进行嘉靖、隆庆、万历瓷器对比展,所谓“对比展”,是指故宫博物院传世的完整瓷器与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碎片复原瓷器的对比展示。景德镇考古所所长江建新告诉我,这已经是明代御窑瓷器对比展的第六次,也是收官的一次。对比展的一大意义在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瓷器大多是流传有序的,部分器物可能难以断代,而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遗物因为有绝对地层可考,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都比较明确,可以提供一个标尺。“比如现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馆里的一件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是中国最早的斗彩瓷器。上世纪80年代在西藏萨迦寺发现过一个斗彩碗,发现者怀疑是宣德时期的,但当时人们认识还不到位,断代为成化器物。1988年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发现了两片与这个碗纹饰一模一样的瓷片,带有‘宣德年制’的款,且位于宣德时期的地层,这就证实了萨迦寺那个碗其实是宣德时期的,说明中国的斗彩瓷器从宣德时便开始烧制了。可以说,这是一件改写中国陶瓷史的器物。”

御窑的遗产
站在御窑厂制高点龙珠阁上,依稀能够看见西侧的昌江河。它穿城而过,自北向南流向长江。古时景德镇名为昌南镇,就是因为地处昌江之南。景德镇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睿明指出,这条大河意义非凡:瓷土、烧窑的木柴、烧成的瓷器,要靠河道的运输;水流又为窑业的生产提供诸多免费动力,如捣碎瓷石,用的就是水车。而周围几座高高的山峦,曾盛产制瓷不可或缺的原料之一高岭土。
尽管“水土宜陶”,但景德镇“瓷都”地位的确立也是一波三折。宋代时,这里以“青白瓷”闻名,白里泛青,青中透白。涂睿明说,青白瓷其实是白瓷的一种,在白色胎体表面,附上了一层略带青色的透明釉。这种青白瓷的色泽和质感,看上去仿若玉的质感,于是以“假玉器”闻名。古时这里地属饶州府,于是所产瓷又被称为“饶玉”。而瓷器在中国的源远流长,一直被认为与自古以来的“尚玉文化”息息相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宋真宗在收到此地进贡的瓷器之后,把年号“景德”赐给了这个小镇。但是即便如此,景德镇在宋代仍面临众多窑口的竞争,特别是号称“五大名窑”的汝、哥、官、定、钧,而且还面临当时的单一制瓷材料——瓷土资源的枯竭。到了元代,景德镇幸运地发现了一种新的黏土材料——之后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高岭土”,改变了景德镇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陶瓷史。人们发现,将高岭土与原来的瓷石混合,可以大大提高瓷器的硬度和白度。这曾是欧洲人历经几百年才破解的制瓷“二元配方”,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高岭土是骨,瓷石是肉”,骨肉均匀,瓷器才能变得致密无孔。
如今,景德镇高岭土矿已经封闭,靠周边类似资源替代,而瓷石依然在城市周边开采着。其中一个产瓷石的山谷是三宝,始烧于五代时的湖田窑和杨梅亭窑所在地。打造了三宝蓬艺术聚落的肖学峰带我们深入山谷,走了没多久,就看到一条倾泻而下的溪流,溪流旁的棚屋里,水碓仍在不停歇地捣碎瓷石。溪流引过来的水流入水车里,水车为几根碓棒提供动力,这种看似原始的技术几百年来未曾改变,肖学峰说,这比机器粉碎得更细致,因此一些做高仿瓷器的作坊依然有需求。粉碎后,再后经过淘洗、风干、晾晒,劈成砖块,就变成一块块码放整齐的“白墩子”——制瓷标准化工序的一部分。
文章作者


贾冬婷
发表文章79篇 获得43个推荐 粉丝1346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助理、三联人文城市奖总策划。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