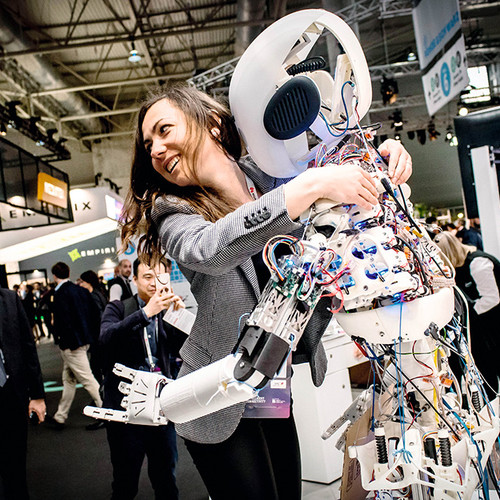朱苏力:送法下乡40年
作者:刘畅
2018-09-29·阅读时长9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4645个字,产生17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口述/朱苏力 采访、整理/刘畅
1997年的时候,我到湖北农村走访,连西部的大山区也去了,发现基层法官那时非常穷,家在县城,但平时住在村里。与外界联系要打长途,村里付不起电话费,就把电话锁上,只能来电话时接。记得有一次同一位40多岁,从部队转业的基层法官打交道,在喝酒时的种种细节里,我发现他极聪明,我考察人家时,人家也在考察我,见我尊重他们,他们才愿意跟我讲真话。
我大老远与他们坦诚相见,是因为当时正赶上又一轮大规模裁军,先前将复员军人分配到基层法院的政策引起广泛争议,觉得转业军人的军人作风不利于法治的专业化;又赶上当时推进司法改革,其中之一是抗辩制改革,过去由基层法院的法官调查案件事实,现在要让控辩双方请律师调查;另外就是把矛头指向基层审判委员会制度,学界以外国经验为基准,认为它违反了司法规律。
我当时已博士毕业归国,在北大任教。大家彼时正在热议电影《秋菊打官司》,流行的解说是,觉醒的中国农民拿起了法律的武器,我则认为,这其实反映了法律进入中国农村基层后“水土不服”,农民发现自己受骗了,所谓的法治不是农民消费者需要的商品,而是法律人试图推销给农民的伪劣产品。
所以,面对那时的思潮,我认为法治一定要关注中国人民的需要,中国的法学也得从中国法治实践中总结提高。部队里读的《毛选》,让我一直坚信“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上大学时读费孝通的著作,在美国的留学经历,又让我对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有了更深的体认,能够拉开距离看问题。有着这些智识准备,我就打算亲自实地看看,没有受过法律训练的基层法院的法官,如何处理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案件。
我原是不懂农村的,我本身是城市人,15岁当兵,有两年驻在村里,部队的干部战士几乎全来自农村,但与他们5年多的长期交往,让我对农村也只能算有点直观了解。1995年开始,我应邀到武汉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办的法官班授课,学员都是基层法院的法官,我借此机会访谈这些法官,又去了他们工作的各地法院。在田野调查中,颠覆了我的许多观念,让我变得保守了。
最典型的是基层审判委员会制度。法院法官遇到一些疑难、重大案件,主审法官会把案件交到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我在调查之前,也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起码不利于法官的独立判断。但我在湖北访问了100多位基层法官,他们也谈及了我担忧的问题,也认为肯定有弊端,也有坚持认为自己的判断更合适,审委会的判断反而有误的情况,却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制度不好。想想谁都是“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不愿被人管着,他们为什么还能接受呢?
法官给的理由很多,主要理由还不是面对疑难、新颖案件,年轻法官解决不了,审判委员会的委员资历通常比较深、有经验,他们需要审委会把关,或需要统一法律适用的尺度,最重要的原因是,基层法院的法官生活在熟人社会中,活得很难,工作也很难。
基层法官基本都是本地人,在熟人社会里,许多人在解决纠纷时,会以各种方式找到法官,法官不可能六亲不认。但审判总会有个结果,不可能两全其美,甚至公平的判决常常会令双方都不满。即便法官判决上会秉公执法,在别人找到他时,他既不能公开表示六亲不认,也不能先都应承下来,那等于骗人家,结果出来后,人家会更愤怒。在这种情况下,法官需要有个制度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审判委员会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机制。被人逼急了,法官会说:“这我说了不算,合议庭说了也不算,这得上审委会”。
审判委员会是不得已的选择,转业军人问题、抗辩问题,同样如是。理论上讲,我非常赞同法官应当来自法学院毕业生。问题是即便今天,在能进企业、律所、政府机关的前提下,有几个正规法律院校的毕业生愿意长期坚持在中西部基层法院或人民法庭的?因此,在我调查研究的年代,甚至10年前,转业军人在基层法院人民法庭已是素质相对高的群体。我退伍时才21岁,而我在部队时,周围那些特别聪明的人,虽然正规学历比我在部队时高,但他们比我大5到8岁,退伍时都恋爱结婚了。婚后需要养家,怎么去上大学?像我的父母是中层干部,足以养活家庭,我才有余力考学,可当时多少家庭有这种条件?因此,在中国这个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至少在特定时期内,一定不能在学历与才能之间画等号。
何况,基层纠纷也不那么复杂,司法本身更是不以知识为导向,而是一个明智判断导向的职业。在基层法院面对某些案件或人民法庭中,有无学历不是个问题。尤其在基层法院人民法庭,人们是要解决纠纷,而不是听法官说理的。比如离婚案件,法官讲得再有理,婚姻以感情为基础,他们不愿离,法官若依法判离,一方可能当场就喝农药。类似的事,通常转业军人反倒比大学毕业生更能有效应对。
没有律师,又何谈抗辩?上世纪90年代末的县城里还有律师,人民法庭里便几乎绝迹。在没有律师代理的人民法庭,我曾见到一位法官给双方当事人解释“法庭辩论”,“就是可以吵架,但不能骂人”。而世界各国,律师都是追逐高收入的城市动物。中国律师超过10%在北京,30%的律师集中在4个最大的城市,法学院毕业生不会到农村去。即便国家有补贴,法学院毕业生下到农村,我认为农民也未必受用。不是农民不关心法治,而是农民务实,只要事情能比较公道地解决就行。即便村里有律师服务站,咨询也要花钱。他会直接到法院要求立案,法官告诉他不能立案,但同时也要告诉他该怎么办,他其实就获得了免费的咨询。
文章作者


刘畅
发表文章102篇 获得4个推荐 粉丝498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