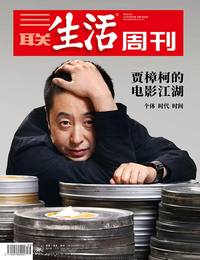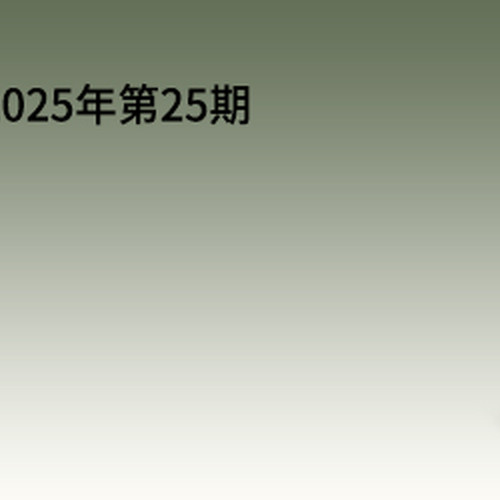乌菲兹美术馆:文艺复兴的灵魂居所
作者:薛芃
2018-09-26·阅读时长18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9439个字,产生1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2019年,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将迎来正式对公众开放的250周年庆典。作为全球最知名的美术馆之一,乌菲兹美术馆以美第奇家族的收藏为基础,从藏品、建筑到美术馆历史各个方面,无一不是今天回看意大利文艺复兴文明最丰富真实的样本。
也因为收藏有波提切利的《春》《维纳斯诞生》、拉斐尔的《圣母子》、米开朗基罗的《圣家族》、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卡拉瓦乔的《酒神巴库斯》等一大批世界名画,乌菲兹不但是各国游客佛罗伦萨之行的“打卡圣地”,也在艺术和历史研究的专业领域举足轻重。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游客数量的激增和公共服务管理的疏漏,乌菲兹的参观体验越来越不尽人意,逐渐陷入“啃老本”的诟病中。穿梭在美术馆里,仿佛掉进了一个时空黑洞,一方面,文艺复兴的魅力会将你拉回500年前全世界最辉煌的文明中,但另一方面,混乱的参观动线和老化的场馆设施也让人产生时代的错位感。近5年来,乌菲兹投入了大量成本改变这一现状,试图让这座古老的美术馆焕发新的生命力。
给名作搬新家
2018年7月,乌菲兹美术馆内,修整一新的35号厅正式向公众开放。这间位于美术馆西翼的展厅中,墙上只挂了三件作品,都是达·芬奇的。
由于达·芬奇的留世作品不多,馆藏的每一幅都被视为珍品。这三件作品起初都是为教堂而画的宗教题材作品,为了呈现出更好的观赏效果,工作人员将现在的墙壁涂成灰白色,并用刮铲抹出斑驳的肌理。作品上罩了一层美术馆专用玻璃,既为了安全,又因为玻璃的特殊材质,可以减少光的折射,让参观者无论站在哪个角度欣赏,都不会太反光。
其中一幅《博士来拜》画于1481年,尺幅很大,但没画完。在奥古斯丁修士的委托下,29岁的达·芬奇开始画这幅画,提前支付的报酬帮他缓解了经济上的拮据,可不到一年,他就动身去米兰了,留下这幅连底色都还没完成的“作品”。无奈,几年后,奥古斯丁修士又找来画家“利皮父子”中的儿子菲利皮诺·利皮(Filippino Lippi),画了一幅题材相同、构图相似的《博士来拜》,算是填上了达·芬奇挖的坑,这幅作品如今也收藏在乌菲兹美术馆。
现在看来,因为“未完成”,达·芬奇的这幅《博士来拜》反而变得更加有名,画面中人物多半还停留在草图的状态,研究者们常常通过这件作品来研究达·芬奇的作画过程。但修复者的眼光更敏锐些,千禧年之后的两次修复和维护中,工作人员都发现了这仅有的底色上并非全是达·芬奇真迹,亦有后世留下的痕迹,在经过清洗、材料修护和底板加固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样貌应该是几百年来最接近那个“未完成”状态的了。

与《博士来拜》共同放置在35号厅的是另两幅《圣经》题材绘画——《基督受洗》和《受胎告知》。这三件作品都是达·芬奇在20多岁的青年时代画的,后两幅都完整、细腻,但风格尚显稚嫩,与其成熟时期的绘画语言有不小差别。当这三件作品共处一室时,恰好勾勒出一个年轻、野心勃勃又才华横溢的大师蜕变的历程。
在接受本刊专访时,乌菲兹美术馆馆长埃克·施密特(Eike Schmidt)解释道:“展厅全新的安排和设计,客观上放缓了参观的节奏,给观众提供了更多思考的时间和空间,也让观众可以比较莱昂纳多·达·芬奇绘画风格的变化。将这一展厅放在整个美术馆来看,也是艺术史叙述方式中的一环,这个展厅之后,则以更多15世纪同时代佛罗伦萨艺术家的作品,展示了达·芬奇是如何开启对后世深远影响的。”
离35号厅不远的41号厅,也是才向公众开放不久的全新展厅,被称为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厅。两幅创作于1504至1505年的拉斐尔作品尺幅相当,并排悬在墙上,这是一对夫妇肖像画,画中人物是当时佛罗伦萨商人阿格诺罗·多尼(Agnolo Doni)和他的妻子玛德琳娜·斯特罗齐(Maddalena Strozzi)。文艺复兴时期,人物肖像画已经开始普及,除了教皇和王室,有一定资本积累的中产阶级也会邀请当时的艺术家为自己画肖像,既有纪念意义,又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以拉斐尔在世时的地位来看,拥有一幅拉斐尔为自己画的肖像应该是一件很荣耀的事,给多尼夫妇画像时,拉斐尔才20岁出头,还很年轻,画风却已经有成熟时期的影子了。画中两人眼神庄重地凝视着前方,虽是世俗中人,却不失典雅,在拉斐尔的作品中,神性和人性总能和谐地统一在人物身上。
多尼夫妇肖像画不止正面一面,背面是另外一组双联画,画的是古希腊神话故事——在大洪水后,普罗米修斯的儿子丢卡利翁和妻子碧拉是建造方舟的最后幸存者。这组双联画由拉斐尔工作室中一位名为“塞鲁米多大师”(Master of Serumido)的画家完成。为了让观众可以欣赏到正反两面,美术馆定制了一种玻璃立式展柜,将作品360度呈现在观众面前。
另一边,米开朗基罗的《圣家族》带着浓重的宗教色彩,更让人心生敬畏。“文艺复兴三杰”中,米开朗基罗最擅雕塑,他流传下来的绘画作品只有位于梵蒂冈的西斯廷礼拜堂系列壁画和这幅唯一的油画《圣家族》。在同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史家、建筑师乔尔乔·瓦萨里(Giogio Vasari)眼中,米开朗基罗是真正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英雄”,达·芬奇可不是。达·芬奇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比宇宙还广阔的好奇心,在瓦萨里看来正是一种缺陷,导致他很多作品和设计都无法完成,半途而废。而米开朗基罗那种专注笃定、似与神灵对话的状态和作品才是真正艺术的集大成者。
不同于一般矩形画面,《圣家族》是正圆形,打破了常规的视觉束缚,被称为Tondo。装饰复杂的金色边框足有近20厘米厚,也是米开朗基罗亲手雕刻制作的,无论放在哪里,《圣家族》都无疑是最显眼的那一个。巧合的是,这幅作品的主人也曾是多尼夫妇,他们向米开朗基罗定制这幅画,送给8岁的女儿作为生日礼物。
7年前,我第一次去乌菲兹美术馆参观时,《圣家族》还被簇拥在诸多小画中,在一面靠近转角的墙壁上,人来人往,驻足久了多少会有些不好意思。如今,在这个全新的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厅中,美术馆改变了从前“众星捧月”的展陈方式,减少同一空间的作品数量,馆长施密特解释道:“将最重要的作品放在视线中心是一种非常巴洛克的方式,我们将它用在博物馆的展陈设计上,这些作品就像磁铁一样把观众引入房间,停留更久。”
文章作者


薛芃
发表文章137篇 获得6个推荐 粉丝921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