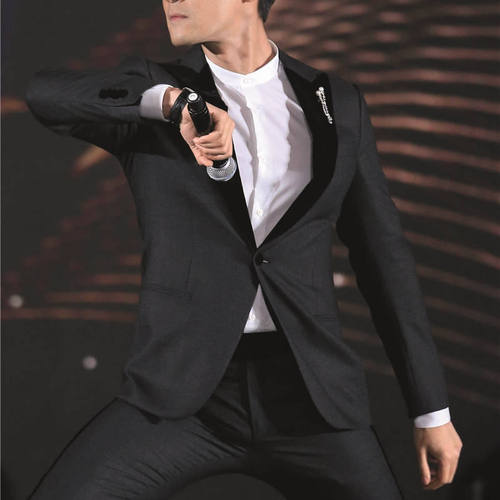北京最独特的面包房,精神病人给你做面包
作者:博客天下
2018-09-21·阅读时长13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6619个字,产生1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 胡宁
全北京有数不清的面包房,精美或粗糙的,高档或低端的,昂贵或平价的,但没有一家会比这一家更独特。
那些法棍、面包圈和桂皮卷的味道平淡无奇,特别之处在于面包师。面包全部出自6位精神障碍者之手。这些人在社会上可能被不礼貌地称为“疯子”,他们索性改造了贬义的称呼,给面包房取名为“CRAZY BAKE(疯狂面包)”。
不过,疯狂面包只有作坊,没有真正的门店。这些面包产自一道紧闭的红色的大铁门后面,大门两侧挂着牌子:北京市朝阳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在北京五环外的苏坟村这7亩土地上,有200个床位提供给各类精神障碍者,其中九成以上患有精神分裂症。一个70多平方米原本作为会议室的房间,被改造成了面包作坊。
6位面包师是从大量患者里选出的。他们的病情得到了较好控制,能实现基本社交。对他们来说,做面包是一种自愿参加的康复项目。
托管中心主任杨云和面包师们都希望能有更多机会走出铁门,走入人群。但是能走出去的时间和距离都太有限了。每周最多两次,大铁门会为面包打开那么一小会儿。装满面包的箱子被一位面包师抱出来。随后,他会坐上车,跟着工作人员去送货。此时,“疯狂面包”会打开一个小小的豁口。
“我们在家连饭都不做,还能做面包吗?”
张志东17年前被送到这里,在所有的面包师里,他是在这道铁门进出次数最多的一位。每周,他都有一两个下午把面包亲手递到顾客手中。每个面包都由他亲手写好标签和收货人,封入牛皮纸袋。
这件事他从2004年做起。
做面包之前,他还跟病友们一起种过菜,组过英语小组,上过电脑培训班。这些都是不同的“康复项目”。杨云认为,做面包是众多项目中康复效果最好的。

2012年5月11日,山东省邹平县精神卫生中心的病患者
最初提出做面包主意的,是两名外国志愿者伊万和娜塔莎。瑞典姑娘伊万嫁给了一个中国人,德国姑娘娜塔莎则是跟着来华工作的丈夫暂居中国。张志东刚认识她们时,这两个外国姑娘刚过30岁,如今她们分别都是拥有几个孩子的中年母亲。
伊万喜欢做主食面包。当初,她与娜塔莎向杨云提议,是否可以让精神障碍者来做面包。烤面包不像种菜那样为季节所限,所得利润可以用来贴补中心运行,也能让参与做面包的人增加一点收入。她们愿意负责寻找销售渠道——销路直到今天仍有赖于她们。面包主要在她们的朋友圈里推广。每周有一两次,面包师会到一些固定地点配送或贩卖。
能不能办成面包房,杨云心里也没底。第一步,她得找人去学做面包,再回来教病人。作为一家民办机构,这家中心除了每年能通过评比获得官方的奖励资金之外,没有财政拨款,也没有大额的社会捐赠。维持运转主要依靠病人每个月上缴的托管费。还总有人无法交齐。她没有余钱去雇外面专业的面包师。
最后,杨云想了个办法,把当时负责中心饮食的大师傅吕文海找来,请这位做惯了麻婆豆腐的厨师去跟伊万学做面包。她自己也一同去学。
效果比她预想的好太多。只看伊万示范了一次,吕师傅就都学会了。桂皮卷、麻花面包、面包圈、火锅面包,这是精神障碍者第一批要学做的四种面包。都是技术含量不高的。
但是,当杨云喊病人到一起开会商量做面包的事情,她听到最多的反问是:我们在家连饭都不做,还能做面包吗?
主持中心康复工作的王康乐解释,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有“始动性缺乏”的表现。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衰退,生活懒散,情感淡漠。平时如果不是护工督促,很多人连洗脸刷牙都保证不了。
张志东、史望安、余文睿等面包师被送到托管中心前,都生活在高度相似的房间里:脏衣服堆积如山,异味充斥着整个屋子,水槽里都是没刷的碗筷,厚厚的油垢凝结在厨具上,房间里没有能“下脚”的地方。从衣物来看,分不清主人过的是春还是冬,是日还是夜。张志东的房间还有他砸得满地的玻璃碎片。史望安在家里乱丢烟头,火星惹出过一场小乱子。余文睿的衣服穿得乱七八糟,很难想象她家中那张照片里纤细干净的主人公,会是她。
杨云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群体。他们“对自己没信心”,长期患病导致他们动手能力较差。她没别的办法,给全体病人开了三次“动员大会”,又单独做工作。张志东是最早表示愿意参加的人之一。
张志东上过大学,还做过大学教师,在外企工作过。人生最顺的时候,他拥有一家自己的公司。直到现在,接待外宾时,杨云有时还要依靠张志东为她翻译。
张志东慢慢总结出来抗病的心得:“我们有这毛病的人,千万别闲散。一闲散,就不是好事儿。”
最后,面包房终于踉踉跄跄地开起来了。所有的面包师都经过了病情的评估,也征得了家属的同意。
吕文海手把手地教这些人怎么揉面团,怎么把麻花的一侧搭上另一侧。他看一两次就能上手的东西,有的病人要学上整整两个月。有时候前一天刚做出些样子了,第二天就又回到原点,需要从头再教。连扫地拖地擦桌子这样的事,都需要一步步指示着完成。
第一炉成形的面包出来时,面包房所有人一起,眼巴巴地望着烤箱的指针,等着它归零的一刻。杨云永远记得那个味道,“特别好吃”,虽然看起来,那些面包绝对不是卖相最好的。
“犯病”时,她觉得电视节目都在针对她
面包房运行不到半年,赚来的钱就给中心买过两台洗衣机、三台空调,连电费都是从这笔钱里出的。
14年里,这笔钱还买过一台冰箱,200个塑料收纳箱,100把椅子,给全中心200个病人更换过好几轮床上用品。
吕文海每天看着他们做面包,跟杨云已经达成了默契。他们不指望自家的面包师能像外面的同行那样独当一面,“只要有进步就好”。卫生实在收拾不好,吕文海就来补缺。不断有新加入者做不好面包,为完成订单,吕文海干脆自己动手,“不能给顾客不好的东西”。
多年以来,面包师们来来往往,只有张志东、史望安和一名兼做会计的精神病人坚持了下来。退出者有的是因为疾病发作,有的是个人意愿不想参与。对此,杨云从不强求。

2014年12月31日,南京福园小区内的一家公益机构内,一位智力障碍青年和他绘画的房屋
作为面包房的“大管家”,吕文海深知不能用普通面包房的要求框定他们。就算是每个工作日上午3个小时左右的做面包时间,也一样有人突然中途消失,“连个招呼都不打”。“犯病”时,余文睿觉得电视节目都在针对她。
坚持下来的人身上,改变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杨云认为,他们的社交能力、处理个人事务的能力都在变好,“犯病”的次数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杨云有了个大胆的想法。她在离中心一公里左右的社区租了一套房子,让面包师和工作人员一起居住,尝试着在外面生活。
这个尝试持续了10年。
在大铁门外的这个住处,张志东能够做出可口的家常菜,余文睿品尝到了久违的“自由”,她终于重拾了一点点自己年轻时的影子。每逢出门,她都会换上漂亮的裙子,而不是穿着睡衣,每天在床的附近打转。
但是,这里并不是真正的“家”。一位同住的康复医生总是提醒这一点。他监督着他们一日三次、一粒都不能少地吃下形形色色的药丸,还要用手电筒照亮他们的口腔,检查他们服药。
“疯子”的标签没那么容易被摘掉。张志东还记得,有一年圣诞节,他们赶工生产出一批面包送到一家外企的年会上。那位外国老板激情澎湃地向自己的员工推荐“疯狂面包”。现场气氛热烈极了,张志东怀里的面包很快被抢购一空。
可是年会结束了,炫目的灯光关闭了。友好和热烈就像一场白日梦迅速破灭。刚刚围满了人的圆桌,只留下了一桌子的面包。
文章作者


博客天下
发表文章568篇 获得9个推荐 粉丝2417人
博闻雅识,非凡之客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