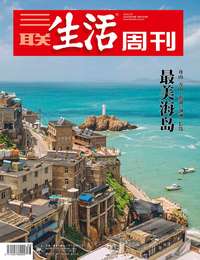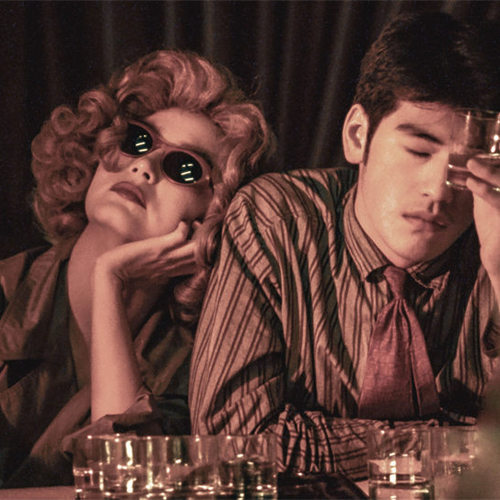单田芳的评书演义
作者:傅婷婷
2018-09-19·阅读时长9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4652个字,产生11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板凳头儿”
单田芳生前的工作习惯,是每天早上4点左右起床,工作到晚上8点,中午稍微休息会儿。女儿单慧莉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到了晚年,父亲会先把书做一些标记,不用的地方折上,然后把编好的东西打印出来,用笔勾勾画画,记在脑子里,用听众能理解的自己的语言来录书。虽然后来有了广播,不用在茶馆现场说书,但是父亲仍然会把要说的书都记在脑子里,这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了。再后来,有一些比较生疏的人名,父亲会写下来先熟悉一遍,说的时候就能记住了。”
在单田芳的儿子单瑞林眼中,父亲每天的生活也就是书:“比如他当年看‘三国’的时候,会在上面标注一些生僻字的字音和来源,在《新华字典》上查阅。每出一个新的版本,他都会买来看。”
单田芳原名单传忠,“田芳”是后来的艺名。他父亲单永魁是弹三弦儿的,母亲王香桂是说评书的,但他父亲一直希望“改换门庭”,根本不想让儿子说评书。单田芳上面三代都是说书人,他小时候帮助母亲做过很多记录,包括《隋唐演义》《大明英烈》《三侠五义》等等,但是自己从来没想过做个评书艺人。18岁那年,他父亲遭难被抓,母亲要离开父亲,单田芳不敢相信这件事,从沈阳跑到母亲正在说书的齐齐哈尔求证。当他得知母亲已经办好了离婚手续时,心灰意冷,回家途中,他决定挑起养家糊口的担子。
1954年冬天,他和一位走得很近的叔叔李庆海踏上了从沈阳去营口的列车,也踏上了说书之路。曲艺界的拜师收徒,在今天看来也许显得老派,但是民间艺术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延续下来的。在营口的一家饭店里,李庆海当众收徒,单田芳恭敬下跪:“师傅在上,受弟子一拜!”
后来单田芳在自传里回忆那段日子:“当时老师在台上说我在台下记录,每天到了晚上都是艺人们最愉快的时候。在演艺圈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大部分人都是阴阳颠倒,白天发困,晚上精神。到了晚上,师傅开始给我上课,教给我说评书的要领以及表演人物的技艺等等。”“由于我师傅没有文化,他需要参考,很多书就由我来读,他听,我们爷俩相辅相成,应该说在那段时间对我未来评书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55年,21岁的单田芳到了鞍山市曲艺团,认识了很多曲艺界的前辈,其中包括赵玉峰。赵玉峰后来和单田芳成为了师徒,他教会了单田芳手眼身法步、故事情节设计、诗词歌赋等等很多东西,也和单田芳切磋单家的看家书《明英烈》。
到鞍山不久,单田芳跟曲艺团说要登台说书,但是登台需要考试,单田芳靠《明英烈》中的段子摘得冠军,文化局的领导点评他时用了三个字:“准演员”。单田芳觉得自己一下子“从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变成了准演员”,心情很好。当时鞍山有7个茶社,每个茶社每天有早中晚三场,都有正式演员表演。于是,曲艺团开创了一个“板凳头儿”的先例:中场和晚场之间的空闲时间。单田芳开始在一个叫“前进茶社”的地方说“板凳头儿”。曲艺团让单田芳给大家讲《明英烈》,单田芳勤学苦练,用他自己的话说,“饺子是什么味儿都没吃出来”,“连做梦也在说书”。
1956年的大年初一,对单田芳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第一次登台,单田芳十分紧张,按照“板凳头儿”的安排,要说4段,每段30分钟。可是单田芳一口气说了两个多小时,把这事儿给忘了。茶社经理过来跟单田芳说:“单先生你跑到这儿来过书瘾来了,你看看都几点钟了?”单田芳恍然大悟,听众大笑。这次说书,让单田芳得到了在当时来说算是丰厚的报酬,也让他彻夜难眠,恨不得第二天马上接着说。他开始喜欢上了说书这件事儿。
单家擅长“长袍书”,但是对武侠书比较欠缺,于是单田芳开始跟师兄杨田荣学习。杨田荣给他讲《三侠五义》,单田芳回忆这段过程:“田荣兄每天抽出时间来到家里,不管刮风下雨,酷暑严寒,准时不误。哥俩面对面坐着,把房门一关,也就没有干扰了。”
文章作者


傅婷婷
发表文章33篇 获得26个推荐 粉丝199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