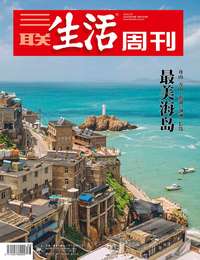澎湖列岛:古典价值,现代生活
作者:葛维樱
2018-09-19·阅读时长27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13992个字,产生23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对于我这样的外来者,从台北松山机场出发,低空飞行45分钟,是遍览岛屿的好时机。海平面上的风车自在地轮转,湛蓝海水下的澎湖主岛环抱住无波无澜的内海。外海则是台湾海峡最凶险的“黑水沟”。
我采访的时候,正好赶上冬夏交汇的时间点。在澎湖,鱼和天都只分寒暑。地处热带和亚热带交界的澎湖岛屿,官方数字至今统计为92个,民间常说97个。完全由内陆移民组成的汉族人口,在400年里,在澎湖岛屿上生活。我在跑遍了澎湖海域的东南西北最角落的地方,发现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部分,澎湖人和生活,却维持着一种古典的价值,自由的范式。作为离岛、偏乡,澎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步调,自有一种更新的节奏。
只有在澎湖,才可以活成这样。
寻找外婆的澎湖湾
脚下是茵茵绿草,我站在一片面向大海的高地之上。浅蓝色的天空,深蓝色的海水,空中间夹着一片极薄的白云。整整晒了一天的刺眼的白色阳光,从海上四面八方的射向这片高地,突然就开始偏黄了一点。先极目远眺,再收回视线,从海面往岸上看,岛屿的山崖都是绿色,在靠近底部的时候裸露出黑色的玄武岩,再往下,就是一片弯月形的海滩。
金黄色的沙滩之外,是到处黑色礁岩的海湾,人既不能走进海里,船也无法从海中靠岸。一丛巨大的仙人掌在高地边缘生长,针刺又长又硬,叶片比人的头还大。果然“没有椰林坠斜阳”。我想起在博物馆看到的那幅荷兰人对澎湖的想象图,是1604年荷兰人记忆中妈宫庙的样子。他们回国后口述给画家,妈宫庙周围是高高的五彩玻璃窗,像个大教堂,巨大的妈祖娘娘是丰腴的美人,两边是长着翅膀、执扇子的金童玉女,庙旁边还有巨大的椰子树,一看就知道是臆测。
我一直都在寻找“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的外婆的澎湖湾,可是澎湖人都告诉我,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地点。甚至连澎湖湾本身,原本只是本岛内海的一个概念,为了推广旅游,都变成了一个大概念了。然而无论概念怎么变,其中的质朴情感和简单印象却一直推动着我。夕阳西下迅速改变着海湾里的光影,我在西屿等待夕阳,切实地感到,也许“外婆的澎湖湾”就是这样的一处小小的不到两公里长度的自然港湾。

这个在地图上找到不到名字,村庄上方也只标明了“塔公塔婆”这两个石头信仰的标志物。宁静而荒凉,是澎湖西屿外安的一处高地,当地人骑着摩托车,从我面前因为减速,而扭转了起来,路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在澎湖乃至各个离岛,摩托车都是最简便的交通工具。这种摩托车很轻巧,我和台湾摄影师黄子明都没有像样的防晒措施,到这里才发现,男女老少,都用口罩、墨镜、薄手套、带面巾的帽子把自己罩得严严实实。防晒在岛上不是为了爱美。过度暴晒是澎湖的白内障患病率高于台湾所有的城市。
没想到,我向当地人打听这个地方的时候,澎湖人告诉我,这里是刚刚被选定的“世界最美海湾马拉松——澎湖湾”的起点。这场赛事即将在我离开后不久在澎湖举行。印象澎湖和现代澎湖,果然还是有很多重合之处。
对于一个现代化的澎湖,市区仅仅是指马公市区的两条最热闹的马路,仁爱路和民生路。澎湖的麦当劳2002年才开。从市区打车要按出租车公司的电话打过去预约,没有空跑的车在街上拉客。如果仅从街道和建筑上看,街道狭窄,大部分旧旧的建筑物至少有30年以上的历史。
蒋介石当年前往台湾第一晚下榻的“第一宾馆”仍在。澎湖县政府也在日据时代修建的二层楼里办公。“第一宾馆”面向的大海,就是马公市区最热闹的海岸“观音亭”,这里是市民娱乐休闲的海滨公园。虽然这里被打造成海洋公园,却也不是我心目中的澎湖湾,这里太城市化。周末来到观音亭海湾,有当地小学和中学生参与的古典乐器演出。本地歌手唱的歌曲,也是怀旧的90年代金曲风,对于我这样的过客倒是耳熟能详。
那个没名字的小海湾,最符合我的想象。唱起《外婆的澎湖湾》的潘安邦生长在五六十年代的澎湖,当时澎湖开始修建水泥的堤坝。祖孙两常常在港湾里看船,他和外婆当年他们讨论的是“是喜欢出航的船,还是返航的”,潘安邦说喜欢出航的船。“当时外婆没有说话,他应该是知道我会远走高飞了。”潘后来回忆过。
1979年为潘安邦写下《外婆的澎湖湾》的音乐人叶佳修曾回忆,曲成极为顺利,潘安邦用台北的公用电话,打给澎湖的外婆唱了这首歌。潘安邦自己的文章中写道:“我从小的一切游戏总和海分不开来。捉螃蟹、拾蚌壳、堆沙城,哇!真的,生长在海边的孩子相信是世上最幸福的。”
“虽然也有些混沌,但感觉中却是美好、明朗的。”潘安邦从小要帮外婆敷豆芽菜,清晨4点,扶着菜车,和拄拐杖的外婆一起去市场卖。“有着脚印两对半”的小路,对于台湾人情的简单动人的勾画,带着时代记忆,穿越了海峡,成为所有中国人几十年里最亲切自然的情感流露。“这一条路到我们家有很深的回忆,是那种,带着自己,走到各地,都不会忘记的回忆。”

现代澎湖的情感转换
潘安邦的外婆家就在澎湖古城墙脚下的眷村“笃行十村”。作为澎湖的特殊时代产物,眷村已经在十几年前就被清空改造了。眷村就位于澎湖仅存的古城门“顺承门”的脚下,中法战争后,清政府修建妈宫庙城墙,城墙以里就是今天澎湖古建筑的核心区,仍能看出古代城镇初具规模。城墙在1904年被日本拆除,并用城砖修筑了马公码头,倒是实用。至今退潮时前往码头,还能看到黑色的古墙石。
一进笃行十村,竟然听到的是夏天热辣的摇滚乐,年轻人将这里改造成了咖啡馆、小酒屋、冰果屋和杂货店,水泥墙面加上木格子门窗,竟然成了热闹的露天“星空电影院”,晚上7点半放港片《与龙共舞》。本来酷热天气下的一排排简陋的小平房,潘安邦和张雨生两个音乐人曾经的成长经历,在这里重合。真实中两家并不认识,但居然相隔只有几十米,在眷村里完全称得上邻居了。
“无言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取。”张雨生1966年出生在澎湖的大雨之中。现在张雨生曾经生长的小屋,挂着他儿时在眷村里和小伙伴们玩游戏的黑白照片,和全家六口围坐吃饭的质朴画面,1971年他家有了父亲亲手砌的厕所,改变了去眷村公厕的生活,这家人还是眷村里第一个买彩色电视机的家庭。概括了相邻的两间别人家的房舍,现在一起建成了简朴的张雨生故事馆。
作为现代台湾音乐的代表,张雨生的歌曲代表作有太多关于大海的意象和情感,这种思维属于现代,并不沉重,却自由、热情、坚定,“小时候,渴望壮硕的成熟,长大后,我有雪亮的天空”。
澎湖人的观念并不封闭落后。澎湖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社会学者王明辉告诉我,澎湖列岛地方生态特别有意思。“不是传统宗法社会、农业结构再到城镇化那么简单,而是经历了福建渔民移来,大航海时代的荷兰侵略者、马关条约被割让50年、近海渔业发展和衰落等等一系列演进的小岛。”近十几年的澎湖社会议题,是渔业改革,大量外劳涌入,新移民包括了大量外籍新娘,和老人们的生活问题。“澎湖是一个制度或者任何事物的实验场。让人兴奋。”澎湖还是台湾第一个发放老人年金的县。“经过历史的沉积,澎湖发展成了一个自更新力很强的社会。”
澎湖人给我举了个很近的例子。台湾对金马澎三地开放了赌博特许令,允许当地经过“公投”,设建博彩业。这个议案在马祖通过了,但是到了澎湖,第一次投票时,反对方以4000票的微弱优势胜出,第二次“公投”时,反对方和支持方票数竟然达到了9∶1。也就是说,除了地产和财团,澎湖老百姓一边倒地全部反对开设赌场,被提的最多的口号是“渔民的尊严”。
目前正在进行激烈的县长选战。大街小巷,村口的墙壁上,都是被选人的巨幅照片和口号。现在的澎湖列岛人数人口是9万多,正在进行的激烈选战中,有效选票是6万张,票差很小。另一个数据是,光绪年间澎湖的人口统计是6.754万人,日据时代最后一次统计是7.842万人。一个多世纪以来,澎湖人口出现了少见的稳定,出入几乎相抵。
只有休闲,没有观光。比起台湾很多主打海洋牌、小清新的热门岛,澎湖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生活。
文章作者


葛维樱
发表文章52篇 获得17个推荐 粉丝1022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