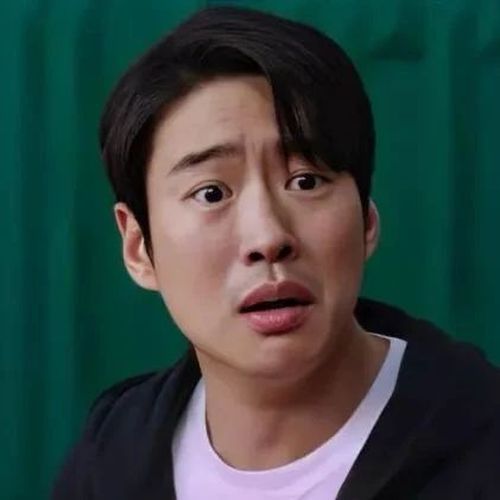一个温暖的雪夜
作者:朱伟
2018-08-13·阅读时长4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2474个字,产生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 / 朱 伟)
这好像是刘白羽作于50年代一篇记不得是散文还是小说的标题,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它刊登在下乡时在我们宿舍里流传的一本被翻得特别肮脏的《人民文学》里。这篇散文或者小说的情节与意境已经完全没有记忆,但“雪夜”给予一个温暖前置的标题却一直萦绕我心。在东北下乡时,这雪夜的温暖是烫得烙背的炕,是火炉里火烧柴禾像火车头一样喘息的轰隆声。此时双层窗玻璃上融化的冰霜像是泪痕,有雪片羽毛般飘到冰碴与水汽交融的玻璃上,便瘫软成微小的水珠,变成泪痕的一部分。这时想到的就是“夜幽静而多怀,风触楹而转响”。而东北这样静静的雪夜实际并不多,更多是趴在雪地中的小屋整个都被狂啸的风所颠簸,天上、地上、房上的雪肆虐成一片,雪涛烟浪。推门出去,风似利刃,坚硬的雪在风的速度中像是密集的子弹,根本分不清天地。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童年的雪是被绵绵厚厚地包裹着像蘑菇一样的小木屋,灯光是在蓝盈盈的雪上拉出很长灯影的橙黄。那温暖的记忆是,还钻在暖暖的被窝里,母亲就把凉凉的手伸进来。看看,母亲说,老天爷昨夜又做了好事。此时从被窝口探出一只眼睛,呵气里窗玻璃已被阳光耀得发亮。那时家里冷到所有毛巾都冻成两片折叠的薄薄的板,好像稍一折都会折断。母亲将衣服暖在夹层被子里,早上喝的粥装在竹壳热水瓶里,煤炉上水壶里袅袅飘着热气。这样的记忆,窗外的雪就是晶莹着的温润——让太阳照着是绵软的微微颤动的红,没阳光的地方,檐则被雪压成黑黑的凝重。童年的雪,“未若柳絮因风起”,轻盈中带有那种稚嫩的雪香,氤氲中没有气势,鲁迅所说“雨的精魂”的悲凉也体会不到。
早时感觉雪中的味道,都从梅那里去寻。也许就因为毛泽东那首《卜算子·咏梅》及“梅花喜欢漫天雪”一句的影响,揣摩味道在“雪意梅情”。“雪意梅情”中最有诗意当是“踏雪访梅”,也就是李渔所说,在感觉天有雪意之时,要带着“帐房”进山,三面封闭留一面以待赏雪观花。帐房中要备炉炭,为取暖也为温酒。这雪梅关系是,风送香来,香随寒至,雪助花妍,雪花怒放便成为雪艳冰魂。按文人雅士们的说法,最佳观梅之地在苏州邓尉,那里团团密密、重重叠叠到处梅花,称为“香雪海”。在梅花最深处有“吟香阁”,有《探梅歌》与李渔的诗意呼应;“雪花如玉重云障,一丝春向寒中酿。春信微茫何处寻,昨宵吹到梅梢上。”我感觉的意境中,这雪应该就飘舞于清亮夜色中,如在寒皎中的嬉戏。它们是漫天飘飞的精魂,召唤千树万树梅花开成刺目的漫山遍野,雪色岚光于是充溢悲怆气味。
文章作者


朱伟
发表文章122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1548人
《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