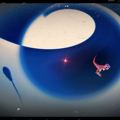王澍:向乡村学习
作者:贾冬婷
2017-03-16·阅读时长23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11564个字,产生5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重名之下
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建筑学院的一间教室里,王澍正在给他的新一届研究生评图。几个方案一字排开,都是有关如何将传统建造方式带入现代的。这一方向是王澍就任院长的这个建筑学院的特色,也是中国建筑学教育几十年来都悬而未决的大问题。显然,这对于这些刚刚升入“研一”的学生们来说很有挑战,大部分方案都遭到了王澍毫不留情的批驳。旁边的书桌上放着一瓶墨汁,几支毛笔,铺着几张棕黄色宣纸,纸上的字显然是刚写上去的,墨迹还未干。风风火火打理着各种事务的王澍妻子陆文宇告诉我,这是某个学生写的,也来自师承。这个习惯是王澍自大学时代就养成的,他几乎每天早晨都练一小时字,这能给即将开始的一天带来平静。
如今,平静对王澍来说尤为可贵。作为普利兹克奖历史上第二年轻、也是第一个非西方建筑师被加冕后,王澍获得了他未曾企望的名声。这一明星效应如此显著,以至于一直作为抵抗建筑师代表的王澍,成为各种商业和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要将他推向他所抵抗的那一面。
在此之前,王澍的生活是半隐居色彩的,甚至在获得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之后,很多建筑圈内的人都在打听他是谁。他自认是一个“业余”建筑师,和陆文宇共同创立的事务所也被命名为“业余建筑工作室”。“业余”一词在这里有对“专业”的反讽意味,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不为金钱和名声束缚、随心所欲的自由,“可以随时工作,随时不工作”。他的建造方式也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与技术相比,他更喜欢手艺;与建筑相比,他更愿意造房子;与建筑师相比,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个文人。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普利兹克奖选择王澍的原因,他们看重这种批判性的思维,尤其是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平庸建筑物被批量生产的中国。
普利兹克奖如何改变了他?王澍说,他的立场不会改变。他告诉我,几年前他和库哈斯在卢浮宫有一次公开对话,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库哈斯最后撂下一句话,要等着看。“你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名了。在这样的重名之下,我们看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当然有些事情已经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以前他的工作室每年只接一个项目,获奖后有成倍的客户找上门来,他坚持只增加一个,每年一共做两个。而且“普利兹克奖效应”也有它积极的一面,他逆潮流的建筑观有可能对政策造成影响,进而影响主流建筑活动。“我会选择真正可能影响社会的项目,尽管有些是‘吃力不讨好’的。比如每年的两个项目中,一定有一个在乡村。乡村现在占到了我工作的一半。”
2月的象山校区,已经有了一些春天的痕迹。早早萌芽的小草在未经硬质铺装的路边蔓延,有些就在教学楼破旧砖瓦铺就的墙面里滋生,让这里更有野生的味道。这个刚刚10年的校园是王澍获奖之前的代表作,就建在一座村庄里,保留了农业结构,道路也是根据农田的阡陌肌理确定的,建筑物顺应山势、模拟山形,看上去像是已经在这里很久了。有位朋友在看了之后问王澍,背后这座山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人自问自答:“这山是建筑完成之后才出现的。”
我们离开的时候,王澍的学生们正聚在建筑学院的中庭乐此不疲地玩一个游戏:一个人把这座楼从上到下所有的窗户一扇扇全打开,或者准确地说,它们既是窗,也是门,连起来又成了墙,总共有四五十扇。等那些厚重的木板全部被推开,风和光钻进楼里,室内室外连为一体,就像是打开了一个魔术箱。这个时候,他们一定也开启了和老师一样的信念:“我们身处一个由疯狂、视觉奇观、媒体明星、流行事物所引导的社会状态中,在这种发展的狂热里,伴随着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混合着由文化失忆症带来的惶恐和轻率,以及暴富导致的夸张空虚的骄傲。但是,我们的工作信念在于,我们相信存在着另一个平静的世界,它从来没有消失,只是暂时地隐匿。”
| 编辑提示:在以下的付费内容里,您将看到王澍的两个最新项目,富阳山馆和文村的设计理念、开展过程,这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大师,中央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建筑学院院长,来看他是怎样来解决新与旧的错位,给农民造房子的。——“农村小洋楼顶天100万元。现在王澍设计的房子,听说有人出到800万元了。”
文章作者


贾冬婷
发表文章79篇 获得5个推荐 粉丝1344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助理、三联人文城市奖总策划。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