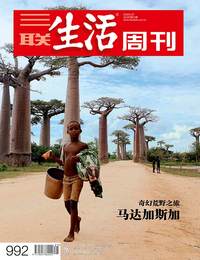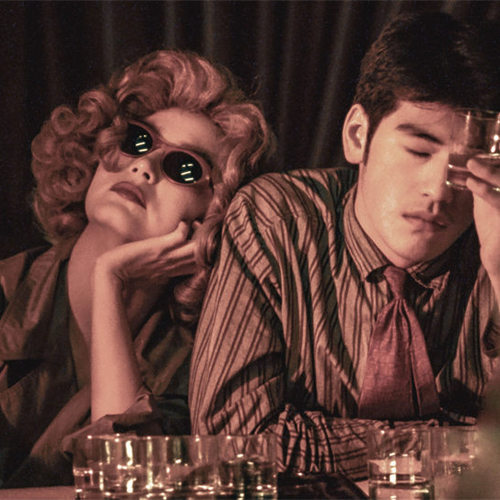蒋勋:讲给“大家”听的人
作者:傅婷婷
2018-06-25·阅读时长9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4767个字,产生9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采访蒋勋前,还没看见他,已经听到他熟悉的声音。现在的音频付费节目中,蒋勋的音频课有广泛的传播度。对于受众来说,他扮演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启蒙者的角色,用浅白的语言给大家讲艺术史,讲《红楼梦》,也用这样的方式去写“孤独”、写“品位”。
蒋勋很愿意以“启蒙者”的身份与大众沟通。早在1993年,蒋勋就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全彩印刷,成为很多青少年的美术史入门读物。他回忆:“当年,老董(董秀玉)帮我出这本书,希望我写一本帮小朋友讲美术史的书,那时我就设定了给15岁的孩子讲,这个当然很困难,美术史这么多复杂的专业名词,怎么给15岁的孩子讲?我那时候有一个朋友的女儿,是我的干女儿,她刚好15岁,读中学,我写一段就念给她听,她没兴趣我就改,改到她每次听了就有兴趣。所以我还是有信心,再难的东西、再复杂高深的文明都可以用简单的方法讲给孩子听。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心愿,这个文化要传递下去,大概也必须要用这样的做法。最后,我们没有用‘孩子’而用‘大家’,因为老董觉得我们都是孩子,很多人对美术史都不了解。于是书名就成了《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
在当下语境里,“大家”有三种含义:世家望族,著名的专家,众人。而蒋勋,似乎一直在这几个身份中寻找平衡,给“大家”提供一种见解。他开始做美学内容普及的时候,互联网还没有普及,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还很单一。互联网普及后,一些慕名去听蒋勋的课程或者看他书的人,开始表达自己对浅显阅读的不满足。而关于蒋勋的争议,是因为有学界的学者对他所传递的知识部分内容的不准确性提出意见。事实上,在他身上一直叠加了学界和大众两个不同的评价标准。
而在蒋勋自己的讲述里,他对“知识”“沟通”的理解形成于法国留学期间。1972到1976年,蒋勋在法国留学期间打工时,曾在卢浮宫担任讲解员。在巴黎,他经历了1968年“五月风暴”的余震,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感觉到了打破阶层进行“沟通”的重要性。蒋勋说:“1968年,法国人也在思考一个问题,知识是不是应该被少部分人垄断?比如法语讲vous跟tu,vous是‘阁下’如何如何,如果我用‘阁下’来称呼你,后面的动词都会变,很多的敬语。可是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学生对一个学者用了vous以后,后面就放弃了自我思考的很多可能;如果用tu,是比较平等的。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其实也说,我们能不能把一些人与人之间故意造成的隔阂拿掉,用比较自在的方式沟通。比如,原来上课有一个高高在上的讲台,老师坐在讲台上,学生在底下,这样的关系是以上对下的,同时也是对立的。他们就想,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圆形的教室?老师跟学生是在圆形当中的一圈,比较平等,没有主从的问题。”
在巴黎大学的读书经历,一方面影响了蒋勋跟大众沟通的方式,另一方面也让他对绘画有了新的认识,正是这种认识,影响了他后来讲解美术史的方式。蒋勋记得上课时老师讲印象派:“印象派画的女人是什么样子?拿一个小洋伞,戴着帽子,脸上有面纱,很细的腰,皮肤好白好白。皮肤白,是印象派的画里面的贵妇人、资产阶级女人的一种美。为了保护这个‘白’,所以用面纱,用小洋伞。”而在70年代的巴黎,女人对“美”的概念与印象派绘画有了区别。“只要有太阳,很多女人脱光了躺在塞纳河旁晒成bronzé,就是古铜色,那才是美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从经济史来看,在印象派的时代,要打小洋伞保护皮肤的白,因为劳动的女人都是黑的,所以是阶级之间的区别。而现在古铜色变成美,因为要买很贵的飞机票,才能飞到曼谷或者巴厘岛把皮肤晒得黑黑的。”蒋勋说,“所以美的背后其实有经济学的东西。美是有符号的,比如为什么唐俑中的女人都是胖胖的?她的低胸服装为什么跟宋朝的纤弱不一样?其实跟政治史、经济史都有关系。这个是符号,符号背后有很多的文化含义可以解读,其实我后来一直在用这个东西。”
6月9日,蒋勋在上海举办他在大陆的首次艺术展览,名为“天地有大美——蒋勋的艺术人生”。展出近50件作品,包括绘画、手稿、影像和声音。发布会结束后,蒋勋给大家做导览,讲解中,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不喜欢展览。在工作室,你跟一张纸或者一块画布发生长时间的恋爱关系。展览很像婚礼,婚礼像是一个仪式表演给大家看,说我们两个要在一起。所以我告诉自己,够了,一次展览够了,一次婚礼够了,还是回去好好恋爱。”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你提到《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最初是“设定给15岁的孩子讲,当然很困难”,难在哪里?
蒋勋:我想每一个专业都有它专业的术语。这个东西其实不是难,而是我们用惯术语以后,外行的人就不太容易懂。比如说美术史,我讲“春蚕吐丝”,这是讲晋朝顾恺之的画里的某一种线条。大家可能不知道“春蚕吐丝”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可是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去解释这四个字,一个春天的蚕,它吐出来那根细丝的连绵不断。唐朝的吴道子画人像,叫“吴带当风”,是说线条有衣带被风吹起来时飘荡的感觉,所以线条有变化,有顿挫和转折,就跟“春蚕吐丝”那个连绵不断的线不一样。我觉得可以换一个方法来告诉孩子:你穿了一件衣服,在风很大的时候走到山上去,衣服被风吹起来,你也可以观察到那个衣服本身就有一个线条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这些专业问题其实是容易克服的。难在哪里?难在有没有心让别人懂。如果你觉得我的东西就是高深的,别人不可能懂,它就越来越难。所以我相信美是一个沟通的方式,如果有心愿,就一定可以沟通。
文章作者


傅婷婷
发表文章33篇 获得15个推荐 粉丝199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