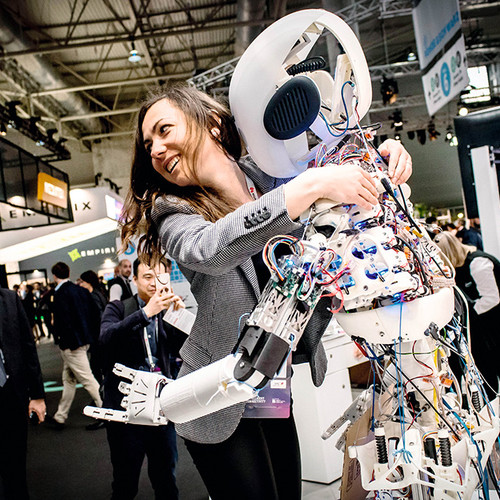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一场未竟的纪念
作者:刘畅
2018-05-07·阅读时长20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10037个字,产生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英雄归来
2018年3月28日上午,曹家麟在家里关注地观看迎接第五批在韩国的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的电视直播。20具装着烈士遗骸的棺椁披上国旗,随着民政部副部长高声呼喊,“祖国接你们回家”,中方人员向遗骸三鞠躬,由解放军礼兵护送入中国而来的运输机。降落辽宁沈阳桃仙机场后,志愿军烈士遗骸被迎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进入中国领空后,两架歼-11B战机划空而过,飞行员在机上报告,“我部飞机奉命为你护航”,音容清晰可辨。半个多月过去,电视里出现的这个画面,仍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冲击着他的回忆。
跑!60多年前在朝鲜战场,只要听到战机的轰鸣,这是曹家麟唯一的反应。天空是敌人的,敌机昼夜不停地轰炸,他无法想象在云层之上俯视陆地的感受,他们只能在密林和防空洞间穿梭,领略饥饿、慌张与痛苦。后勤被破坏,他每日的口粮只有六两,没有盐,吃不到副食,他患上夜盲症。他的胳膊上留着飞机带给他的印记:一个清晨,他从防空洞里出来,下山洗脸,忽然听到轰鸣的声音,敌机已俯冲下来,他被战友拽着往山上跑,胳膊一疼,便发现被敌机机关炮的弹片“咬”了一口。
“朝鲜的妇女、老人抬着我们的伤员,在雨里和火里奔跑。雨大了,他们脱下衣服给伤员挡雨,遭到敌人的轰炸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扑在伤员身上。”因修坑道时曾被滚落的巨石砸中,曹家麟常年头痛,久久失眠。“我多想再看到他们或他们的后代,多想去吊唁遗留在战场的战友。”
他把自己的晚年交给了客死他乡的逝者,遗留在韩国的志愿军烈士遗骸是他生活的重心。“从第一批烈士遗骸归国到现在的视频和文字材料,我都有。”82岁的曹家麟留着利落的短发,说起话来中气十足,似乎仍枕戈待旦。一台笔记本电脑、两台台式机、专业扫描仪、五六块1TB的硬盘,他的装备库里,载满志愿军烈士的资料。电脑的通信软件里,志愿军老兵和志愿者的消息不断。遇人来访,他在笔记本和台式机之间来来回回,想到一个材料,便从台式机的“资料库”里拷给人看。而五年来,在家里观看烈士遗骸归国的直播,已成为他的习惯。

跨过“三八线”
接回烈士遗骸的那天,89岁的张泽石却没看直播,近年来他已不愿再与朝鲜战争的文章、影像有任何接触。“我不想再做噩梦!那场战争给我们这些承受磨难的老人,留下的伤痛太深。众多战友已离我故去,我们的心理变得很脆弱。”在京郊石景山附近的家中,张泽石在追忆往事时,总带着岁月隔阂下无奈的苦笑。他反复地念诵《陇西行》里的诗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像大多数志愿军老兵一样,张泽石和曹家麟两位老人80多年来素未谋面,但他们却曾因朝鲜战争聚到一起,又被冲向迥异的人生轨迹,直至晚年,那场战争始终或明或暗地萦绕在他们心头。
张泽石是当年志愿军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张泽石1946年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次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便离开清华园,回到成都老家投入发动群众的地下斗争,迎接解放。“我曾在四川大学搞‘学运’,在川西坝子上发动贫雇农参加游击队。”1950年春节,张泽石正式穿上军装,他感到骄傲的同时,渴望家乡政权巩固后,便复员回清华上学。
1951年3月,他所在第三兵团第60军180师538团从成都出发,直到在河北整训时,他方得知,马上要进入朝鲜战场。而他不知道的是,他上来便要面对最残酷的第五次战役。

第五次战役在第四次战役挫败下匆忙展开。朝鲜战争的前三次战役中,中朝军队把“联合国军”赶到“三八线”以南,占领了美军的补给基地仁川港和汉城(今首尔)。但“联合国军”在第四次战役期间,发现了志愿军补给的问题。他们就此发明了“磁性战术”,与志愿军僵持,不给中国军队补给时间,同时在局部依靠火力优势,密集突击,等轰炸停止便立即反扑。第四次战役后,中朝军队终因实力悬殊,全线重又撤回“三八线”以北。
文章作者


刘畅
发表文章102篇 获得14个推荐 粉丝498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