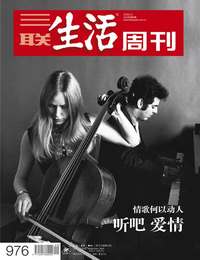狗从哪里来?
作者:刘周岩
2018-03-01·阅读时长20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10263个字,产生15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改变历史的一刻
一小群衣不蔽体的野蛮人正在穿越茂密的草丛。
这是远古时代,人类还远未主宰地球。这个部落的人的生存环境极为艰苦,无时无刻不处于对周遭野兽的恐惧中,树林、灌木丛中都隐藏着不可知的危险。他们已经拥有了原始的弓、箭,身体形状、大小和今天的我们已经相仿,但动作与眼神却更接近于动物。
刚刚结束的一场对老虎的围猎中,这个部落又损失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猎人。生存条件的逐渐恶化让他们决定迁往平原上的另一片区域。迁徙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原来的领地,每当夜幕降临,部落人围着营火入眠,在他们周围总徘徊着一种形迹可疑却又多少不同于其他野兽的动物——狼。它们或许是被烤肉的味道吸引,或许是为了什么目的,没人把它们放在心上。到了新营地,部落人恍然发现,没有狼在周围徘徊并在有危险出现时狂吠,自己终夜不得安眠。
经历了许多个疲惫不堪的夜晚之后,他们忽然在某天又听到了那熟悉的嚎叫声,一头狼出现在了不远处。这群野蛮人有点不知所措了。以往,每当狼靠得太近,他们就用石块将它赶走,这一次他们拿不准是否还要这么做。年轻的部落首领站了起来,许久之后,他做出了一个让同伴感到惊讶的举动——他从刚捕获的猎物上割下了一块肉,扔在了狼的身边。这个时刻,永远地改变了狼,也永远地改变了人类。
以上的叙述,是对狗诞生时刻的一种想象。原始人类意识到狼的守卫功能而主动喂食并驯化了狼,这是现代动物行为学创始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奥地利人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对狼如何变成狗这个重大问题的解释,他于1949年所著的《狗的家世》(So kam der Mensch auf den Hund)代表了那个年代对狗的最新理解。某种意义上,当人类第一次和狼主动接触时,狗就产生了。尽管事实上它们还需要许多代的演化,直到变为一种性情和外貌都不同于祖先的生物,再开始和我们长达数万年的伙伴关系。
狗的诞生关系重大。狗是最早和人类熟悉起来的动物,是公认的被人类驯化的第一种动物,远早于其他家畜,更是唯一一种在农业出现之前就被人类驯化的动物。狗也是所有动物中和我们的关系最密切的。这种密切关系是双向的。对狗而言,它们根本就是因人类而生,如果没有人,也不会有狗,是人驯化狼而创造了狗;对我们而言,狗在生活里扮演着最丰富的角色。人类驯化多数动物主要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肉食资源,对狗则完全不同。驯化之初狗被用于守卫、狩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狗又被用于运输、放牧、搜救、导盲……能在如此多样的领域助益于人类的动物,仅有狗一种。
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帕特·西普曼(Pat Shipman)于2017年5月出版的新书《入侵者》(The Invaders)中,她甚至提出了一个富有争议的假说:从非洲走出的智人正是因为驯化了狼,靠着人和狗的组合大大提升了狩猎能力,继而灭绝了原本生活在欧亚大陆的尼安德特人,现代人类才就此产生。对狗起源的探索,正是对我们自己的文明之路的探索。
今天已没有狗诞生时刻的直接见证者,但历史留下了痕迹。众多间接的线索中储存了我们的祖先和狗的祖先的“遗言”,他们之间的故事就蕴含其中。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们正在破解这些“遗言”,尝试揭示出早期人类与狗之间的互动究竟是怎样一幅图景。

殷墟狗讲述的故事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的副研究员李志鹏博士带我来到了动物考古整理室。他从库房中取出了一箱古代狗骨标本,不同部位的骨骼被分门别类放置在保存袋中。“这副骨骼相当完整,颅骨、颌骨、肋骨、肢骨、脊椎等都很全,还有阴茎骨,由此知道这是一只公狗。”李志鹏一边介绍,一边按照大体方位摆出了大部分的骨骼。这副无言的骨架静静地凝视着我们,它仿佛有许多事情要诉说。
“这是在殷墟中出土的,距今有3000多年历史。”李志鹏说。这只狗来头不小。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是商朝晚期都城,20世纪初被发现并在李济等考古学家的主持下开始发掘。殷墟证实了“夏商周”中商代的确凿存在,出土了大量甲骨文片和后(司)母戊鼎等珍贵文物,被视作近代以来中国考古的最大发现。
这具狗骨呈现的形态特征已经与现生狗无异,说明商代人已经拥有了和今天一样的狗,不过只通过骨骼还很难将其确定到某个具体的品种。李志鹏介绍,除了狗骨本身,发现狗骨的位置也至关重要,如果是在“灰坑”(考古学中对遗址中生活垃圾堆的称呼)里发现的零散狗骨,说明是人类食用狗肉后的残留,而眼前这只完整的狗骨则不同,“这只狗是在人类墓葬的腰坑里发现的,墓葬中随葬狗牲是商文化中常见的葬俗,尤其是晚商时期”。所谓“腰坑”,是墓葬中人的腰部下面挖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坑,在这个最贴近逝者的位置特意放一只狗随葬,充分说明了商人与狗不同寻常的关系。

我们的先人为什么要让狗陪葬?“狗在晚商时期实际上扮演了护卫、田猎助手等角色,商人非常重视狗。商人的宗教信仰让他们相信不仅人死后有灵,动物也是如此,狗可能是被用来继续在死后的世界里守卫主人。”李志鹏提到一个关键区别,商人墓葬里也有猪、牛、羊等动物,但通常只是放一条腿,而狗都是完整的,这说明随葬的猪、牛、羊可能只是作为“肉食”,狗却需要发挥其功能,所以保留了完整的躯体。
墓葬中狗的年龄与数量也大有玄机,暗示着一个可能自商代就存在的狗的饲养与贩卖的产业。根据李志鹏对殷墟中孝民屯遗址84具狗的鉴定,1岁以下个体为54具,占三分之二比例,可见商人有意选择幼年个体用作随葬狗牲。已经成年的狗在家庭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杀掉随葬未免浪费、成本太高。不过2个月以下没有断奶的狗商人也是不杀的,体现了一种怜惜之情。商代用于殉葬的狗数量非常大,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家家正好有幼狗。“我推测,商代晚期殉犬的盛行可能导致专门的养狗业的产生。也就是说需要狗牲殉葬的时候,家中没有幼狗或自己不养狗的家庭就从专门的养狗户那里购买幼狗。”李志鹏说。殷墟中出土的甲骨文也提到商王征贡犬时一次多达上百只,间接印证了商朝时规模化养犬业的存在是有可能的。
这具殷墟中的狗骨讲述了不少它和我们的先人之间的故事。看来在中华文明刚起步的阶段,狗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不过,狗的起源显然要比距今3000余年的商代还要早得多。在人类历史更早的阶段,我们与狗之间的故事是如何发生的?考古学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文章作者


刘周岩
发表文章102篇 获得29个推荐 粉丝904人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