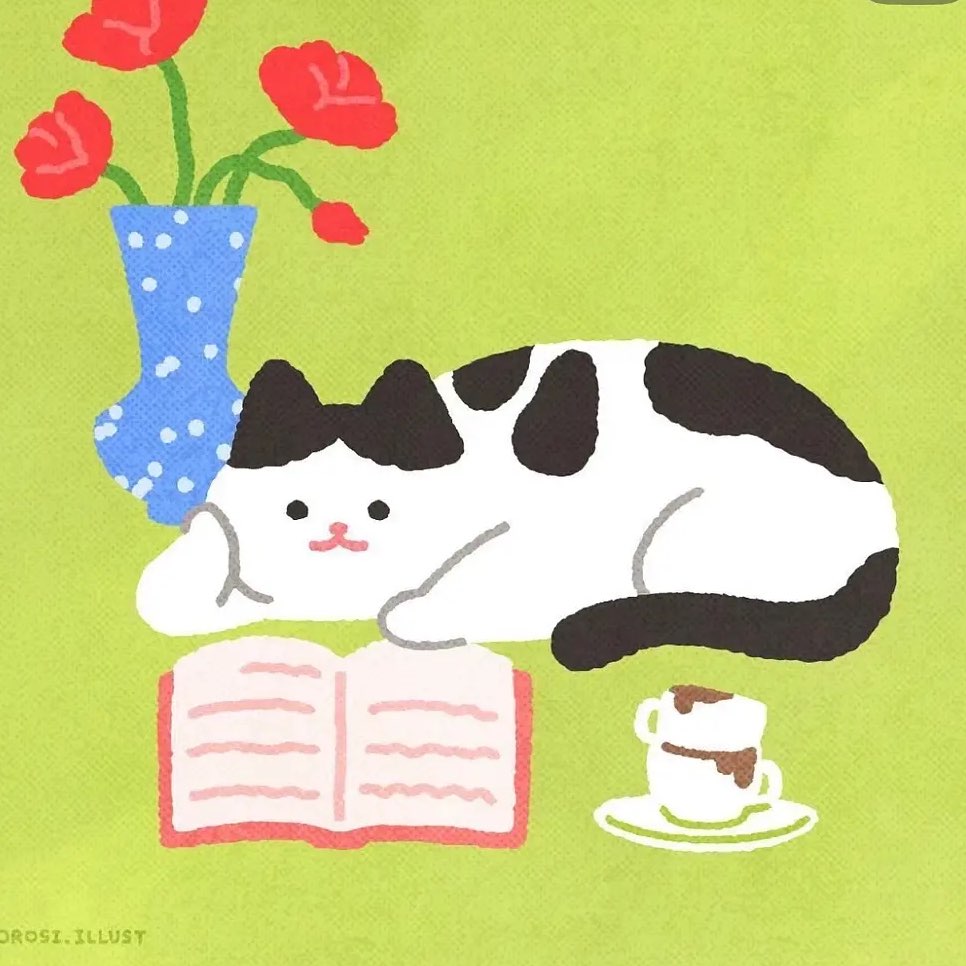鲁迅之疑 “国民性”的检讨再检讨
作者:舒可文
2018-02-25·阅读时长18分钟
3759人看过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9005个字,产生113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文 / 舒可文)

( 1928 年3 月16 日,鲁迅在上海景云里寓所 )
“中国问题现在已变得远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内部问题了,可以说,它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未来的20世纪,它将是一个比现在更为紧迫的问题。”
1892年,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为他的《中国人的特性》在英美再版写这个绪论时,尽管已经预设了长远的100年,还是没料到预想的还不够远。100年后的又一个90年代里,像是返老还童,这本书至少有4个版本在中国出版,英文版至少在2002年又一次再版。新一轮对“中国问题”的检讨被重新启动,当然不是来自于这么一本很不严谨的随笔集。就像“五四”前后的国民性讨论由自省到反省,转而批判,继而“自蔑”,终是有一个现实处境和一种理想来打底的。
于我而言,这种检讨从有所共鸣的那一刻,就伴随着几近自我否定的刺痛。百年更变,悠悠岁月,当年时贤们的理想与今日的理想有哪些区别?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处境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或者感受自我否定的刺痛或者沦为阿Q的纠结之间,是否有一条自我和解并与世界和解的道理?正是在这种纠结中读到的鲁迅,便有异于之前读到的教科书导读了。从鲁迅去世前的“一个也不宽恕”,回溯到他从文之初的《破恶声论》、《文化偏至论》,鲁迅的斗士形象方显示出另一种面貌,其间30年横眉冷对劣质的“国民性”,竟迂回错综地起自那样一种对自我和解的期望。
文章作者


舒可文
发表文章1篇 获得2个推荐 粉丝127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