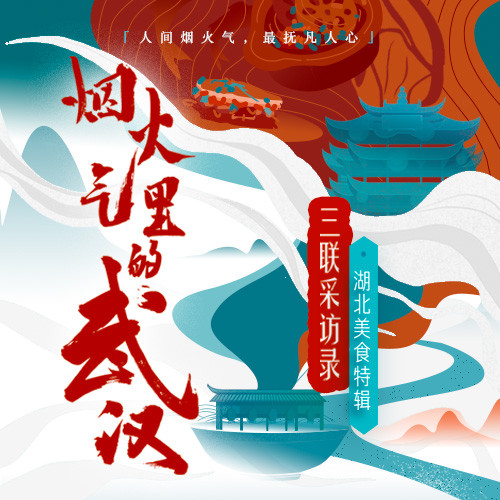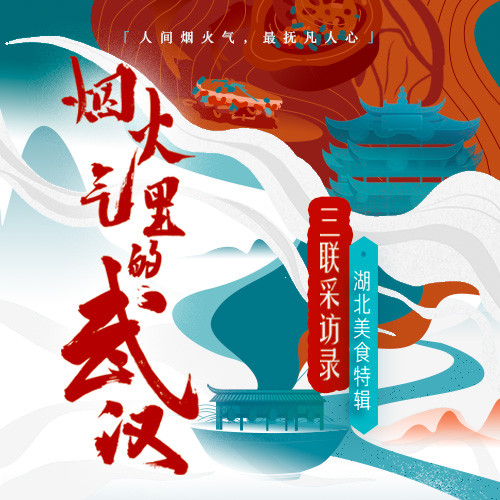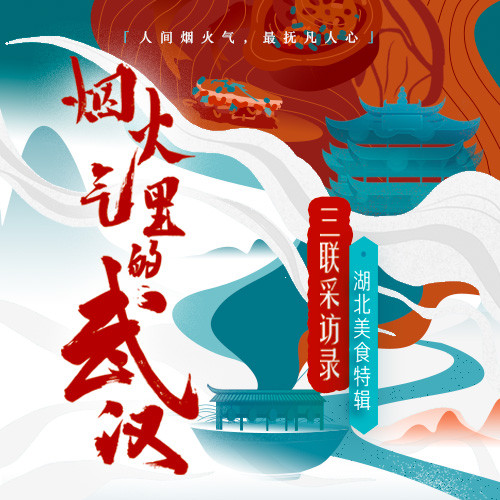文艺墨尔本 ,摩登悉尼
作者:黑麦
2018-02-14·阅读时长26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13389个字,产生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大概是“猫本”这个名字太过贴切了,墨尔本这座精致的澳大利亚小城似乎真的变成了一只“慵懒的猫”,安静地趴在维州的南端,望着世界,人们在这里也展露出一只猫本来的面目。“雪梨”是悉尼的广东叫法,几十年前来这里的香港人用甜爽的水果命名这座城市,确也形象,这果子散发着香气,温甜且多水,作为一个充满移民的城市,这颗“梨”竟也可以搭配各种料理。

这个世界有不少“互掐”的城市和地区,像北京和上海,又如美国的东西两岸、英国的南北,再比如日本的大阪和东京,墨尔本和悉尼也是一对。每当听说有人从悉尼来,墨尔本人就讲“要下雨了”,可事实情况是墨尔本的天气才是阴晴不定。当然,闭口不谈城市,相安无事。记得我第一次和墨尔本人讲起我曾在悉尼留学的经历时,那人的第一反应是:“你是不是觉得墨尔本很适合生活?”如果这时还不知收敛地夸赞悉尼,那人就会噘嘴,试图告诉我“真不会聊天”。
当然,这是一场无关胜负,又毫无恶意的争执。悉尼强调的是摩登和富有,而墨尔本讲究精致和安逸。从这些可以瞥见这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公民群体对于一个城市的喜爱和依赖,既然习惯了某地的生活,就会遵循下去。只是那个夹在两城中的首府堪培拉,成为这场“争执”中最大的产物,也成为一个很容易被人遗忘的首都城市。
走近一家餐厅,同样可以看出两个城市的区别来,当一盘菜被端上桌时,悉尼这边多半会强调自己的老师傅、正宗,而墨尔本则会耐心为你解释它的融合和创意。作为食客,大可不必为这两种“食物认知”而匆忙站队,从口味上讲,你甚至很难讲出哪种味道更佳,只是,作为两种烹饪信仰,一种捍卫了传统的文化调子,而另一种则延续了它的生命。
多年前的小故事
2000年,澳大利亚还很年轻,悉尼歌剧院也只有27岁,那年,我和一群留学生花花绿绿地走上飞机,揣测起悉尼的模样。在飞机上俯瞰城市是一片低矮的红顶房屋,走下飞机还是相似的感觉,那时候听老一拨的留学生常说“村儿里的事”,才觉得好像是这么回事。
我的第一个房东来自广东,会做美味的煲汤,房东钟太太听说我从北京来,特意“煲”了锅鸡蛋西红柿汤,我喝了一口觉得味道奇怪,她用蹩脚的国语解释,自己先把鸡蛋煎熟,然后加入各种海鲜干货和鲜番茄,煲了40分钟呢。在那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那锅汤对于一个老移民来说,已是不易。那会儿我还不知道,和我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还有三个广东兄弟,他们是当地“茗记”海鲜大酒楼的掌勺厨师,这个餐厅至今还在。我曾当着他们的面把一锅白粥煮成米饭,他们不懂我讲的国语,只是端起锅,轻轻松松给我炒了盘美味的蔬菜。
那会儿还没有“早午餐”一说。早餐通常是“Weet-Bix”公司出产的各种形状且口味相似的谷物麦片,我倒上一杯牛奶,和房东5岁的女儿坐在一张台子上,把她看的《天线宝宝》调成英文配音的《七龙珠》,顺便看着房东为我们“精心”准备午餐。她把澳大利亚特产“能多益”巧克力酱涂抹在一片面包上,然后盖上另一片面包,装入食品袋,午餐就做成了,我和她的女儿分别得到两块和一块,塞进书包。
澳大利亚人的午餐的确简单,因为“少食多餐”贯彻得好,上午和下午的茶歇(Tea Break/Coffe Break)足以补充体能。打开同学房东制作的三明治通常如此,大多是一些蔬菜和火腿,来自欧洲的房东偶尔塞进一片车打(Cheddar)奶酪和腌黄瓜,偶尔还能碰到房东在切片面包里涂抹了“Vegemite”(发酵的蔬菜酱,非常有营养,别称澳洲的臭豆腐),又一次有个男孩的天津房东给他的午饭盒里带来两个包子,那天午休,几个中国留学生眼睁睁地看他吃完,表现得很羡慕。不多久,当我们熟悉了澳大利亚之后,几乎一出家门就把房东做的午餐甩进垃圾桶,我通常会在上火车前,把它塞进房东女儿的书包。街边的炸鱼店很快就变成了我们的食堂,撒着鸡盐(Chicken Salt)的炸鸡块、煎鳕鱼汉堡,这些在那个时期的中国不常见的街头快餐,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
很快,我在安萨桥(Anzac Bridge)附近的一家海鲜餐厅找到了工作,那是一家装修雅致的餐厅,门面简单,摆盘精美,服务生穿着干净的白衬衣,总是面带微笑,餐厅的合伙人之一是这里的总厨,他留着一点小胡子,讲话的时候很温和。我第一次知道了澳大利亚还真有“美食”,印象中那餐厅出售大量的鱼菲力、烤龙虾、生蚝、小牛肉,偶尔还会有人点上一只价格不菲的黄油煎比目鱼。上菜前,有个人会盯着盘子看几秒,似乎在做最后的检查,等他点头默许后,才会有服务生把菜端上桌子。
我从洗碗的工作混到了沙拉台,这让我彻底知道了一个高级料理厨房的辛苦,厨师需要像一群沙丁鱼一样在总厨的领导下完成各自的工作,每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后,厨房里所有人成了清洁工,需要把厨房彻底清洗一遍才能回家。在繁忙的夏季,我们会工作到夜里两点,那时候,我会在随身听里放上一张“碎瓜”(Smashing Pumpkins)唱片,端着一杯便利店的机打咖啡,一个人站在市区中心,看着醉酒的人等夜班车。我提出辞职后,老板用一份香橙煨羊肉(Lamb Stew with Orange)贿赂了我,让我在那里多留了两个星期。
那会儿澳大利亚还效仿美国,后院烧烤着实流行了一阵。我有个大学同学喜欢美国金属摇滚,他的爱好就是烧烤,我吃过最薄的牛排也是在他家。那时候总能见到拿着VB啤酒的年轻人聚在烤炉边聊起澳式橄榄球,他们口中的悉尼队是天鹅(队徽),墨尔本是魔鬼(另一个队徽),我总觉得这个象征搞反了,也可能越是缺少什么就越需要膜拜什么。几年后,在一个墨尔本朋友家吃饭,无意中提起“Rugby”(橄榄球),急忙被纠正,“我们这里叫Footy”,他给我拿了一瓶VB,喝起来也没有当年苦了。
我的另一个房东许太太来自福建,她在查斯伍徳(Chatwood)有几套房子,那时,她只给自己和家里人留了几间,其余全部出租给了留学生。一方面为了收入,但是让她洋洋得意的是这三十几口人的伙食,全部出自她一人,并且自得其乐,游刃有余。下午6点,是她的送餐时间,她挨户送去刚刚做好的主食和几个菜,也偶尔点火现炒或是做汤,凤梨酥和甜点也是她的强项。某次她得知我回国探亲,赶在我出发前送来便当盒,对我说,飞机餐不好吃,我给你带了点儿。那会儿安检还没有今天这般严格,待我坐在飞机上打开餐盒,是两种口味的金枪鱼寿司,顿时觉得很感动。
印象中,我总在去大学的路上买一种塑料袋包装的牛肉派,和一瓶建怡可乐,很多年后我看到瑞克·斯坦(Rick Stien)在一档美食节目中说道:没有人知道里面是什么肉,可能是牛、羊,也可能是死袋鼠(开玩笑),但是这个被浓重焦糖口味的烧烤酱涂抹的馅饼,可能是澳大利亚的第一款美食。
摩登澳餐,两个中国男孩
摩登澳大利亚是一个带有“一些野性意味”的字眼。原始、自然、纯粹,这是它变成食物时的解读。
文章作者


黑麦
发表文章231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2330人
沉迷于对抗中年危机的美食作家,对groove着迷的音乐编辑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