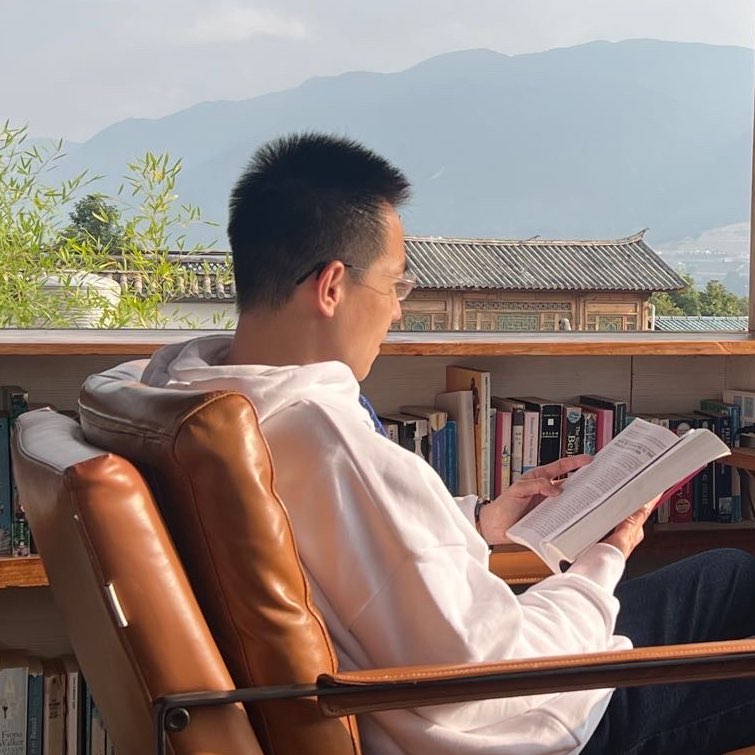新加坡故事,城市不是孤独的存在
作者:葛维樱
2018-02-07·阅读时长17分钟
1299人看过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8735个字,产生12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 1965年5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考察安居工程时与当地孩子们聊天
)
很多人和我一样,到新加坡第一件事,就想学会分辨哪栋楼是组屋。下午步行在康柏谷组屋区,骄阳被高大绿树遮蔽,那些写着“叻沙”“烧味”之类招牌下的巴刹里,老人悠然用勺子吃炒饭,幼儿园孩子们在草地上跟老师读诗,“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今年初我走访新加坡做了一篇美食报道,尽管那一行吃到许多华丽食物,组屋之下的巴刹却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喝一杯9毛钱的煎蕊,看着硕大的海鲜被做成平民的云吞和快炒,组屋是我可以感觉到的新加坡最直接的制度式甚至宪法一般的存在。当下住宅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意味复杂,越来越明显的阶级固化、身份认同、户籍制度和教育改革,无一不附加在住宅上,在一个超级大城市里,我们似乎被戴上了能被住宅魔咒时刻收紧的头箍。压力越来越大,孤独感与日俱增。好奇的我收到了一份来自新加坡国际基金会的邀请:“你想知道更多吗?”
居者有其屋
从地点、高度、建筑外立面、窗户大小、阳台欣欣向荣的热带绿植上,确实很难分辨。“不设围墙的是组屋。”住建部公务员给我个最简单的细节。我发现在新加坡步行确实不会遇到死路,也没有绝对的死角,总能看到几个围坐聊天的居民、一个通往大路的花园。在今天全世界高密度超级城市的行列里,在商业景观下重新定义这个几十年里一以贯之的公共住宅政策,依然像一个不可能却又现实的乌托邦。
0人推荐
文章作者


葛维樱
发表文章52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1022人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