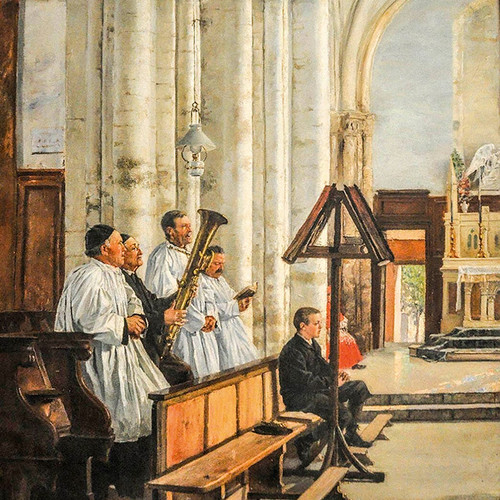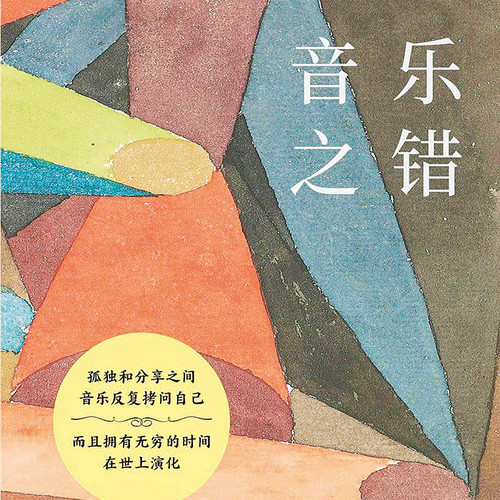魂归何处:《不哀之歌》余墨
作者:爱乐
2021-01-27·阅读时长7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3985个字,产生0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文/曹利群
多年前读到高尔基《俄罗斯浪游散记》,一个唱哀歌的母亲形象立时在我心上划了一个口子:她“双手交叉在胸前,蓬头垢面仰天凝视着,头巾滑了下来,晚风把她栗色的头发轻轻吹拂在她俏瘦的黑脸庞。一双睁得圆圆的眼睛无神地瞪着,仿佛要鼓出来一样。她的样子显得非比寻常,恐怖,甚至是可怕。用坚定的琴弦般的声音不停地哭嚎着。站在她面前的村妇们挤成一团,悄悄地哭了起来……在场的人都哭了,黄昏的天在窗外映得火红,响起一阵阵下葬的哭号”。比哭泣更痛彻心扉的是看别人哭泣,那样哀恸的场面,见证了死亡的同时也充满了生命的庄严。一个名叫安德烈耶夫娜•费多索娃的女人,从14岁一直唱到98岁。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双目炯炯发光,气度非凡,声调时而高亢时而低沉,一双瘦骨嶙峋的赤褐色的手为灵感驱动,从容地挥舞着。类似的情景也出现在穆齐尔《斯洛文尼亚的葬礼》中。从此我便记住了这些唱哀歌的女人。及至编辑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散文诗歌集时,才晓得俄罗斯妇女的悲剧命运从沙皇时期一直延续到铁幕下,只是唱哀歌的女人不再是村妇,而是俄罗斯的诗人茨维塔耶娃。1941年8月,走投无路的女诗人连一份洗碗工的活儿都得不到,只好以一条绳子悬梁自尽。同在后方的肖斯塔科维奇也没能解救得了她。多年后,也即老肖逝世的前几年,终为茨维塔耶娃的六首诗谱写了曲子。有多少遗憾和痛被作曲家倾泻在音符与诗句之间,无以言说地皆被作曲家吞咽。其实无论乡野还是庙堂,口口相传的民歌还是作曲家的创作,哀歌,悲歌,挽歌,大体是一个心思:缅怀先人,抒发胸臆,记录下一段失而难以复得的情感。
究其根本,哀歌(Elegy)源自古希腊的Elegus、elegeia,意思是伴着笛子唱的丧葬歌。最初是指以挽歌对联写成的文字,涉及的主题包括死亡、爱情与战争。也包括墓志铭、悲哀的歌曲和纪念性诗文。无论作为诗还是歌,哀歌都表达了对某位故去的人带有敬意的哀悼。公元前200年,一个叫Sekulos(塞基洛斯)的希腊人为他去世的妻子写了一首歌,然后刻在她的墓碑上。也许这是人类哀歌最早的记录。接下来,一辈又一辈的山野乡人或者职业作曲家写过无数哀歌,无论民间的葬礼进行曲还是宗教的安魂曲,都是对于亡灵的超度。曾经有人问过我,为什么对那些哀伤的东西心心念念。这让我想起阿根廷作家波尔基亚的那句话,“你看不见泪流成河,是因为其中没有那一滴来自你的双眼”。始终记得2005年在北京音乐厅看陈其钢的《看不见的声音》。演出前他在台前讲述说,他经常在梦中与故去的亲人相见,但只见容貌却不闻其声。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看不见的声音”,它将伴随我们走过生命的整个历程。音乐听得我难过。半场休息时刚好碰到他,我说我的感受只有四个字:双泪长流。他居然用同样的四个字回复我。后来他的儿子陈雨豪因车祸丧命,这让他痛不欲生。之后几年的痛定思痛翻转了他的音乐风格,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有心伤,也沉潜着无言的爱。一下又想到了古斯塔夫•马勒,虽然《亡儿悼歌》不是痛惜之作,但失去女儿的他总在之后的作品中心有戚戚。
文章作者


爱乐
发表文章834篇 获得3个推荐 粉丝18379人
三联书店《爱乐》杂志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